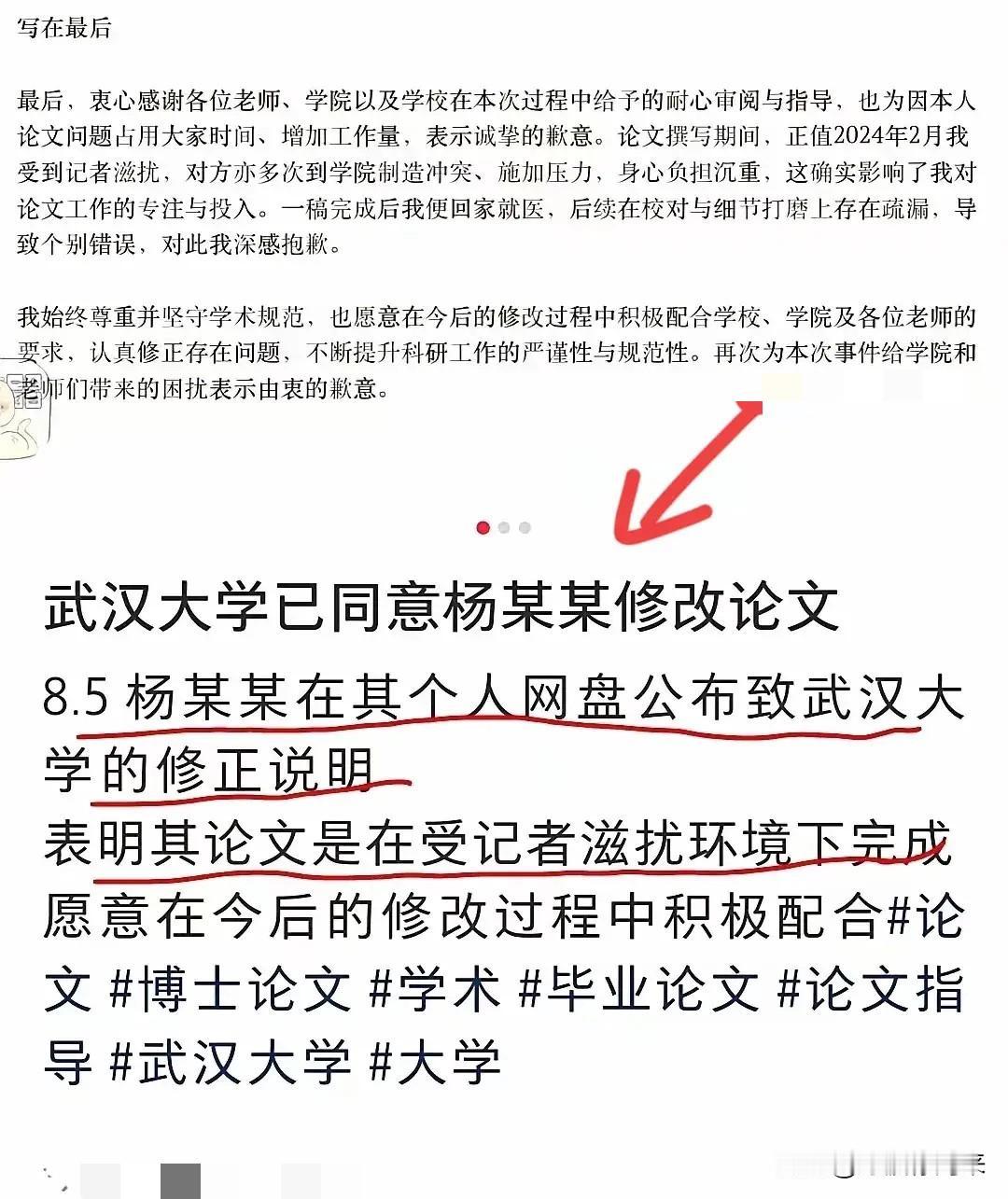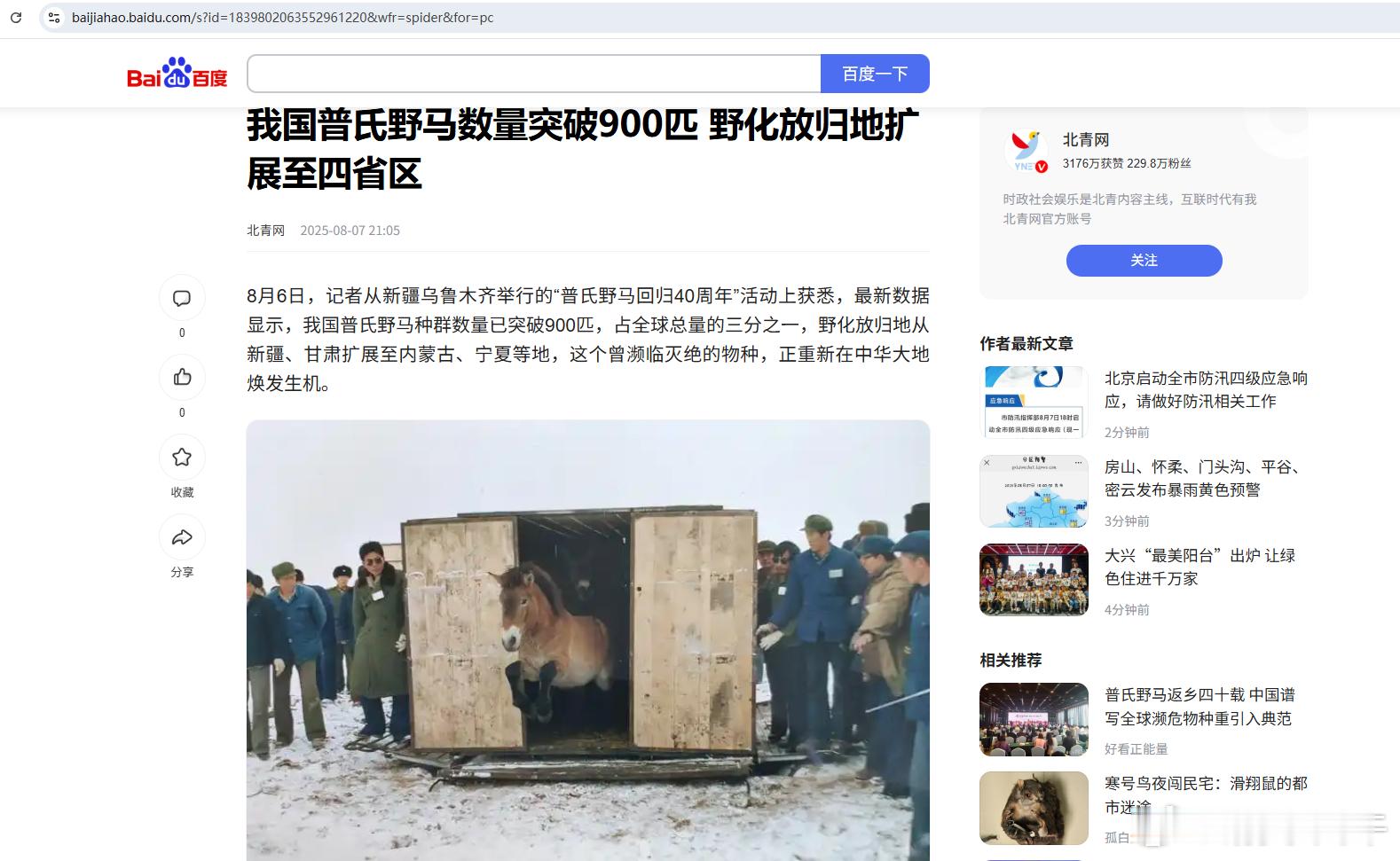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咱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咱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1967年6月17日清晨,罗布泊的戈壁滩上,风沙卷着热浪扑面而来。于敏站在临时搭建的观测点,防护服下的手紧握着一叠计算稿纸,纸页已被汗水浸透。几个月前,他和团队在上海的“百日会战”中,彻夜推演氢弹构型,靠着算盘和一台每秒运算仅5万次的J501计算机,硬生生啃下了热核燃烧的理论难题。 那台计算机95%的时间被原子弹项目占用,留给氢弹组的,只有深夜的零星时段。于敏带着十几个年轻人,泡面箱堆满走廊,演算纸摞成小山,常常一算就是通宵。 试验的倒计时开始了,战机划过天际,降落伞缓缓飘落。8点20分,一声巨响,火球冲天,蘑菇云翻滚而起。于敏的嘴角微微上扬,但眼眶却湿了。他想起1961年那个雪夜,钱三强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们得赶在法国之前搞出氢弹!” 那时的他,刚在原子核理论上崭露头角,却毅然放弃学术前途,转向这个陌生而艰巨的领域。 可这朵蘑菇云背后,他又欠下了家里多少? 回到北京的当晚,家中油灯昏黄,两间小屋挤着老少三代。孙玉芹正在补孩子的一件旧棉袄,针线在布料上穿梭,发出轻微的“嗤嗤”声。于敏推门而入,风尘仆仆,脸上却带着难得的笑意。他提议买只烤鸭庆祝,孙玉芹却愣住了。2元8角一只的烤鸭,对这个月月精打细算的家庭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于敏从兜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钞票,那是刚领到的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可孙玉芹掰着手指一算,房租15元,孩子学费12元,老家寄去的20元,剩下的钱买只鸭子还得再凑凑。于敏低头不语,默默把钱塞回兜里。那一刻,他想告诉妻子,这只烤鸭不是为了一时口腹之欲,而是为了庆祝中国从此有了挺直腰杆的底气。 可保密的誓言像一块石头,压得他一个字也吐不出。 1965年的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机房里,昏暗的灯光映照着一群年轻人的身影。于敏站在黑板前,粉笔屑沾满袖口,嗓子因连日讲解而沙哑。这是“百日会战”的第87天,团队要验证一套全新的氢弹构型。国际核大国对技术严密封锁,国内连参考资料都没有,于敏只能带着大家从“第一原理”出发,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推演。 机房里,算盘珠碰撞的“啪啪”声此起彼伏,偶尔夹杂着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于敏的桌前,摞着厚厚的演算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数字。他的头发已开始脱落,眼神却亮得吓人。同事杜祥琬回忆,那段时间于敏像个“拼命三郎”,常常凌晨还在机房,嘴里念叨着“反应截面”“热核燃烧”。有一次,他发现美国《现代物理评论》上关于氚氚反应截面的数据有误,凭借Breit-Wigner公式推导出正确上限,避免了团队走弯路。 这次发现,让中国少花了数百万的资金,也节约了宝贵时间。 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让于敏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冬,他奉命前往西北参与最后攻关,三个月下来,体重从120斤掉到不足100斤。回到北京时,孙玉芹看着丈夫瘦得像根竹竿,心疼得直掉泪。 她从没问过他在西北干了什么,只默默煮了一碗热粥,端到他面前。于敏端着碗,盯着袅袅升起的热气,突然说:“玉芹,等我闲下来,带你去全聚德吃烤鸭。”孙玉芹笑着应了,心里却知道,这承诺不知要等多久。 于敏的家,是一间逼仄的平房,书桌被孩子和他的演算纸轮流霸占。孙玉芹每月56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还要寄钱给天津老家的父母。于敏的工资因涉密项目审批复杂,常常几个月发一次,家里常靠借钱度日。孩子们记得,母亲总在深夜缝补衣服,针脚细密,像在缝补生活的裂痕。 邻居偶尔嚼舌根,说于敏神神秘秘,怕不是犯了啥事。孙玉芹从不争辩,只淡淡一句:“他干的是正经事。” 1967年氢弹成功后,于敏的生活并未轻松。他继续投身核武器小型化研究,奔波于北京和绵阳的深山之间。1969年的一次地下核试验,他因过度劳累差点晕倒在现场,同事硬是把他搀回宿舍。 孙玉芹从没抱怨,但每逢周末,她总拉着于敏去玉渊潭散步,想让他喘口气。可于敏一坐下,就掏出纸笔演算,急得孙玉芹满公园找人。 1986年,于敏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2000元。回家路上,他特意绕到全聚德,买了只金黄酥脆的烤鸭。 晚饭时,孩子们围着桌子,盯着那只19年未实现的“烤鸭梦”,眼里满是笑意。 于敏的一生,是无数个日夜与算盘、公式为伴的隐秘岁月,也是与家人聚少离多的亏欠时光。他用智慧为国家铸就核盾,却用最朴素的生活温暖着家人。1967年的那朵蘑菇云,不仅是中国核武器的里程碑,更承载了无数像于敏一样的科学家及其家庭的牺牲与坚守。

![商家也是没办法了,只能拿预制菜配料表自证清白[汗][汗]](http://image.uczzd.cn/1608647452444728434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