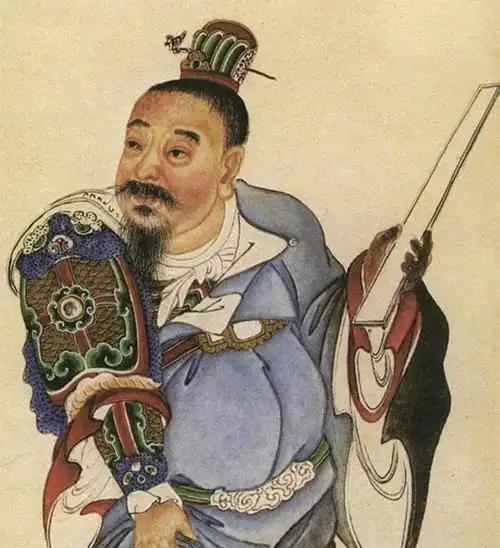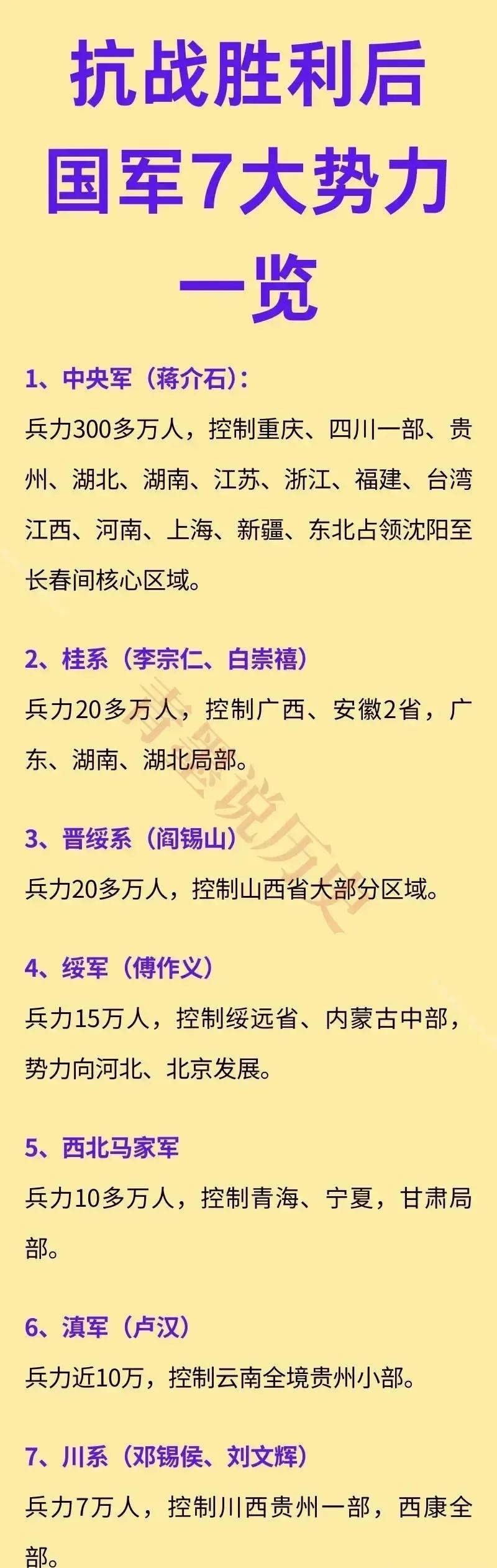蒙古西征时侵犯突厥女性,造出一新民族,如今成了俄国人的噩梦。
主要信源:(《蒙古帝国史》;《俄国史教程》;《金帐汗国兴衰史》)
1236年寒冬,伏尔加河被严寒彻底冰封,冰面坚硬如铁。蒙古王子拔都率领十万铁骑,如一股汹涌的洪流,浩浩荡荡地冲过冰河,目标直指保加尔人的比拉尔城。
这座伊斯兰风格的城池颇为富庶,城内商贾云集、贸易繁荣。然而,蒙古人的攻势异常猛烈,持续了整整四十五天。最终,坚固的城墙在蒙古人的轮番攻击下轰然倒塌。
城破之后,惨状令人不忍直视。城中的男子几乎全部战死,而女人和孩子则遭遇了更为悲惨的命运,她们被蒙古人像驱赶牲口一般,赶进了蒙古军营。
据一位波斯史学家记载,蒙古人从城中挑选出年龄在十二到四十岁之间的突厥女人,将她们视为士兵的私有财产进行分配。仅这一座城,就有几十车的女人被运走。在整个西征过程中,被蒙古人抓走的突厥女性可能多达十万。
这些可怜的女人,白天要为蒙古士兵缝制铠甲、烧茶做饭,承担繁重的劳役;到了晚上,她们又沦为士兵的伴侣或奴隶,饱受折磨。
蒙古军营中还制定了一条残酷的规矩:在战场上立下战功的人,可以优先挑选女人。蒙古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沉默不语的突厥女子,竟在不经意间埋下了未来翻盘的种子。
在军营里出生的混血孩子,他们的第一声啼哭仿佛都带着突厥歌谣的韵律,学会喊出的第一声“妈妈”,也是用突厥语。孩子们整日缠着母亲,跟着她们学习诵读伊斯兰教的经文,口中念叨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等经文内容。
蒙古父亲们常年在外征战,偶尔回到军营,惊讶地发现孩子们之间吵架都用突厥语,就连放马时哼唱的小调,也带着伏尔加河地区独特的韵味。 女人们在白天劳作的间隙,会偷偷用突厥语传递军营里的消息,比如“东边抢到了布匹”“河对岸藏着好马”等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闲话,就像撒在军营里的草籽,逐渐生根发芽,悄然改变着一切。
到了1250年,金帐汗国的公文书里,突厥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等到拔都的孙子忙哥帖木儿继承汗位时,士兵们在汇报军情时,嘴里竟不时冒出突厥词汇,如“朋友”“自由人”等。曾经在金帐汗国通行的蒙古语,在自己的地盘上反而成了需要翻译的陌生语言。
金帐汗国的发展如同草原上的一场野火,燃烧得迅猛,熄灭得也迅速。十四世纪后半叶,这个庞大的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王公贵族们为了争夺权力和地位,相互倾轧、内斗不止,边疆地区也陷入了无人有效管理的混乱局面。曾经纵横驰骋的蒙古骑兵,如今却成了贵族们内斗的工具。 在权力真空的缝隙中,一群特殊的人崭露头角。他们是混血后代,父亲是蒙古士兵,母亲是突厥人。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突厥的语言和文化,对草原的地形了如指掌,骑马射箭的技艺十分高超,性格也十分刚烈。
他们既不认同蒙古人的大汗,也不亲近突厥部落。当金帐汗国的统治中心开始崩塌时,他们最先嗅到了自由的气息。
与此同时,一些生活在底层的蒙古人、突厥人和斯拉夫人,由于无法忍受沉重的苛捐杂税和贵族的残酷剥削压迫,纷纷逃离汗国的控制范围,前往那些汗国势力难以触及的地方,如第聂伯河下游的激流险滩、顿河的广袤草场以及乌拉尔山的茂密森林。
他们给自己取名为“哥萨克”,在突厥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自由人”“冒险者”或“流浪汉”。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们的身份和生活状态,他们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只依靠自己的兄弟伙伴生存。
为了在这乱世中求得生存,哥萨克人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他们精心挑选适宜防守的地盘,建立起自己的据点,称为“塞契”,其中最有名的位于扎波罗热地区。
第聂伯河流经此处时,形成了众多岛屿和乱石滩,船只根本无法顺利通行。哥萨克人便在这些岛屿上搭建营房,用粗壮的树干堆砌起高高的城墙,挖掘深深的壕沟,将其作为坚固的堡垒。
如果敌人从水路进攻,混乱的河道会让他们寸步难行;如果敌人从陆路来袭,茂密的芦苇地和泥泞的沼泽将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锤炼出了哥萨克人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在马背上长大,孩子们还没学会走路,就已经开始学习骑马。大人们甚至可以在骑马时入睡,马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生命的依托。
哥萨克人的骑术堪称一绝,他们能够在高速奔跑时迅速转身射箭,也能在马镫下巧妙藏身,躲避敌人的攻击。战斗时,他们轻装上阵,不穿笨重的铠甲,只佩戴轻便的护甲,甚至有人光着膀子冲锋陷阵。他们的武器主要是马刀、长矛和弓箭,后来又配备了火枪。
他们的战术灵活多变,以“打完就跑”为主要策略:像狼群一样,熟悉地形后悄悄靠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抢夺财物、打击敌人后,便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塞契内部的管理模式十分独特,既有民主的一面,又强调严格的纪律。重要事务由大家共同召开“拉达”会议决定,并选举出头领盖特曼,但盖特曼不能独断专行。一旦军令下达,所有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严明。
如果有谁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或者违抗命令、偷窃他人财物,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轻则挨鞭子,重则被砍头。这种独特的管理模式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哥萨克人就像一把锋利的刀,融合了蒙古人的灵活、突厥人的坚韧和斯拉夫人的硬气,让周边邻国寝食难安。
哥萨克的崛起,让莫斯科大公国既感到恐惧,又十分头疼。恐惧的是,哥萨克人为了生存和展示自己的本领,经常打劫金帐汗国的残部以及波兰和俄国南部的村庄。他们抢夺财物、掳掠人口、烧毁土地,成为了南方边境地区的噩梦。
更让沙皇们烦恼的是,哥萨克人不承认任何君主的主权,他们将塞契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向任何政权缴纳税款,也不承担任何差役。沙皇们深知,这群桀骜不驯的“野人”随时可能闹事,对中央集权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沙皇们想出了一系列办法。从伊凡雷帝开始,他们用钱粮和武器拉拢哥萨克人,承诺给予他们自由待遇和一定的土地。哥萨克头领还被授予权杖和贵族名号。
沙皇们的如意算盘是,让哥萨克人为自己守卫南方边境,抵御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入侵,在战争中充当先锋。作为交换,哥萨克人则需要效忠沙皇,履行兵役义务。
在后来的历史中,哥萨克人在开拓西伯利亚、与波兰和土耳其作战等过程中,冲锋陷阵,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从未熄灭。
沙皇的政策逐渐收紧,对哥萨克人的管制越来越严格,比如限制他们传统的抢掠行为、推行新的宗教政策等。这些举措让哥萨克人感到憋屈和不满,积累的怨气最终爆发。
沙皇们的噩梦成真了。十七世纪的斯捷潘·拉辛起义、十八世纪的普加乔夫起义,都是由哥萨克头领振臂一呼,广大农民纷纷响应。起义的烽火燃遍了伏尔加河地区,甚至一度打到了莫斯科城下。
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但它们就像一记记沉重的鞭子,抽打在沙皇的背上,让沙皇们意识到,自己曾经招安的这把“利刃”,如今已经变成了威胁自身统治的“祸根”。
对此,您又有怎样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