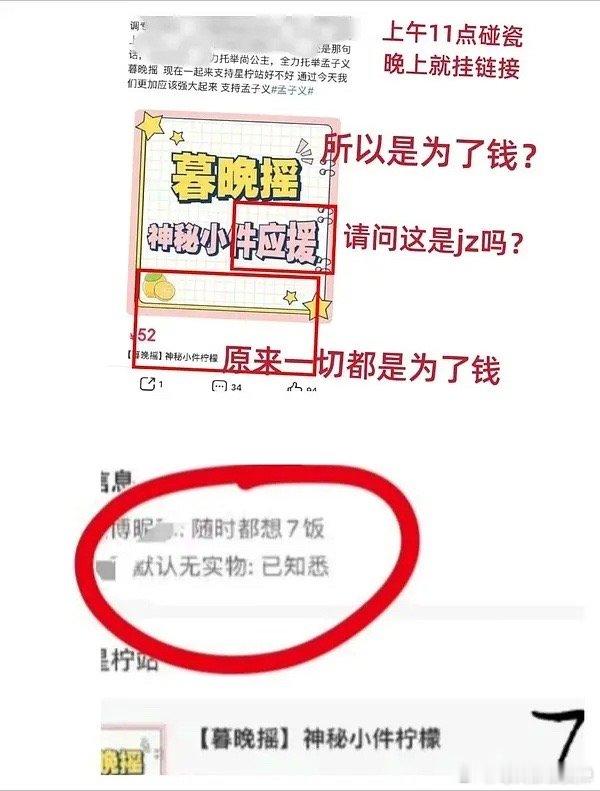1945年,湘西会战150个鬼子各身绑上百斤炸药,紧贴武冈城墙拉响导火索,城墙倾圮,千余日军发起猛攻。军长施中诚令74军集中卡宾枪、汤姆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疾向缺口狂扫。 城墙塌下去的那一刻,施中诚正站在北门城楼的残角上。望远镜里,日军像潮水往缺口涌,绑炸药的鬼子残骸还挂在断砖上。他攥着指挥刀的手沁出冷汗——武冈是湘西门户,丢了这城,日军就能直插芷江机场,整个会战的防线就崩了。 74军刚从雪峰山转战过来,士兵们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卡宾枪是刚从美军那领的,不少人还没摸熟。 缺口里腾起火柱,砖头像爆米花一样乱蹦。施中诚把望远镜往下一压,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传令兵正猫着腰往上冲,钢盔大得能盖住半张脸。 “军长,子弹箱送上来了!”娃儿嗓子劈叉,却笑得见牙不见眼,“美国佬的汤姆枪,子弹真亮,像镀了油!” 施中诚没搭腔,抬手给他整了整歪到一边的绑腿。娃儿袖口一截白纱布露出来,血迹干成了酱油色——那是三天前在雪峰山被弹片啃的。枪声密得像雨点砸铁皮,施中诚突然冒出一句:“怕不怕?” “怕个鬼!”娃儿咧嘴,一口白牙,“我哥在常德城墙上被鬼子挑了,今天咱得把账算回来。” 说话间,缺口处传来一阵闷罐似的爆响,火焰喷射器“呼啦”一声,把冲在最前面的鬼子点成火把。焦糊味顺着风飘上来,混着糯米三合土的潮腥,像谁家蒸坏了的年糕。施中诚心里一揪:这城墙是老百姓拆了自家灶房,把糯米舂碎拌灰浆,一杵一杵夯出来的。如今墙塌了,灶房也没了,老百姓却拎着菜刀、扬着锄头往缺口跑,跟当兵的一块扛沙袋。 “军长,让老乡撤下去吧!”副官凑过来喊,“他们没枪,顶不住!” 施中诚摇头,嗓子发干:“他们早把命押上了,撤?往哪撤?” 他忽然想起出川时老娘塞给他的布包,里头三块大洋、一把炒米,还有张皱巴巴的纸条——“儿啊,打不赢就别回来。”老娘不识字,是隔壁教书先生写的。施中诚当时笑,说老娘真看得起儿子,三块大洋就想买场胜仗。现在才懂,那纸条不是给他一个人,是给所有把背抵在城墙上的人。 缺口又被撕开一道口子,鬼子像蚂蚁涌进来。一个穿蓝布衫的老汉抡起扁担,照头劈下去,扁担断了,人也被刺刀挑了个趔趄。老汉倒下的瞬间,怀里滚出一只瓦罐,碎了一地腌辣椒,红得扎眼。传令兵扑过去想扶,被老汉一把推开:“小崽子,开枪啊!老子七十了,够本!” 枪声更密,卡宾枪、汤姆枪、汉阳造,响成一锅粥。施中诚忽然听见一段旋律,细一听,是有人在唱《长城谣》,调子跑得厉害,却一字一句砸在人心上——“长城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唱歌的是个扎麻花辫的姑娘,正把一捆手榴弹往战士怀里塞。她抬头冲施中诚笑,眼睛亮得像两颗星:“军长,炸完了再唱给您听!” 施中诚喉头滚动,想说点什么,一颗炮弹在脚边炸开,气浪掀得他倒退两步。再抬头,姑娘不见了,只剩半截麻花辫挂在断墙上,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天边泛起蟹壳青,炮声渐渐稀了。缺口被沙袋堵上,鬼子留下一地焦炭,退了。施中诚踉跄着走到缺口,看见那半截辫子下压着张纸条,墨迹被血晕开,勉强能认出一行字——“若还听见长城谣,便是我们赢了。” 他蹲下去,把纸条折成小小一块,塞进贴胸口袋。风从雪峰山吹来,带着松脂和硝烟的味道。远处,老百姓开始清理废墟,有人哼起小调,跑调的还是那一句——“长城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施中诚摸摸传令兵的头,娃儿正用刺刀在砖上刻字,歪歪扭扭三个字:武冈城。他问:“刻它干嘛?” 娃儿咧嘴:“怕哪天我死了,有人来找,知道这儿叫武冈,知道咱没退。” 施中诚没说话,抬头看天。天很蓝,像被水洗过的瓷。他忽然想起美国人发枪时说的一个词:Home front。当时翻译半天没翻出味儿,现在懂了——前线是城墙,home front是城墙后那口冒着热气的糯米锅,是锅边唱歌的姑娘,是抡扁担的老汉,是刺刀刻下的三个字。 枪声又响了,这次是追击的号音。施中诚拍拍屁股站起来,把指挥刀往肩上一扛:“娃儿,走,咱们把账算完。” 阳光斜斜地切过城墙,缺口像道愈合中的伤疤。风卷着硝烟,把《长城谣》的调子吹得很远很远。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