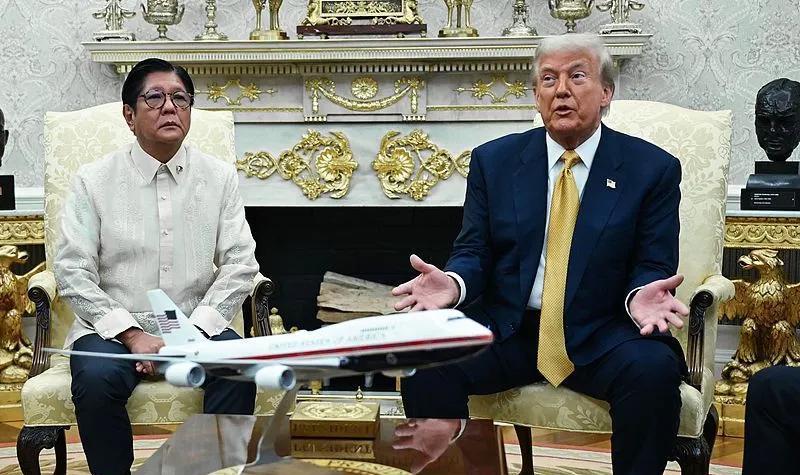加税这种事,凭什么特朗普行, 拜登奥巴马不行?
还记得2018年那个夏天吗?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挥动关税大棒,向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砸下15%到40%不等的重税时,世界贸易体系仿佛挨了一记闷棍。
彼时,批评声浪铺天盖地,预言“经济自杀”的分析师比比皆是,然而,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2025年中回望,一个冷酷的现实是,特朗普当年的“关税风暴”非但没有成为孤立的历史事件,反而开启了一个“经济武器化”的新时代。
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何看似“离经叛道”的特朗普能做成这事,而他的前任们却踌躇不前?
这背后,远非个人能力高低那么简单,而是时代齿轮转动下,美国战略焦虑的集中爆发与全球权力格局深刻重塑的必然产物。
说奥巴马和拜登“菜”,显然有失公允,奥巴马时代,美国虽已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但整体上仍试图,在全球多边框架内维持其主导地位,其战略更偏向于规则内的竞争与接触。
拜登时代(2021-2025初),尽管延续并深化了特朗普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初期也曾短暂寻求与盟友协调“去风险化”而非简单脱钩,但其政策工具箱里,“关税”这把刀的使用,相较于特朗普的“无差别攻击”,显得更为“精准”且试图披上盟友协调的外衣。
美国社会内部撕裂的顶点, 2016年前后,美国蓝领阶层对全球化导致产业流失、工作机会外移(尤其是流向中国)的愤怒达到高潮。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正是这种民粹主义浪潮的集中体现,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并利用了这股力量,将关税包装成“夺回工作”、“惩罚不公平贸易”的直接武器,在国内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动能。
这种动能,是奥巴马和拜登在各自任期内初期所不具备或不愿全力激化的。
大国竞争临界点的到来,到201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高端制造(如高铁、通信设备)、科技(如5G)等领域的快速突破,以及经济总量的迅猛追赶,让美国战略界真正感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迫近。
特朗普打破了前任们相对克制的“接触+防范”策略,直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税战成为其遏制中国崛起最直接、最具“爆发性”的手段。
他率先捅破了那层“战略模糊”的窗户纸,多边贸易体系的脆弱性暴露,WTO争端解决机制在特朗普上台前已陷入僵局,其效率低下和难以约束大国行为的弱点,被特朗普充分利用。
他绕开WTO,直接依据国内法实施单边关税,以“破坏规则”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示了美国仍拥有的、基于实力的“特权”。
这种“复杂性”在于,它既破坏了体系,也迫使所有国家重新审视对这套旧体系的依赖。
2025年5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对华“301关税”的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大幅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等关键清洁能源产品的关税,部分税率甚至比特朗普时期更高。
欧盟紧随其后,在2025年7月正式启动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并威胁征收临时关税,虽然其声称程序更“规范”,但背后的保护主义动机与对产业竞争力的担忧,与特朗普逻辑一脉相承。
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出口管制和技术投资限制层层加码, 这些非关税壁垒与高关税共同构成了更复杂、更具“针对性”的经济遏制网络。
特朗普当年的“鲁莽”,某种程度上是撕下了旧秩序的温情面纱,提前将大国博弈中“经济武器化”这一残酷的底层逻辑摆上了台面。
他证明了,即使付出自身经济代价,超级大国也有能力利用其市场地位和金融霸权,对对手乃至盟友实施具有强大破坏力的“非军事打击”,这种能力的展示本身,就改变了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