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新疆喀什城下,左宗棠面对上万俘虏,毫不犹豫地下令:“降者亦杀!”一语震动朝野,外界哗然。有人劝他宽容以归化,他却冷冷一句:“我不能拿几十万百姓的命,去赌他们会不会悔改。”这不是冷血,而是乱世中的铁血担当。 城楼上,年近七旬的左宗棠望着上万名阿古柏叛军的残兵败将。 那些跪着的人,昨日还是挥舞屠刀的恶魔,手上沾满了亲人的鲜血。 左宗棠最终命令:“降者,亦杀!” 1865年,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廷内忧外患,悍然入侵新疆,建立伪政权。 十年间,天山南北沦为血海。 阿古柏匪军所到之处,屠城灭村,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喀什、和阗、阿克苏,昔日繁华的丝路明珠,化作累累白骨。 清廷庙堂之上,“海防”与“塞防”之争喧嚣尘上。 李鸿章等人主张放弃新疆,认为那是“化外之地”,不如将财力投入海军。 左宗棠拍案而起,怒斥其短视:“新疆者,中国之右臂也。臂断则蒙古不保,蒙古危则京师震动! 弃新疆即弃蒙古,弃蒙古即弃京师!” 他深知,失去新疆,沙俄将长驱直入,英帝国虎视眈眈,华夏西北门户洞开,国将不国! 1875年,年过花甲、疾病缠身的左宗棠,以“抬棺西征”的决绝姿态,率六万湖湘子弟踏上征途。 抬着的那口棺材,是他“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誓言,更是对身后骂名的无畏担当。 西征之路,粮草匮乏,武器落后。 士兵们背负“复我河山”的木牌,怀揣着收复故土的信念,穿越茫茫戈壁,忍受酷暑严寒。 收复北疆后,兵锋直指南疆阿古柏老巢。 然而,叛军狡诈凶残,降而复叛如同家常便饭。 阿克苏城下,清军曾对一支穷途末路的叛军施以援手,赠予粮食。 不料,这些人转眼便倒戈相向,将城池献与阿古柏。 肃州城外,左宗棠亲自收编的数百降兵,看守外围堡垒,却在半年后趁夜哗变,焚烧粮草,劫掠仓库,致使两千余无辜百姓惨遭屠戮。 哈密城下,假意归顺的降兵暗中勾结外敌,险些切断清军命脉般的后勤补给线,酿成前线覆灭之危。 一桩桩血淋淋的教训,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片土地上,对豺狼的仁慈,就是对羔羊的残忍。 喀什城破前,清军曾射入招降书,承诺既往不咎。 然而,城头扔下的,却是清军劝降使者的头颅! 那一刻,左宗棠只冷冷道出一句:“此等狼子,饲以膏粱亦难驯!” 此刻,喀什城下,上万降卒跪伏雪中。 幕僚们有人低声劝谏:“大帅,杀降不祥,古之明训。况上天有好生之德,或可收编归化,以显王师仁德?” 左宗棠却被直起身,指着城外的乱葬岗:“仁德?你们可知那乱葬岗下埋着多少冤魂?整整三千喀什百姓!被他们活活剥皮抽筋,曝尸荒野!可有人讲仁德?!” 他颤抖着手,从怀中掏出出征前陕西父老塞给他的万民血书,上面密密麻麻的血指印,诉说着沦陷区百姓的深重苦难与殷切期盼。 “‘若不收复新疆,子孙永为蛮夷’!这是百姓的血泪心声!我左宗棠抬棺西征,不是来当菩萨的!是要为惨死的同胞讨还血债!是要为子孙后代永绝后患!” 他目光扫过城下那些跪伏的身影,最终下令:“传令!立决!无需再报!” 这道命令,是他用毕生清誉和身后骂名,为南疆百姓换取的生存空间。 军令如山。 清军刀斧手列队肃立,被反绑的降卒被押至坑边,无人哭嚎,无人求饶,只有沉默。 刀光闪过,白雪染成刺目的猩红。 左宗棠站在城楼上,背对着行刑的方向。 他并非铁石心肠,这万人伏诛的惨景,如同重锤击打在他心头。 但他更清楚,在这弱肉强食的乱世,在这虎狼环伺的边疆,优柔寡断的“仁德”,只会让更多无辜者重蹈覆辙。 他的“铁血”,是为了根除后患,让这片饱经蹂躏的土地,真正获得喘息与重建的机会。 果然,“杀降”之举虽震动朝野,引来京城御史雪花般的弹劾,斥其“不仁”、“嗜杀”。 但铁一般的事实是,喀什乃至整个南疆,自此迅速安定下来。 左宗棠没有沉浸在胜利中,他深知,真正的“仁政”,不是对敌人的宽宥,而是对百姓生计的切实保障。 仅仅十年,喀什人口翻了三倍,荒芜的田野重现生机。 当地百姓感念其恩,自发在城边立起石碑,刻上四个朴拙而深情的大字:“左公保我”。 这块石碑,历经风雨,无声诉说着那段铁血铸就的和平。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这掷地有声的战略远见,连同喀什城外的石碑,共同铭刻下这位晚清重臣不朽的功勋与深沉的担当。 主要信源:(《左宗棠全集》《新疆图志》《清史稿·左宗棠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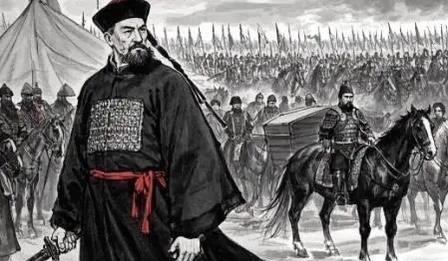

云卷云舒
[赞][赞][赞]
哈哈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左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