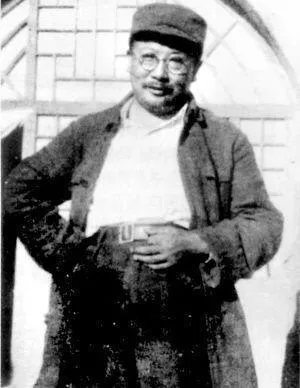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克农从毛主席的房间中搜出一颗炸弹,却找不到嫌疑人,正当他百思不解时,附近的寺庙忽然传出了敲钟声!
1949年3月24日深夜,北平西郊的香山笼罩在一片薄雾中。月光洒在双清别墅的青瓦屋檐上,映出几分清冷。院子里,李克农站在一棵老松树下,嘴里叼着半截烟,眼神却像鹰隼般扫视着四周的阴影。远处,隐约传来几声犬吠,打破了山间的寂静。他低头看了看表,指针指向凌晨两点——再过几个小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专列就要抵达清华园站。这是“进京赶考”的关键一刻,容不得半点闪失。可就在这紧要关头,一场无声的危机正悄然逼近。
天还没亮,李克农带着一队警卫员走进双清别墅的主屋。这座坐落在香山半山腰的宅院,原本是清代乾隆皇帝的行宫,如今被选为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屋内陈设简单,木地板被擦得锃亮,空气中弥漫着松木和老房子的霉味。李克农习惯性地蹲下身,检查毛泽东即将入住的卧室。他用手电筒照向床底,昏黄的光束扫过一块不起眼的木板,突然,他的手一顿——光束里,一团金属的冷光刺痛了他的眼睛。
“这是什么?”他低声喝道,声音里透着寒意。警卫员小王赶紧凑过来,脸色刷地白了。那是一枚炸弹,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蛰伏的毒蛇。炸弹的引线粗糙但致命,足以炸毁整间屋子。李克农的脑子飞速转动:这地方已经被翻查了不下十次,岗哨密布,连只老鼠都难溜进来,炸弹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更可怕的是,敌人是谁?他们还藏在哪儿?
他当机立断,命令警卫员封锁别墅,彻查每一寸角落。战士们像拉网捕鱼般,把屋顶、墙缝、甚至院子里的水井都翻了个遍,可除了这枚炸弹,再无其他线索。李克农站在院子里,眉头紧锁,脑子里翻腾着各种可能性。内部有鬼?不可能,他带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老革命,忠诚度毋庸置疑。外来渗透?可岗哨日夜巡逻,连送菜的马车夫都要查三代家底。就在他陷入僵局时,一阵低沉的钟声从山腰传来,“当——当——”,悠长而诡异,像是在嘲笑他的困惑。
那钟声来自香山脚下的一座尼姑庵,名叫慈云庵,平日里香火寥寥,几乎无人问津。李克农猛地一拍大腿,意识到一个被忽略的漏洞——为了尊重宗教习俗,保卫组对庵堂的检查草草了事,只核对了住持和几个尼姑的身份。这地方离双清别墅不过百米,地势隐蔽,简直是藏匿的绝佳地点。他立刻召集一队精干的便衣队员,借着夜色摸向慈云庵。
庵堂的木门半掩,油灯昏暗,空气里混杂着檀香和潮湿的霉味。李克农带人悄无声息地围住院子,推门而入时,一个老尼姑正低头敲着木鱼,嘴里念念有词。见有人闯入,她手一抖,木鱼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李克农盯着她的眼睛,那双浑浊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慌乱。他冷冷一笑,挥手示意搜查。
果不其然,在老尼姑的禅房里,战士们从床下挖出一个暗格,里面藏着美制雷管、一部发报机和几页密电码本。更惊人的是,她袈裟里还缝着一把手枪,子弹上膛,随时可以击发。审讯中,她很快崩溃,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她名叫慧清,表面上是出家人,实则是国民党保密局的暗桩。北平解放前,军统高层将她留在这里,专门伺机刺探情报、制造破坏。她趁夜色潜入别墅,放置了炸弹,本想用钟声掩盖撤退的动静,没料到李克农的反应如此迅速。
这起事件让李克农后怕不已。他站在双清别墅的庭院里,望着远处山峦起伏的轮廓,心里像压了块巨石。北平刚解放,国民党留下的特务网络远比想象中复杂。1949年初,北平城内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多达百余个,职业特务不下8500人,藏在商贩、学生、甚至寺庙的僧人中,无孔不入。
为了确保安全,他连夜调整了安保方案。别墅的勤杂人员全部更换,岗哨从三班倒改为两班倒,连送来的蔬菜都要用探针检查。他甚至亲自带人挖了一条防空地道,尽管毛泽东笑着说“太夸张了”,他还是坚持把工事加固到能抗住小型炮击。 每晚,他都会站在别墅的露台上,借着微弱的灯光翻看情报,哮喘的咳嗽声在夜里格外清晰。他的右眼早已失明,那是早年在苏区熬夜制定保卫条例时落下的病根,但他从不提及,部下也只当他戴眼镜是为了遮掩疲惫。
香山的夜晚并不平静。松林间偶尔传来夜枭的低鸣,山风吹过,树影摇曳,像无数双眼睛在窥视。双清别墅的院子里,青石板路被踩出浅浅的痕迹,那是警卫员巡逻时留下的。屋内的油灯昏黄,投下长长的影子,每当风吹窗棂作响,战士们都会下意识地握紧枪柄。这样的氛围下,李克农的每一次决定都像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949年7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迁入中南海,双清别墅的使命暂时告一段落。李克农站在香山脚下,望着那座承载了无数惊险的宅院,点燃了最后一支烟。没人知道,这五个月里,他粉碎了不下六起针对中央领导的暗杀阴谋。
历史不会记录每一场暗战,但那枚被拆除的炸弹、那阵夜半钟声,早已刻进新中国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