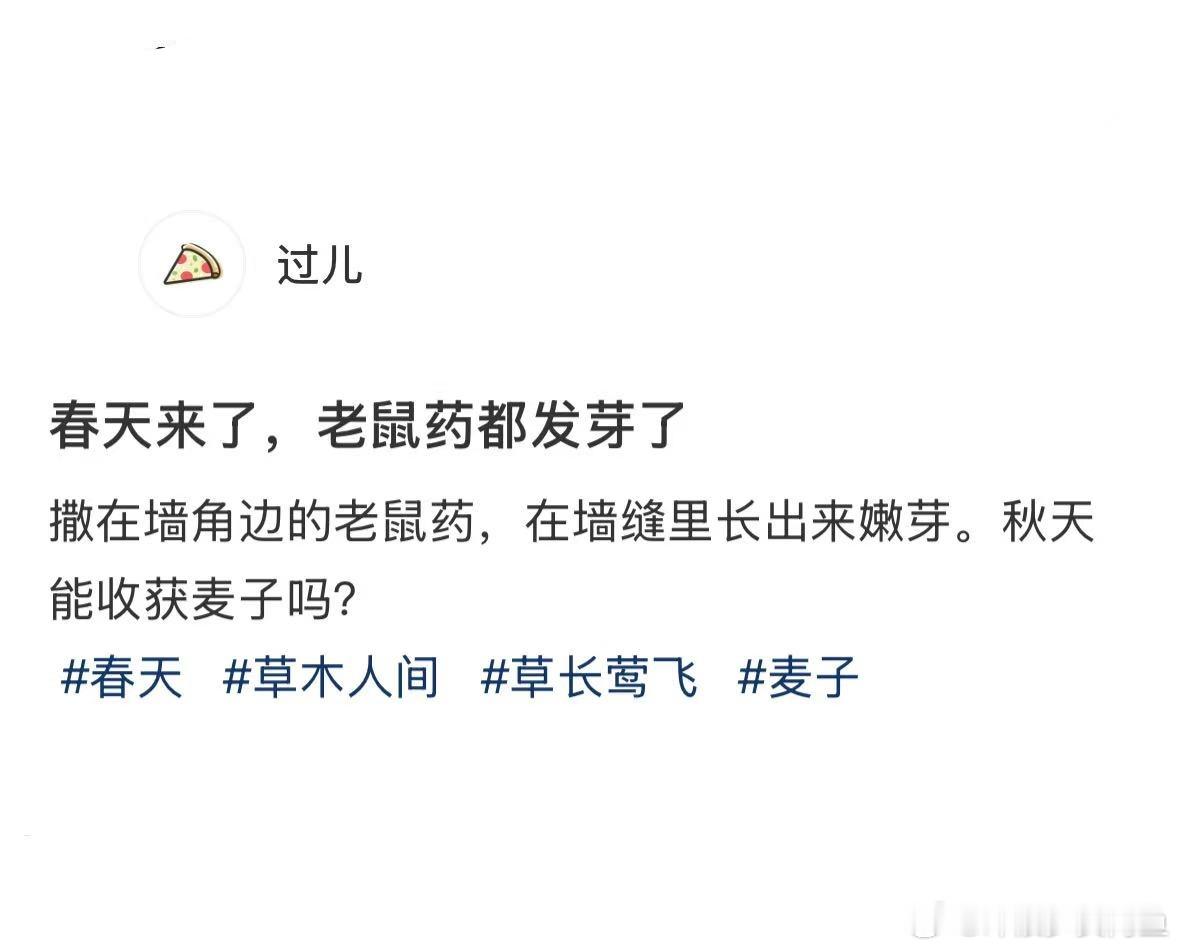江南人家,庭院里种植的鱼腥草随处可见,但凡庭院里或庭院外有可种植绿化带的,都能看到鱼腥草娇小优雅的身影。如今,正是鱼腥草花盛开的季节。 鱼腥草实在是一种奇妙的植物。乡下人唤它"折耳根",文人墨客称它"蕺菜",而《本草纲目》中则记作"蕺",李时珍说它"叶有腥气,故俗称鱼腥草"。 这草的叶子是极有意思的。心形,宽大,正面深绿,背面却常常泛着紫红。叶脉分明,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开去,像是谁用细笔精心描画的一般。春夏之交,茎顶上会抽出穗状的花序,开满细小的白花,四片花瓣,中间点缀着黄色的花蕊,朴素得很。但妙的是那花穗基部生着四片白色的苞片,形如花瓣,远看倒像是一朵大白花。 鱼腥草的气味是极特别的。手指轻轻揉搓叶片,便有一股子腥气窜上来,初闻令人皱眉。但这气味里又藏着几分清香,像是混了泥土和水汽的味道。奇怪的是,这腥气经滚水一烫,便化作一种奇异的香气,引得人食指大动。西南一带的人最懂得欣赏此物,或凉拌,或涮火锅,或与腊肉同炒,总能化腐朽为神奇。 此草性子寒凉,入药能清热解毒,排脓消痈。《滇南本草》说它"治肺痈咳嗽带脓血,痰有腥臭"。《本草纲目》亦载其"散热毒痈肿"。现代医家更发现它能抗菌抗病毒,治肺炎、气管炎颇有良效。乡间老妪常教小儿采来煎水喝,治那热伤风最是灵验。 我幼时在乡下,常见农人于田埂边采撷此草。他们手法娴熟,只掐那嫩茎嫩叶,留其根本,来年又可再生。母亲常将鱼腥草洗净切段,与辣椒油、蒜末、酱油、醋同拌,做成一道开胃小菜。那滋味初入口时确有些怪异,但细细咀嚼,便觉一股清气自喉间升起,暑热顿消。 而今城里人吃鱼腥草,多是餐馆里精致的凉拌折耳根,或火锅店中装在竹篮里的嫩芽。殊不知此物最妙是野生的,长在湿润的田边地角,沾着露水时采来最佳。人工种植的虽肥大好看,却少了几分野性的气息与药效。 鱼腥草实在是一种矛盾的植物。气味虽腥,却能治病;模样朴素,却有大用;生于秽土,却能洁净人体。它不似牡丹富贵,不如幽兰高雅,但自有其朴实无华的价值。这倒像极了那些默默无闻的乡野之人,虽不起眼,却在关键时刻显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每见鱼腥草,总想起那句俗语:"家菜没有野菜香。"人生百味,有时正需要这点腥香来点醒麻木的味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