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后文简称秦王稷)为啥最后要杀白起?这对秦国来说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吗?
一切要回到他们合作得如胶似漆的那些年。
白起与秦昭襄王的“黄金组合”
那会儿的白起,简直就是秦王稷开疆拓土、横扫六国的超级大杀器!
时间回到战国中期(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像吹气球一样猛涨,野心也跟国力同步膨胀。当时的秦王稷(秦昭襄王)在位时间超长(56年),他有雄心,也敢用人。
白起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军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靠着能打仗、会打仗、敢打硬仗恶仗的狠劲儿,一步步从底层士卒爬到了军功爵位的顶峰。

这对君臣搭档一起干了啥惊天动地的大事?看看白起的战绩牌:
伊阙之战(前293年):白起作为主将,一战干掉魏韩联军24万!这是秦国东进的里程碑胜利,敲开了中原的大门,也彻底打响了白起“人屠”的威名(因为杀降太狠)。
鄢郢之战(前279-278年):长驱直入楚国腹地,攻破楚国旧都鄢(今湖北宜城)和国都郢(今湖北江陵),把楚王撵得鸡飞狗跳跑到陈(河南淮阳)苟且。这一仗,直接把南方巨无霸楚国打得半身不遂,几十年缓不过劲儿来!秦王稷高兴得不行,封白起为武安君!这爵位,分量沉甸甸!
华阳之战(前273年):长途奔袭救援韩国(当时韩是秦盟国),大败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展现了长途机动、闪电突袭的硬实力。
最顶峰:长平之战(前260年)!这场战国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役,把白起的军事才能和秦王稷的君臣信任推到了顶点。秦国和赵国为了争夺战略要地上党,倾全国之力对磕。秦王稷启用白起为帅(秘密更换王龁)。白起以退为进,诱敌深入(赵括取代廉颇),然后出奇兵截断赵军粮道,形成合围!将四十多万赵军(包含少量上党韩军)死死困在长平山谷。

坑杀四十万赵卒!为了彻底摧毁赵国战争机器,解决粮食问题,白起下令将绝大部分投降的赵军坑杀(只放回240个年幼的)。这次残忍的举动震惊天下,但也彻底打断了赵国的脊梁骨!赵国从此一蹶不振。秦国扫除了东进的最大障碍。
看看这些战果,哪一场不是震动天下的大胜?白起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战争机器,指哪打哪,攻必克,战必胜!秦王稷呢?他对白起简直信任到了极点!要兵给兵,要粮给粮,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把最高的荣誉赏给他。这对君臣,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不可逆转的优势。白起是秦王稷实现霸业梦想的最强武器,秦王稷则是白起展现军事天才的最佳舞台。两人配合默契,大杀四方。
表面看,这简直是最完美的君臣组合。秦王稷志在四方,白起为他披荆斩棘。“我王剑之所指,即白起军锋所向!”这种关系,看起来固若金汤。

将相之争
然而,再坚固的堡垒,也往往是从内部先开始松动的。白起和秦王稷这对黄金搭档走向悲剧的关键转折点,跟一个人的到来密不可分,应侯范雎。
范雎是魏国人,很有才能,但被魏国丞相陷害差点死掉。他逃到秦国,在公元前270年左右见到了秦王稷,一番“远交近攻”的大战略(放弃之前穰侯魏冉等人远攻齐国的策略,改为集中力量优先收拾身边的韩赵魏),说到了秦王稷的心坎里。秦王稷如获至宝,立刻重用范雎,拜为丞相,封应侯。
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非常成功,帮秦国一步步削弱邻国。但他这个人有个特点:权力欲强,心眼小,特别记仇,而且对掌握兵权的军事将领非常忌惮!在他看来,国家的最高权力核心,应该在丞相府和他这个丞相手中,而不是在前线那些打打杀杀、功高震主的将军们手里。

矛盾首先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穰侯魏冉。魏冉是秦王稷的亲舅舅,也是前丞相,权力很大,长期把持秦国军政(包括白起早期的崛起也得益于魏冉提拔),还喜欢带着兵跑老远去打仗(比如打齐国),劳民伤财。范雎说服秦王稷,将魏冉罢免,驱逐回了封地(前266年)。这标志着范雎彻底掌控了朝政大权。
罢免魏冉这件事,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白起和秦王稷之间激起了不易察觉的涟漪。
魏冉是白起的“伯乐”和政治盟友。白起的快速崛起,离不开穰侯魏冉的大力推荐和支持。两人不仅政治立场相近,私交也不错。范雎整倒了魏冉,这让白起很自然地站到了范雎的对立面,或者说,范雎天然地视白起为潜在威胁和魏冉的残余势力。

将相矛盾初露端倪。随着范雎在朝堂上说一不二,他和白起这位手握重兵、功勋卓著的军方首脑之间,必然会产生权力摩擦。一个是运筹帷幄、深居相府的谋略家,一个是大开大阖、常年在外的军事统帅。决策权、资源分配权,乃至在秦王稷心中的地位,都是两人暗中较劲的战场。
最重要的是:秦王稷的态度开始变化。罢免舅舅魏冉,显示出秦王稷集权决心非常强,不再容忍外戚权臣。他对范雎言听计从,说明他更倚仗“外客”(外来人才,如范雎、后来的蔡泽)来制衡国内的老贵族和军方势力。他对白起的依赖,开始掺杂了一丝丝不易察觉的警惕。毕竟,白起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威望太高了,手握的军队也太可怕了!

这种微妙的变化,起初还不明显。白起依然在打仗,依然在立功(比如长平之战就在魏冉被罢后不久爆发)。但在长平之战后处理赵国的问题上,这对君臣之间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公开的巨大分歧!
分歧之大,直接导致了两人关系的急剧恶化,也为白起的命运埋下了最致命的伏笔。
长平之战后,白起想干什么?他想趁热打铁,一鼓作气,直扑赵都邯郸!灭了赵国!
这想法有毛病吗?站在军事角度看,一点毛病没有!长平之战刚结束,赵国人被杀得魂飞魄散,国内一片哀嚎空虚,青壮年几乎死光,抵抗能力降到冰点。这时候白起带领士气正旺的秦军,拿下邯郸,灭掉赵国,对秦国统一天下,绝对是事半功倍、缩短时间的大好事!白起的建议是基于军事逻辑和战争经验的正确判断。

但是!秦王稷,尤其是他此时最倚重和信任的丞相范雎,是怎么想的?
范雎这人,除了权力欲强,还有个致命弱点:私心重,容易被收买,尤其害怕别人功劳超过他,影响他的地位。
赵国一看秦国要来灭国,知道硬扛不住,立刻派出了顶级说客,苏代(苏秦的兄弟或族人),带着重金贿赂范雎!苏代对范雎说了一番非常扎心的话:“范相国啊,您想过没有?如果白起真的灭了赵国,您猜他的功劳得多大?到时候封无可封,怕不是要位列三公之上?地位比您还高啊!”这话一捅,直戳范雎的心窝子!是啊!白起本来就牛,要是再灭了强大的赵国,那还有我范雎什么事?
于是,范雎立刻跑去劝秦王稷:大王!咱们打了长平这么惨烈的大仗,士兵需要休养!国库也消耗巨大啊。再说赵国现在愿意割地求和(割让六座城),咱们不如见好就收,让士兵喘口气,咱先把地盘拿到手稳扎稳打多好?这话听起来也有点道理(秦国确实也伤亡很大),符合秦王稷一向谨慎(或者说不想军队被一个将领长期带领)的作风。关键是,秦王稷此时对范雎的信任和依赖远高于白起。

结果是:秦王稷采纳了范雎的建议!下令白起,撤兵!不许打邯郸,接受赵国割地求和!
这道撤兵命令,对白起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眼看着一战定乾坤的历史机遇白白流失!白起内心那个郁闷、不甘、愤恨可想而知!他对范雎的怨恨达到了极点!同时,在他内心深处,对秦王稷做出这种“短视”决定的失望和不理解,也悄然滋生。
虽然白起遵从了王命撤军,但这件事就像一道深深的裂痕,刻在了他和秦王稷之间,也让他和丞相范雎彻底变成了水火不容的政敌。君王、权相、名将,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木,已经开始剧烈晃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崩塌。

抗命不从与君臣决裂
长平之战后撤兵的恶果,很快就显现了。赵国压根就没想真的割让那六座城!他们只不过是用“拖字诀”争取时间喘口气。秦王稷被狠狠耍了一把!这口气秦王稷哪里咽得下?而且他觉得,我现在休息够了,兵也补充了,你赵国还敢耍我?必须教训!于是,在赵国违约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59年)九月,秦王稷再次发动大军围攻赵都邯郸,准备一雪前耻,这次志在必得。
那么,派谁挂帅?秦王稷首先想到的还是那把最锋利的剑,白起。
按常理,白起之前就主张打邯郸,现在机会又来了,他该主动请缨、一雪前耻了吧?但事实恰恰相反!
秦王稷下令让白起挂帅,结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白起,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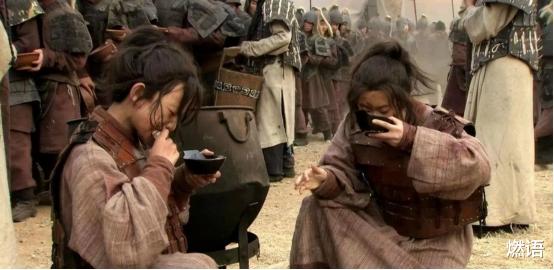
他拒绝的理由很充分:
战机已失。白起说:“长平之战后,赵国是吓破了胆,内部空虚到极点。那时候我们一鼓作气,邯郸唾手可得!可惜大王您听了别人的话,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意思是,当年让你们打,你们不打,非要等人家缓过气来再打?
局势已变,“现在呢?赵国缓了一年多,痛定思痛,国内同仇敌忾!对外,他们积极外交,跟齐国、魏国、楚国这些死对头都重新勾搭上了,寻求支援(‘国内实,外交成’)。我们这会儿去打,赵国为生存必然死拼到底,诸侯又怕我们灭赵后更强大,肯定会救赵!咱秦国这边,长平的损失还没完全补好呢。这样里应外合,咱秦军必败!这仗打不得!”
白起的分析,是基于战场实际情况的战略预判,非常冷静和专业。

但秦王稷这会儿可听不进去!他满脑子是被赵国戏弄的怒火,一雪前耻的决心!他觉得,只要派我大秦的精兵强将,上下一心,没有打不赢的仗!白起不肯去,那就是故意推脱!
好吧,大将不来,那就换人!秦王稷先派五大夫王陵领兵出征。结果王陵打邯郸打得磕磕绊绊,损失不小,吃了瘪(损兵折将)。
前线不顺的消息传回咸阳,秦王稷更急了!也更气了!他又一次强令白起挂帅!心想:我都派人试过水了,现在你总该去了吧?
但白起呢?干脆利落,再次拒绝!而且理由更充分了:
“我生病了!”(武安君称病)。
这就有点敏感了!你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要你出征你病了?是真病还是装病?在秦王稷和范雎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抗命”外加“装病怠工”!是对秦王命令的极大蔑视!

秦王稷这火“噌”地就上来了!他感觉自己作为君王的威严被严重挑战!他不信没人能打下邯郸!你白起不去?有的是人想去!
于是,秦王稷改派大将王龁(之前攻打上党的主将之一)去替换王陵,率领更多军队,继续猛攻邯郸!这一次秦国投入巨大兵力,围城围了好几个月(前258年),攻势非常猛烈。
结果呢?白起的预言不幸成真!
赵国人在国都危急存亡之际,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平原君赵胜等人散尽家财鼓励军民守城,组织敢死队不断出城反击骚扰秦军。 更重要的是,外交努力成功了!楚王(在毛遂自荐的劝说下)、魏王(信陵君窃符救赵),各自发大军救援邯郸!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两大名将领着联军杀到!
秦军被赵军拖在邯郸城下久攻不克,早已疲惫,现在又遭遇诸侯精锐联军内外夹击,顿时大败!损失极其惨重!这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在对外扩张战争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战略性挫败!

消息传到秦国国内,朝野震动!秦王稷的脸色可想而知有多难看!这不仅仅是一场败仗,更是对秦王稷决策的无情嘲讽,不听白起之言,果然大败亏输!这脸打得啪啪响!
在这种局面下,秦王稷对白起的不满、怨恨、猜忌达到了顶峰!
怨恨其“乌鸦嘴”,你怎么说什么就应验什么?这不显得我这个大王决策无比愚蠢吗?
怨恨其“见死不救”,你明明知道这么打会输,为什么不挺身而出?看着秦国吃败仗,看着我的军队死伤惨重?你心里还有没有秦国?有没有我这个大王?
怀疑其忠诚:仗打成这样,你不但事前预言,还拒不出战,你是不是心存怨恨?是不是觉得我不用你就活该失败?是不是故意想看我笑话?甚至……你白起是不是觉得你的军事才能比我这大王还高明?高明到可以不听王命了?
秦王稷这时候对白起,已经不是失望,而是带着一种屈辱、愤怒交织的强烈负面情绪! 白起之前的功勋和此刻的“正确”,在秦王稷看来,反而变成了对他王权的巨大讽刺和威胁!两人的君臣关系,至此已名存实亡,裂痕深不可填。

积怨爆发
邯郸惨败后,秦国国内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中。秦王稷需要发泄怒火,更需要替罪羊。前线将领王龁等人固然有责任,但在秦王稷心中,真正“罪大恶极”的人是白起!
范雎的致命一击:作为与白起势同水火的丞相,范雎深知秦王稷此时对白起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顶点。他立刻抓住机会“上眼药”,煽风点火:“武安君白起,早就预见到会失败,但他就是不肯听从王命去邯郸参战。你看,这证明他内心对大王早就不满了!这种怨望之心太可怕了!这简直是故意拆大王的台啊!” 范雎这番话,直接把白起的“战略分析”和“拒不出征”定性为对秦王稷的“心怀怨望”(怨恨不满)甚至是对君命的故意背叛!这是最能让君王产生杀心的罪名!

秦王稷的决断:驱逐出咸阳!听完范雎的添油加醋,本来就怒火中烧、自尊心极度受伤的秦王稷彻底爆发了!他立刻下令:武安君白起,心怀怨望,目无君王,不能再留在都城了!必须即刻迁出咸阳,贬到阴密(今甘肃灵台县附近的一个小地方)!让他去那边待着反省!白起在咸阳的府邸、荣耀、地位,顷刻间化为乌有。
最后的“冒犯”:滞留咸阳与君臣反目。被贬的白起,心中恐怕也满是悲愤和不平。或许是身体真的不适,或许是心有不甘、行动迟缓,也或许是对秦王的处置彻底绝望,他没能立刻离开咸阳!还在路上耽搁(《史记》记载‘未能行’)。这最后的拖延,彻底点燃了秦王稷内心的最后一丝理智!
在秦王稷看来:你白起当初“装病”拒不出征!
现在让你滚蛋,你又拖着不走!你这不是“病好了能走了,但就是不走”吗?

这叫什么?赤裸裸的蔑视王权!公然对抗君王!
这简直是公然挑战我的底线!我这大王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
秦王稷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对白起仅存的一点点君臣情谊荡然无存,只剩下滔天的怒火和被冒犯的杀机!此时任何人的求情都没用了!
秦王稷亲自下场(或再次通过范雎)痛骂白起:“武安君!你好大的架子啊!我把你赶出咸阳,你居然还赖着不走?!你这是在干什么?对我心怀不满到现在,还装病拖延?!你这完全是反心不死!反相毕露!”(原文意译,用词更狠)
骂完之后,秦王稷做出了最终裁决:白起不是“称病”吗?不是“心怀怨望”吗?不是想看我笑话、对抗王命吗?那好,这个“心病”,本王亲自来帮你“治”!

公元前257年十一月,秦昭襄王派使者,快马追上已经离开咸阳但仍在路途中的白起,送给他一件东西,秦王的佩剑。
赐剑的意思,不言自明:“白起,你自己了断吧。”
权力、恐惧与功高的诅咒
走到赐死这一步,秦王稷心中真的没有犹豫吗?恐怕未必。但促使他必须这么做的深层原因,远不止“你让我丢脸了”那么简单。这是一场权力、性格、现实与历史交织的必然悲剧。
最直接的导火索:王权被挑战的愤怒。“三召不起”(两次拒绝挂帅,最后一次被贬后拖延不行),在白起可能是基于理性、身体或情绪的复杂原因,但在秦王稷和那个时代的君王视角下,这是对君王绝对权威的赤裸裸的挑衅和背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是“君要臣打,臣敢说不打”?

尤其是最后迁延不行,更被视为“拥兵(自身威望就是无形的兵)自重”的潜在威胁信号。秦王稷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处死,来重塑王权的至高无上性,警示所有臣子:没有人,哪怕是白起,可以挑战王权!
权力三角失衡下的必然:将相水火,王恐失衡。秦国朝堂当时形成了危险的三角关系:
白起:军功顶点,军方领袖,士兵心中的“战神”,威望极高。
范雎:相权独揽,深受宠信,主抓政治外交,但与军方(白起)结下死仇。
秦王稷:最高掌权者,依赖丞相范雎巩固王权、对抗旧贵族(如魏冉),但也需要将军白起开疆拓土。范雎和白起这对将相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将秦王稷逼到了必须“二选一”的墙角。

邯郸之败后,秦王稷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确性”,必须掩盖自己决策失误的责任。他不能杀自己倚重的丞相范雎(否则等于承认自己被范雎忽悠了),更不能承认是自己不听良言导致失败(打自己脸),那么,把所有责任推到拒不配合的白起身上,就是唯一的选择。
白起成了秦王稷维护自身“明君”形象和“王权尊严”的必须牺牲品。范雎的谗言只是加速剂,核心在于秦王稷需要这样一个替罪羊。
最隐秘的恐惧:功高震主与无法掌控的“武器”。白起的功劳实在太大,太耀眼了!他几乎以一人之力扫平了六国精锐,杀人无数(伊阙24万、长平40万,功高盖世),在军中威望之高,无人能及。
秦王稷内心深处,不可能对这样一位掌握着帝国几乎全部精锐武装力量的将军毫无顾忌。尤其是当白起表现出不驯服(拒绝出征)时,这种忌惮瞬间转化为恐惧:你连我的命令都敢不听?是不是觉得你功劳大到可以独立了?是不是有朝一日,你会调转兵锋?这种“功高震主”带来的不安全感,在古代君王心中几乎是本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赵国暂时打不垮,但白起这把已经不太听话甚至可能伤主(威胁王权)的“绝世名弓”,在秦王稷看来,已经失去了价值,甚至成了隐患,必须毁掉!

性格的悲剧底色:刚极易折与多疑寡恩。白起性格刚直,不谙政治权术。 他一生致力于打仗,认为军事高于政治,甚至以自己的军事才能“正确性”来否定君王的决策。这种性格在顺境中是优点,在逆境或与君王意志冲突时,就成了致命的弱点。他不懂“功成身退”的智慧,也不会如范雎般阿谀奉承。而秦王稷,在长期掌权中变得越发多疑、自负和寡恩。他晚年猜忌心极重(驱逐舅舅魏冉),不容忍任何挑战。长平撤兵后他意识到错误但无法承认,更强化了他的固执。当白起这个曾经的“国之利器”屡次不按其意愿行事时,秦王稷的多疑将其定义为“失控”,自负将其视为“冒犯”,寡恩则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极端的手段“毁灭”。

白起接到秦王赐剑那一刻,心中是何等悲凉?他曾为秦国开疆拓土立下不世功勋,现在却被自己效忠的君王赐死。他走到杜邮(今陕西咸阳东),仰望苍天,长叹一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我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竟落得如此下场?)随即引剑自刎。
一代“战神”,血染杜邮。他的死,并非败于外敌,而是亡于内部的倾轧与君王冰冷的猜忌。秦国失去了一代军神,但历史证明,秦国制度强大的运转能力和后来王翦父子的“自污保身术”,最终仍吞并了六国。白起的悲剧,是个人才能(军事天才)与政治格局(不懂权变)、绝对王权(君主的猜疑)与将相冲突多重奏下的必然哀歌。
功勋卓著既是荣耀的桂冠,也是悬顶的利剑;君臣同心是霸业的基石,而猜忌则是倾塌的裂缝。武安君白起的结局,是古代君臣关系极限张力下,那把名为权力的双刃剑,最终落下的一抹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