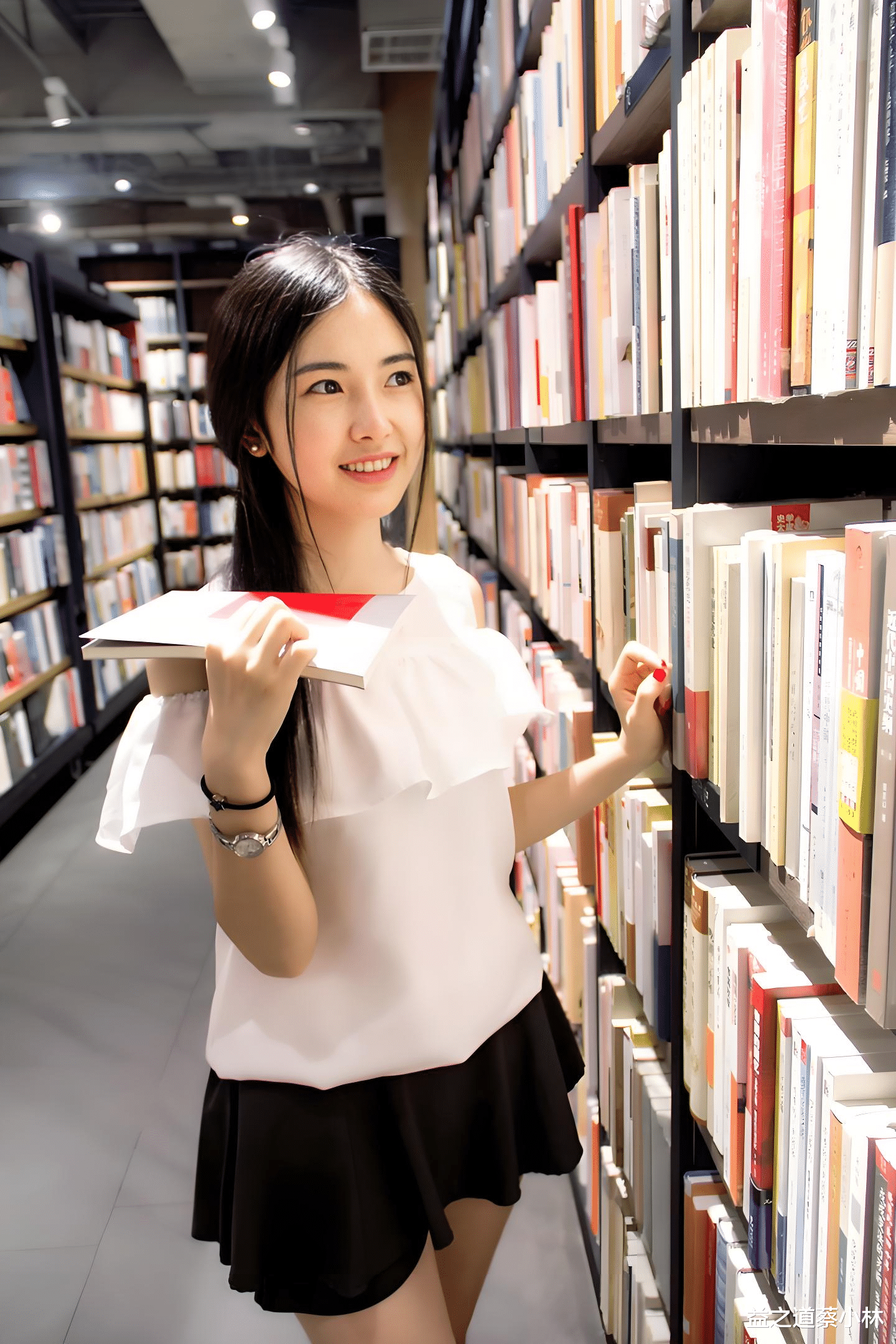《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编物权,第三分编用益物权,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百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条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和登记的规定。
一、历史由来《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条源于《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略有修改。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将发证机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修改为“登记机构”,将所发证书统称为“权属证书”,并将第二款修改为“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权属证书,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第一百二十八条将登记机构应当发放的证书明确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并将第二款修改为“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规范目的或功能物权的设立规范是物权变动规范的重要内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何时设定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条第一款即旨在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的时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条第一款继承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与《物权法》的规定,以便适应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运行的实际状况。
《民法典》物权编确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规则是有重大意义的,它为判定农村土地承包权的设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承包经营权设定问题提供了规范。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登记造册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可以进一步实现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公示与确认,也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
三、规范内容(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本条第一款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时间进行了规定。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旦生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设定。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二)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承包土地的用途;(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六)违约责任。”考虑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以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目的的物权合同性质以及其内容的复杂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换言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虽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必然包含了一项设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以承包合同为依据设定,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带有债权性质。由于在最初的承包过程中,农村的改革并没有完全到位,各种公法上的内容如乡统筹的缴纳等都与土地承包合同关联了起来,土地承包合同成为村委会、乡镇政府控制村民,实现对村民的管理的工具。在目前农业税已经取消,乡统筹与村提留也已经基本取消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合同正在逐渐恢复其民法属性。
按照《民法典》第二百零八条确定的公示原则以及第二百零九条确立的不动产物权原则上应当在登记时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本应当在登记时设立。但是何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不经登记而设立?理由如下:
第一,《民法典》物权编作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规则是对历史上存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的经验总结。
对于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而言,经过第一轮承包与第二轮承包,大部分耕地上已经普遍设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民法典》首先总结了历史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形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规则。
历史地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早已存在于大部分耕地之上,而且基本上是通过承包合同设立的,没有经过登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之初,由于农村土地登记机关未真正地建立起来,不可能要求其普遍进行登记。即使是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普遍设立之后才颁布,在时间序列上总结历史经验的因素超过面向未来的因素。在集体不能再大规模调整承包地的情况下,农村承包经营权未来只能在有限的农村耕地与未承包的部分林地上设定。
第二,我国乡村依然是熟人社会,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之间互相熟悉,而且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需要履行必要的程序,农村土地承包之程序的完成也起到了一定公示效果。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充分参与这一进程并相互熟悉,承包地的地块为村民所熟知,这也会起到一定公示之效果。
第三,我国农村土地登记制度未能完全有效建立并运行。
在农村土地登记机关与登记制度未全面有效建立的情况下,要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合同生效时设定是基本合适的,即使要求通过登记而设定承包经营权也将无法施行。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颁证及其登记,滞后于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需要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完成对农村土地的全面初次登记。
当发包方与多个承包方签订多个承包合同并分别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多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就产生了。为了解决实践中发生的因设定而产生的多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冲突,200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条建立了一个包括登记优先原则、生效优先原则与先行合法占有、使用优先原则在内的冲突处理规则。
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
这一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中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完全符合物权法的法理。
其一,同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当同时存在于一宗土地之上,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另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排斥效果的出现,动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效力。
其二,本条第一款仅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并未规定已经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因此,按照本条规定,按时间顺序第一次设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就已经设立,并将持续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排他效力会使其他与其具有相同品质、权能并须占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不可能再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具有农地权利再次初始配置的效力。
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登记机构发证与登记的效力仅是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具有对抗效力,登记机构的登记与所发的权属证书仅是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并对其进行保护的手段。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登记不同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互换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互换登记会使相关权利人的权利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解决实践中发生的因设定而引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冲突,除迅速对农民已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外,还需要继续完善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规则。未来我国需要继续贯彻公示原则,建立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登记时设立的规则。如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登记时设立,则一旦有一个承包经营权在农村土地上设立,就排除了其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的可能性,从而有效避免这类纠纷的发生。
(二)登记机构发放证书,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义务
本条第二款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能力作出了规定,该条规定:“下列不动产权利,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二)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三)森林、林木所有权;(四)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五)建设用地使用权;(六)宅基地使用权;(七)海域使用权;(八)地役权;(九)抵押权;(十)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
第七条对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了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由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分别办理。不能分别办理的,由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协商办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指定办理。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国务院批准项目用海、用岛,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等不动产登记,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农业部2015年颁布的《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提出,“由县级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作为今后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基础依据”,“为与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衔接,今后可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承包农户可以自愿申请、免费换取与不动产统一登记相衔接的证书”。
2018年修正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登记机构除按规定收取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2018年年底,全国共有2838个县(市、区)和开发区开展农村承包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2亿多农户,确权14.8亿亩承包地,基本完成了全国农村承包地的确权颁证工作。

(一)关于登记的效力问题
关于物权登记的效力,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未经登记,不生效力。二是登记是当事人在物权变动后未经登记,在当事人之间也可有效成立,但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采取了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只需发包方和承包方达成意思表示上的一致,法律不要求该项物权的设立以登记为要件。
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一是承包方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互熟悉,承包的地块人所共知,能够起到相应的公示作用。二是承包证书的发放和登记造册,往往滞后于承包合同的签订,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户的承包经营权,登记造册是作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的程序,如果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传统的物权法原理,必然会损害广大农民的利益。
需要承认的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采用意思主义是否妥当,学术界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而发生互换、转让等情况时“不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模式,切合我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之情况和采行登记要件主义的实际困难,颇为灵活机动且有创新,具有“中国特色”,值得赞同。
也有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制度不严密,存在前后矛盾的立法主张。《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不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立法对承包经营权的变更采用登记对抗主义。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及《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同时又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从该规定推出承包经营权的取得采用的是无需登记的债权合意主义,这就产生了矛盾。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其流转的前提,而承包经营权的变更是流转的结果。立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和流转设置了不同的登记原则,违背了物权法理中物权设立与物权变更应当一致的原则。
(二)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承包农村土地的主体,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和任何理由,非法剥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和任何理由阻挠、干扰、限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权利的实现。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各种原因实际未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其享有承包集体土地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否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解决。”
主要理由是:一方面,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是该承包人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应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而实践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问题在很多方面涉及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如果人民法院将这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可能会涉及农村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通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请求法院判决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因此,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宜将其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而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