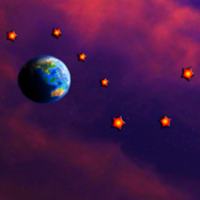文丨曹旭

我不是在黑洞中摸索,中学时代的少年是畏惧黑洞的,羡慕那些同学在放学之后在黑洞中的探险。80年代城市的防空洞,多以闲置失修。许昌市第一中学操场西沿有一个洞口,我们下去过,好像有几千米远,实则的尽头,只有百米之去便可以看到光亮了,那是北教学楼的底层一角,由铁栅栏割断了去向。
更远的地方有同学去过,不知他们如何绕过那些铁篱,摸索着从市一中的北关支点,到达南关的灯塔口,老城的最南端,相距足有四千余米。途中火炬燃烧,洼地烂泥,坍塌砖石,折弯斗转,那是多么奇妙而遐思的壮举,在黑暗里的探险。而少年的自己则是害怕的,不敢涉足的,不知为什么。
我是颇为喜爱探险的,甚至觉得还有什么险要之峰之谷之洞能够去寻找,去进入去长视去久听,看见不见,听到不听。我指的是我笨拙的剑,我指向哪里?哪里可识而豁达。见病灶而通开堵塞的血脉?我光照所及的黑暗边沿及其间的模糊地带与沼泽地带。
《读书》的这篇文章所论,正是这里填海造岛之边沿,即《生命的隐喻与医学的罩门》。其中“膏肓之间”,也可以谓之腠理之域,一种无法抵达的绝对空间,正是我长期或者已是生命所向往的欲望或蠕动。睁开眼,启动耳,伸出手,迈起步,向无知而可知处去,向黑暗和光明间进。当见到“膏肓之间,”我看到灰暗的那丝光亮,看到了这篇文章,知道这是另一洞打开的长穴,原身本质在其中之中,竟是如此纬度和级层。

这也是我常常忧惧其一的,唯恐失去探险探索的欲望,或者说更为担心的是失去那种探索的能力。这种心思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听力、视力、触觉一级的超级心力。这与曾经的一篇文章是一致的吧:《我还能看这个世界吗》《一个写手,唯恐失去的是事物的敏感力》原句忘了,大抵如是。
而当下,我触摸到这冰冷春寒中的温暖,关于生死之间,那冥河的摆渡人,这端芦花摇曳,沙沙低唱,微波清扬,舟水滴桨;彼岸浓雾弥漫,影影绰绰,无声无息,昏暗无着。我生活在这个世上啊,一桨在此岸,一眸在那端。生命如此美好,膏肓之间,无法抵达的绝对之所;无法抵达的抵达,绝对之所的相对之点。我的坐标已定,却又不断有新的迁移,有新的标记。
如此说来,少年时期的畏惧探险,并不是我原力不逮,初衷本意,因为童年之时,三四岁之幼,黑暗不惧,而可独自外室安睡,不惧黑暗而绳系小腰,被母亲下放到红薯窖里,再无甚光线里摸索贮粮,一块儿一块儿红薯搬到荆篮里,由母亲拉上去,并不畏惧黑暗的那种探险,那种任务。
因此,初中一年级的那段畏惧经历,是一个刚刚进城上学孩子的自卑,自卑而偏执的心理情绪。岁月漫漶,只是运气顺达开畅,冥冥之中,自己克服了那种心理情绪,正如我思维之触,思想之觉,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同化异化俗化,而改变初心原意,失去敏感的力;冥河彼岸,无所畏惧。

☆ 作者简介:曹旭,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笔名陈草旭变,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小说见散文在线、红袖添香、古榕树下、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合著有人物传记《那年的烛光》。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