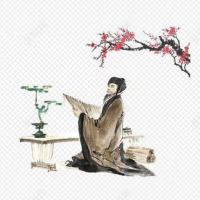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下,户籍制度表现出等级性、世袭性和功能多元化的特点。户等划分在社会制度的构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级制度的集中反映。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分封制瓦解,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逐渐建立,户籍制度开始萌芽。

战国时期贵族政治的残留仍十分强大,社之户口所记录的人名仍以家长或男丁为主。商鞅变法之前,赋役征收的对象仍然是宗族家长。秦献公时期,出现了显著的爵位等级体系、户等划分,这两者结合构成了名田制度。
在先秦时期,血缘关系在等级划分中发挥着主导地位,户籍制度也受到血缘等级身份的影响。即使在“士阶层”崛起之后,宗族血缘关系仍占据着等级排序的主导地位。但在商鞅变法之后,户籍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商鞅进行的两次变法,特别是关于户籍制度的变革,为我国后来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基本规模。变法对先秦以来旧的贵族血缘身份制进行了消除,建立了一个以个体小家庭制为核心的户籍管理模式。

《晋书·刘超传》记载:“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赀。”
具体来说,商鞅将民划分为五十家或五保,让其相互维护、监督,同时建立了县级行政管理机构,自上而下对户籍信息进行分类、统计、管理。除此之外,商鞅还颁布了让“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削弱了血缘等级身份在户籍等级划分中的影响。
商鞅变法对我国的户籍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建立了一个以个体小家庭制为核心的户籍管理模式。商鞅将民划分为五十家或五保,并建立县级行政管理机构,对户籍信息进行分类、统计、管理。
同时,商鞅重新确立了一种新的户籍等级划分标准,即“军功等级”制。按照这种制度,有军功者可以以爵位的高低来划分户籍等级。

此外,商鞅实行的是以农为经济基础的名田制度,商人的地位较低,可能会受到政府的打压。秦代实行严苛的法律,对军功爵制和名田宅制维护有力,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户籍等级划分。在此时期,“富比邦君”的现象并不普遍,只有那些有功于国的人才能高爵。
在古代中国,爵位等级是一个重要的身份标识。根据历史文献,可以看出爵位等级对于家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有着明显的影响。在古代,爵位高低往往与家庭所持有的田亩和宅地的面积相关。

爵高者的家庭所占田亩和宅地数量相对较多,爵低者则相对较少。此外,爵位还对生活中的优待产生影响,例如表现在传食待遇、政府赐衣物和赐酒食等方面的区别。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卿一级的爵位共有九个等级,包括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以及大庶长等等。此外,爵位高低还涉及到在法律和政治上的特权。
爵位等级对于家庭身份、田宅持有量、生活待遇、法律政治特权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影响。卿一级的爵位共有九个等级,包括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和大庶长等。
爵高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享有更多的优惠待遇,比如不用缴纳某些税收,享有军赋等特权。等级越高的爵位,享有的待遇和特权也越多。

在授田方面,立户时间较早的家户会优先授予土地,但在立户时间相同的情况下,爵位高低也是授田的重要依据。此外,在官府对百姓比地为伍的规定中,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很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总的来说,爵位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爵位的等级和授予土地的数量、政治地位、税收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秦汉“比地为伍”到汉朝“关内侯”,爵位的特权越来越受到限制,对于家户授田的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在秦代,户等划分以军功爵级为依据,以有功者行田宅的原则来授予土地。然而到了文景后期,爵制和土地买卖的形势不断变化,户等的评定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西汉中期以后,户等的划分逐渐转为以大家、中家、小家为代表的“财产等级”行列。爵位等级的高低已经不能适用于授田标准,土地兼并问题的出现使得“素封”之家得到了发展。商鞅变法以来,以军功爵制为参照的户等的划分难以维系,这就需要一种新的评定标准。
我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形成时期大概是在魏晋时期之后,但实际上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户等划分的概念。在秦汉时期,户等划分是依据爵位和名田制来授予土地的,而到了汉代之后,户等的划分逐渐依赖于财产状况来评定。

这一变化也影响到了国家赋税征收的方式,即从以爵位为主要依据转变为以户赀为评定标准。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户等制度也经历了多次变革,从“户赋”到“以訾征赋”,再到“户品出钱”,这些变化都反映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变。
《后汉书·刘虞传》记载:“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馀,以给足之。”
学界对于秦汉时期户赋的征收对象和性质等问题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户赋是一种单独的税目,只针对于卿以下的人,征收额度相同;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户赋是一户内所需要缴纳的所有赋税的总和。

根据新出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中的资料,可以解决此争议。据《金布律》规定,出户赋者对象自大庶长(司寇、隐官群体)以下算起,此与秦汉时期户赋征收对象的规定相符。同时,大家所承担的取决于爵位等级的“户刍”也与户赋无直接关联。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秦汉时期户赋的征收对象是卿以下的人,而户赋是一种单独的税目,而非一户内缴纳的所有赋税的总和。据史料证明,秦至汉初户赋征收对象为卿以下爵位中的立户者,是一种单独的税目,每年十月和五月各征收一次。
征收额度不仅限于钱、刍,还可以纳布、茧等实物,甚至可能因地制宜,容有折算的空间。原来认为户刍不同于户赋、户赋仅指茧、丝等说法是错误的,户刍实际上是户赋的一部分。秦至汉初的户赋、刍稾税的征收,其划分深受爵制的影响。

通过严格执行商鞅变法以来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即“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便利”,户赋、刍稾税的征收成为国家摊派给各个爵位中的立户者的赋役。
在汉代以后,社会等级出现了破坏,爵位制度逐渐式微,名田制度也逐渐衰败。因此,财富成为了一个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豪强地主、工商业主通过各种手段致富,处于大家、中家、小家等不同的等级。
大家的家赀巨大,可能达到数亿;中家的家赀的标准在十万以上;小家的家赀则一般在四万以下。此外,还存在一个称为“下户”的户等级,这些人的家赀大多不满万钱,需要政府的赈济。

虽然学者对于汉代家赀标准的看法存在争议,但史料的时间跨度之大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在两汉四百年的时间跨度中,户等的家赀标准发生了变化。在汉代,户等的划分与赋税征收密切相关。家赀成为了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大家、中家、小家等不同的等级根据财富的多少进行区分。
三、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在赋税征收方面,汉代采用“以訾征赋”的方式,即按家赀多寡征收赋税。但是,赋役的摊派虽然以家赀为依据,但是汉代户等的阶层差异严重影响到赋役政策的贯彻施行。
豪强大家往往隐匿流亡之民,官吏不敢苛责而将逃欠的赋税转嫁于小民,小民不堪重负,越发逃亡隐匿,最终负担落于中家,后逃亡者为先逃亡者分摊赋役,彼此仿效,更加重了流亡。

在汉代,户等的划分与赋税征收息息相关。随着按赀征税的常态化,其弊端逐渐暴露,如隐匿家訾、偏袒造假等形成的“强民隐藏,弱民兼赋”问题。曹魏及东吴政权分别进行了赋税调整,将赋税征收的依据从户赀向户品转变。
《续汉书·百官志》记载:“乡置有秩、三老、游徼。”
孙吴户税制度根据旧标准(即所谓“故户”)分为三种等级收钱,而针对赋税征收的弊端,孙吴政府将赋税征收的依据从户赀向户品转变,分上品、中品、下品以及赤贫的“下品之下”四个等级。

吴简中的一些记录显示,吴简中的户分九品的说法并不成立。吴简中“下品之下不任调”意为这些贫困户无力承担各种赋税,由政府安排其从事“给吏”“给卒”等特殊徭役。虽然孙吴与曹魏调整赋税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调整力度存在差异。孙吴时期仍沿用了汉代的恤民手段,即使是贫困户也进行免除和减免赋税。
在秦至汉初,户等的划分与“名田制”相结合,形成了明显的“爵位等级”特色。然而,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名田制”受到破坏,社会贫富分化导致赋役征派、等级划分只能通过“平訾”的过程有差异的对待,户等的划分进入了“财产等级”阶段。
为了适应这一转变,秦汉赋税也出现了变化,由原先的“户赋”和“以訾征赋”转向“户品出钱”。这是一种按照户等标准向全民征收的专项费用。虽然这三种税目都是按户为单位征收,但它们的性质和对象各不相同。

在西汉后期,爵制和名田制的衰落,以及赋税征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得“以訾征赋”这一财产税逐渐确立。汉末时期,“每岁调发,使本县平赀”已成为调役征发的常见手段。
然而,由于此种税收方式存在隐匿家訾、逃亡、偏袒造假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曹魏及东吴政权纷纷对赋税进行调整以应对这些问题,虽然两者的调整方向相同,但调整力度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在秦至汉初,户等的划分与“名田制”相结合,形成了“爵位等级”特色。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名田制”破坏,户等的划分进入“财产等级”阶段。赋税也由“户赋”和“以訾征赋”转向“户品出钱”。汉末时期,“以訾征赋”逐渐确立,但仍然存在问题。
参考文献:《汉书》
《里耶秦简》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