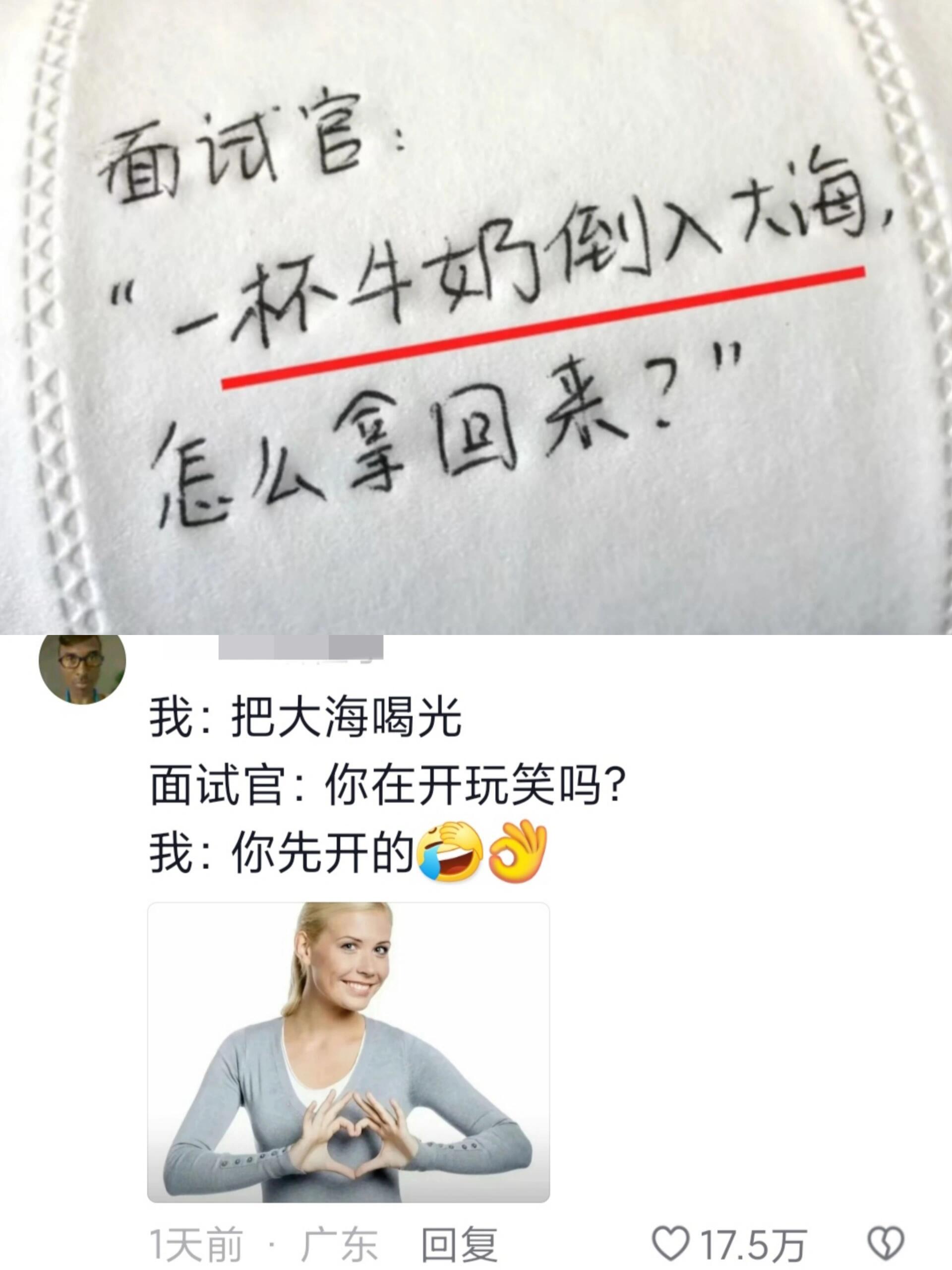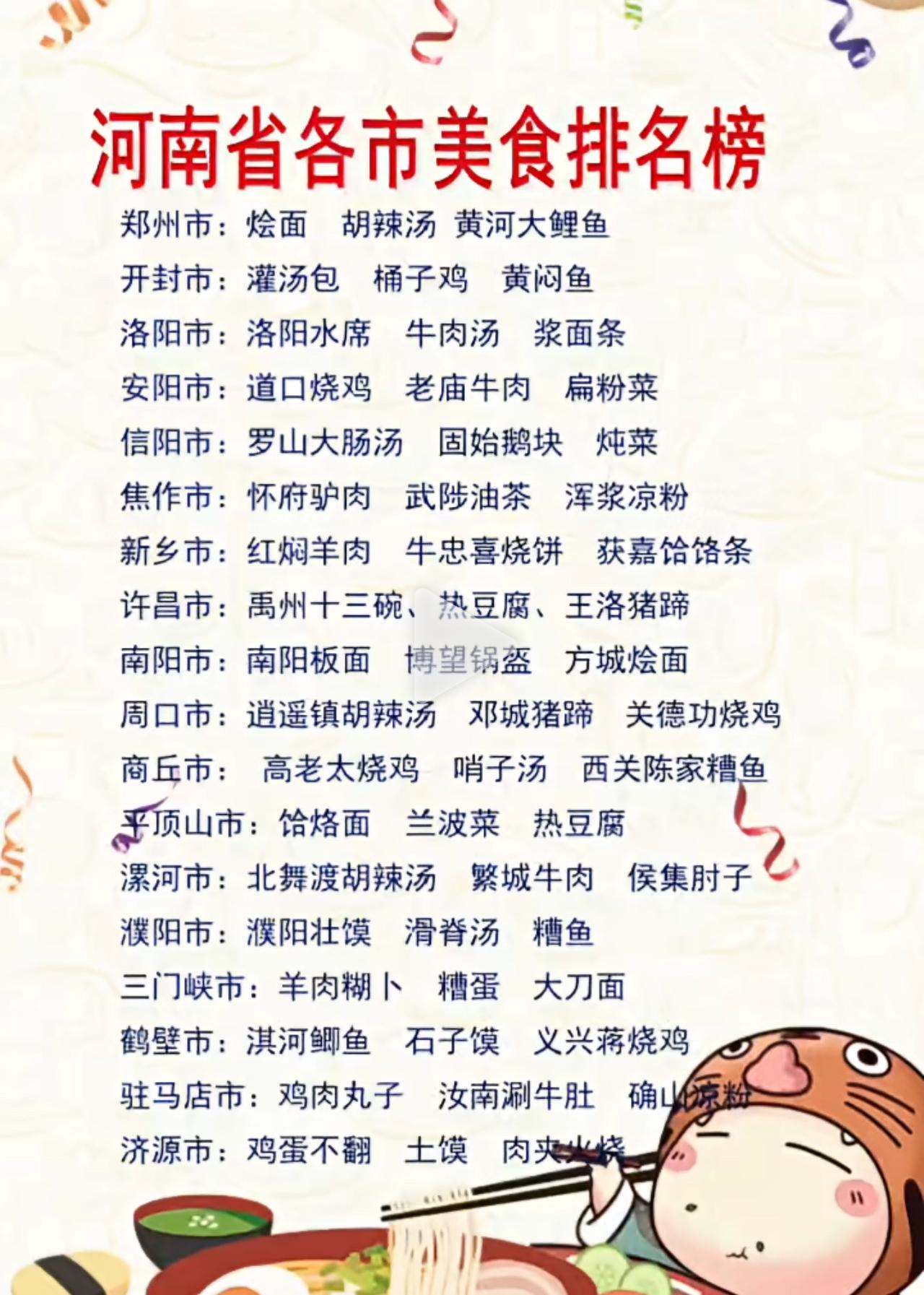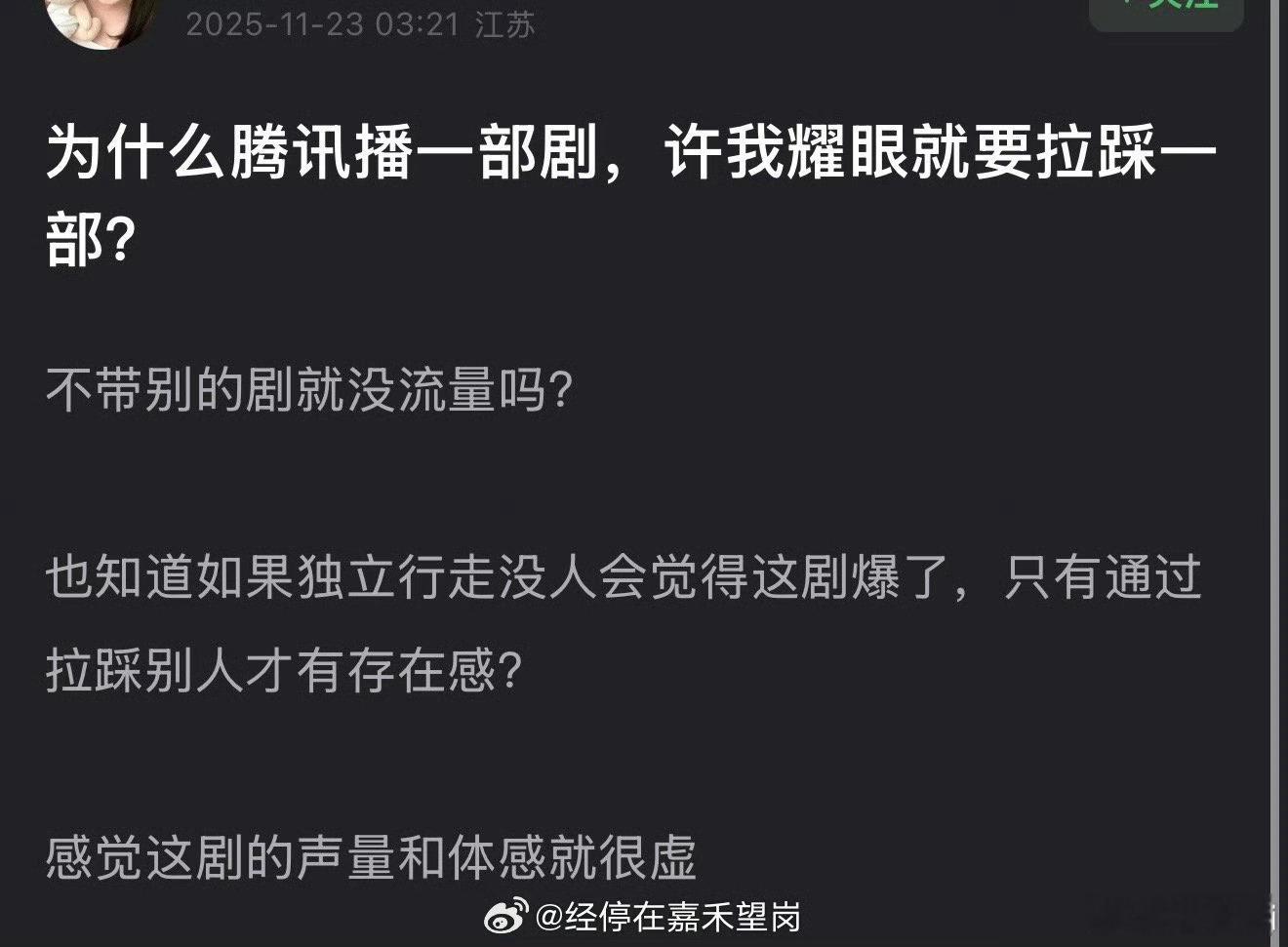西周时巴人在这里扎营,国号巴,仗着山险水恶,把青铜剑磨得锃亮,
硬是守到秦惠文王派张仪来拆了都城。
后来设巴郡,归益州,宋元时成了抗金抗蒙的堡垒,石头城墙上至今留着箭簇凿的坑,风一吹就呜呜响,像老辈人叹苦经。

码头是重庆的根,千百年来商船挤得像沙丁鱼,纤夫光着脊梁把长江拉得打颤。
明清时湖广填四川,挑夫、匠人、生意人扎进来,青石板路被踩得油光水滑。
火锅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码头劳工把边角肉、下水扔锅里,辣汤滚着牛油,驱湿暖身,
一吃就是几百年,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滋味。

川剧的变脸、吐火,跟山城的性子一样烈。
巴人尚武,民风耿直,爬坡上坎的日子磨出了韧劲。
老城墙拆了又修,吊脚楼让位于高楼,
但江边的茶馆还在,盖碗茶泡着茉莉,老头们摆着张献忠江口沉银、邹容办报的旧事,声音混着江水声,越飘越远。
三千年风雨刮过,重庆没被磨软。
江水还在流,火锅还在滚,山里人的硬气还在,这就是活着的滋味,沉在历史的泥沙里,越品越厚重。

这口“脆”从光绪二十四年来。
1898年,涪陵邱家院子的青菜头堆成山,腌菜师傅邓炳成试着用压豆腐的木箱榨除盐水,
拌上花椒辣椒,装坛密封,
这“榨”出来的菜,脆得“嘎吱”响,鲜得掉眉毛。
邱寿安嗅到商机,首批80坛榨菜顺长江卖到宜昌,就此叩开商品化大门,
与德国酸甜甘蓝、法国酸黄瓜并称“世界三大名腌菜”。
这菜,非遗名录里藏着硬核功夫:
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
传承“三腌三榨”古法,青菜头要选“茎瘤芥”,经风干、修剪、三次腌制,坛装发酵百日,咸鲜微辣直窜喉咙。
如今涪陵人还说“榨菜做得好,堂客有教养”,春节煮榨菜鱼,图个“有滋有味”的好彩头。

根扎在明朝崇祯年间的烟火里。
传说崔氏女子为躲战乱,将蒸好的黄豆藏在柴草下,半月后竟生出毛霉,加盐封坛,次年开坛时黑亮油润、清香回甜,成了"巴适得板"的救荒宝贝。
这味儿从跳石河小饭馆飘出,传遍永川,至今已有近四百年,
2008年它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成了"活着的古董"。
它选料严苛,非本地非转基因黄豆不用;
制曲要等毛霉爬满豆身,发酵需一年光阴,方得"光亮油黑、滋润散籽"的姿态。
咬一口,咸香裹着回甜在舌尖化开,化渣不粘牙,配回锅肉、豆豉鱼,能鲜掉眉毛。
老辈子说,这豆豉里藏着永川的风土,
狗屎长毛时投料,雨水节气收坛,全是老祖宗摸出的自然道道。

得从明末清初的嘉陵江码头说起。
船工纤夫们守着瓦罐,把辣椒花椒往汤里一撒,牛毛肚、猪黄喉往沸水里一涮,
这锅“粗放餐”后来成了“闹龙宫”的雏形。
清末南纪门宰房街的牛杂碎,被船夫马大爷拾掇进锅,竟煮出了“毛肚火锅”的魂儿。
2019年6月,重庆火锅传统制作技艺正式入选市级非遗。
它的厉害在“辣得跳脚,香得勾魂”,
牛油打底,辣椒花椒轰轰烈烈,毛肚七上八下涮得脆生,鸭肠翻卷如波浪,蘸着香油蒜泥,一口下去“巴适得板”!
这锅汤里,藏着巴渝人“热辣直爽”的脾气,也藏着“现烫现吃”的烟火气,比那些花里胡哨的菜式,更懂重庆人的胃和心。
啷个?走,烫火锅去!

得从清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说起。
那时潮汕客家人揣着卤鹅手艺扎进荣昌,
撞上本地皮薄肉嫩的白鹅,再融进川卤的麻辣劲儿,就像老茶馆里碰出的火花,
咸鲜里裹着五香回甘,耙软得筷子一搛就脱骨,
一口下去,三百年客家迁徙史、巴蜀烟火气全在舌尖打转。
光绪年间,荣昌白鹅已列县志“重要特产”。
2011年,它正式入选重庆市级非遗。
卤鹅皮薄如蝉翼,咬开是肥美肉芯,蘸水一裹,辣香、麻香、卤香在嘴里“打旋儿”。
当地人喊它“鹅儿肉”,街头巷尾飘着“卤鹅,卤鹅,盯一眼走不脱!”的吆喝。

清同治年间,白市驿的宰牛师傅受成都“卞一芳”饭馆启发,与烧腊匠人创制出这口咸香。
更早可溯至1643年张献忠入川时,穷人送鸭途中用盐抹、竹片绷撑防腐,张献忠尝后赞“干绷”板鸭。
这歇后语至今在重庆坊间流传,道尽“打肿脸充胖子”的烟火智慧。
抗战时,它随白市驿机场通航远销欧美,成为陪都宴饮必备,
1959年国营化生产后更登《重庆菜谱》,
1982年连获国家商业部优质奖,2011年4月列入市级非遗,任明贵为传承人。
这鸭形如蒲扇,金黄油亮,皮脂厚润。咬一口,
烟熏香混着20余味香辛料的醇厚直钻鼻腔,肉质鲜嫩如玫瑰红,
蒸炒皆宜,蒸则软糯回甜,炒则香辣交织,连汤都鲜得掉眉。

生在光绪二十一年的合川城,
1895年“祥云斋”糖果铺创制甜桃片,后经“同德福”改良,
用三江交汇处产的优质糯米、核桃仁、川白糖、陈酿玫瑰,经近20道工序手工精制。
张森楷举人曾带它上北京,赠师友,自此“合川味道”飘向四方。
1926年更在巴拿马博览会夺金,人称“世界第一桃片”。
2007年它列重庆市级非遗,2009年又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这糕点薄如蝉翼,撕开似“桥牌”卷不烂,点火即燃,入口化渣。
甜口香浓绵软,椒盐口酥脆微麻,玫瑰香混着桃仁香,直钻鼻腔。
老合川人常说:“吃桃片要掰成‘莲花瓣’,配杯老荫茶才安逸!”
如今传承人余晓华蒙眼切片,一刀一片薄过纸,每斤250片,手艺绝了!

藏在1917年的斑竹巷里。
陈汉卿、陈丽泉两兄弟嫌炒米糖“寡淡”,蹲在灶前把红糖换白糖,加桃仁花生,又试了油酥新法,愣是熬出那股子“巴适得板”的香脆。
1924年,油酥米花糖出世,从此成了江津人的“年味符号”,
过年走亲戚,提一包米花糖,比说“新年好”还实在。
2011年,这口甜脆被列进重庆非遗,靠的是十道工序的讲究:
选米要宜宾大糯米,蒸米得泡够十小时,阴米晾干后,和着饴糖、芝麻在锅里“翻跟头”,最后切块时“咔嚓”一声,脆得人心尖尖发颤。
甜而不腻,酥而不散,吃一口,满嘴都是米香、油香、坚果香,
像极了老江津的烟火气,扎实、温暖,带着点岁月的甜。

清光绪年间,盐客们将东家丢弃的鸡杂混入土坛泡菜,
用三块石头支锅、瓷盆装料,猛火快炒出酸辣鲜香,既去腥又暖胃,成了寒冬里的“救命菜”。
这锅“边角料”的逆袭,从濯河坝码头传遍武陵山区,
2016年正式入选重庆市第五批非遗,
其魂在“现宰现烹”“老母子水”泡菜。
选土鸡心、肝、胗、肠,配藿香泡菜水,热油爆炒锁脆嫩,酸萝卜增爽脆,麻得舌尖打颤,辣得额头冒汗,香得人直咂嘴,
最后淋香油收汁,撒把蒜苗,那叫一个“安逸”!
如今,黔江鸡杂是江湖菜中的“顶流”。

诞生于清康熙年间。
周嘉镇周老爷等不得压豆腐,舀起半凝固的豆花蘸盐辣子,直呼“巴适得板”,
这口嫩滑便成了巴渝人家的日常。
民谣唱“家家有石磨,户户有石缸”,
青砂石磨出的豆香,裹着龙溪河水的清冽,两百年传到今儿,蘸水已攒下近五十种辣味,
从盐卤点制的“一清二白”,到油辣子红亮的“四红五绿”,吃的是乡愁,嚼的是岁月。
2019年,这手艺成了市级非遗。
黄豆泡足八小时,石磨低速研磨,浆液细腻如乳,点卤后凝成絮状如花,入口绵而不老,窖水回甜。
配碗蘸水,辣得冒汗也停不下筷,配上烟熏腊肉,那叫一个“安逸”!

清末《成都通览》里就藏着它的影子,
那时叫“碎皮酥鱼”,后来才慢慢“脆”了名堂。
传说抗战时重庆谈判,这道鱼就压了轴,泡椒丝儿搭着葱丝儿,红亮亮堆成小山,酸甜味儿直往鼻子里钻,连蒋委员长都派人来讨配方。
更有老巴县“整蛊王”安世敏的野史,
他怕媳妇儿被惦记,故意把鱼炸得歪七扭八,结果成了“丑鱼变美味”的奇谈。
2019年它正式成了非遗,
传承人李盛开坚持用长江箭杆草鱼,牡丹花刀法片出七道鱼片,
裹着自贡井盐、黄花园酱油腌足时辰,油锅里滚出金黄酥脆的皮,咬开是雪白细嫩的肉,
糖醋汁儿裹着泡椒香,酸得人直眯眼又舍不得停筷。

三千年江水卷着泥沙,也卷着巴人的倔强。
你看那码头还在,纤夫的号子化进火锅的沸响里;
老城墙拆了,石头缝里却长出吊脚楼的根。
茶馆的老头呷一口茉莉花茶,说起张献忠的银船沉在哪儿,
话音混着江风飘远。
这城总在拆修,可骨子里的硬气没散,
榨菜嘎嘣脆,豆豉黑亮亮,毛肚在红油里打滚。
日子就这样滚着,从西周滚到今天,越熬越浓。
走,烫火锅去,让那股子辣劲顺着喉咙滚进胃里,烫出个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