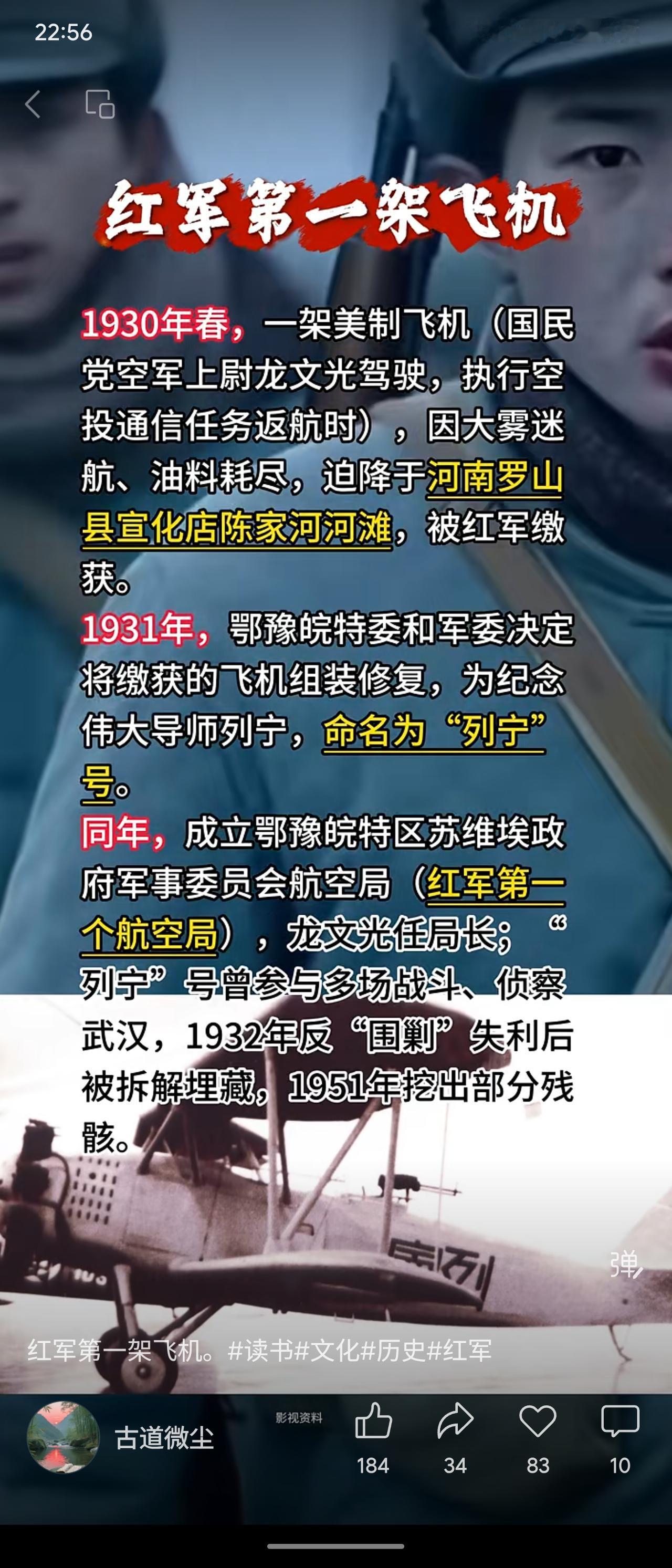1952年晚,几名美军举起刺刀对着志愿军的遗体刺捅,没多久便大摇大摆地离开,却不想在鲜血淋漓的尸体里面,有一双充血的眼睛正愤恨地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邹习祥这个名字,在上甘岭战役的英雄谱上,刻着沉甸甸的分量。那天夜里的事,是他晚年常跟孙子讲起的片段——不是炫耀,是说给后辈听:志愿军的人,站着是长城,倒了也是界碑。 邹习祥是贵州务川人,1922年生在仡佬族山寨。小时候跟着父亲在山里打猎,练出了鹰一样的眼力和兔子般的敏捷。1949年参军时,他已经27岁,是连里年龄最大的新兵,可打靶能十发九中,翻山越岭比小伙子还快。上甘岭战役打响前,他是15军135团1营1连的机枪手,守在597.9高地的7号阵地。 美军进攻7号阵地那天,炮弹像下雨一样砸下来。邹习祥的掩体被掀开了半边,机枪管烫得能烙饼,可他趴在土堆后面纹丝不动——他知道,身后的坑道里有伤员等着他掩护撤退。美军步兵冲上来时,他突然探出身子,机枪扫出一梭子,最前面的三个美国兵应声倒地。可敌人太多了,很快就有七八个端着卡宾枪的士兵绕到了侧面。 子弹打光的时候,邹习祥抓起身边的步枪准备拼刺刀。可他发现,不远处的战壕里,躺着几个牺牲的战友——其中一个是小战士王二牛,才19岁,早上还跟他分吃一块压缩饼干。美军士兵正朝着战友的遗体走过去,刺刀寒光一闪,扎进了王二牛的胸口。邹习祥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他扑过去想推开那个美国兵,却被另一个敌人从背后抱住了腰。挣扎中,他的后背挨了一刀,疼得眼前发黑,可他还是死死咬住对方的手腕,直到对方惨叫着松手。 等他再睁开眼,天已经黑了。他躺在战友的尸体中间,左胸、后背都是刀伤,血把军装浸成了暗红色。他试着动了动手指,还能感觉到冷风灌进伤口的疼。这时候,他听见有脚步声——是刚才那几个美军,正骂骂咧咧地检查尸体,刺刀又扎进了一个牺牲战士的腹部。邹习祥咬着牙,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他们的背影。他想,自己不能闭眼,至少要让这些畜生知道,中国人没全死绝。 后来清理战场的战士发现他时,他的手还攥着一块从敌人身上扯下来的布片,指甲缝里全是血。卫生员给他包扎时,他迷迷糊糊地说:“别碰我战友……他们没输。” 邹习祥的伤养了三个月,左肺被刺穿,落下了病根。可他不肯留在后方,伤刚好就申请回了前线。他说:“我在7号阵地趴过,知道那儿的石头缝里藏着多少弟兄的魂,我得替他们看着。”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邹习祥立了一等功,可他从不跟外人提。有次县里干部来家里慰问,问他当年怕不怕,他抽着旱烟说:“怕?怕就不来当兵了。可看见弟兄们死在眼前,哪还顾得上怕?就想,今天我多杀一个,明天就少一个鬼子祸害老百姓。” 他的孙子邹波后来才知道,爷爷当年的拼刺刀有多险——那个抱住他腰的美国兵,手里拿着一颗手雷,要是引爆了,邹习祥和身边的战友都得没命。可爷爷从来不说这些,只说:“打仗嘛,总得有人往前站。” 1993年邹习祥去世时,床头还放着那本《上甘岭战役回忆录》,书角卷了边,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7号阵地的合影,战士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笑得特别亮。邹波说,爷爷走的时候很安详,像是终于完成了什么任务。 现在再看那段历史,才懂邹习祥那双充血的眼睛里藏着的不是恨,是执念——他要让侵略者知道,中国的土地,哪怕用尸体铺,也不会让你们踩脏。那些倒在战场上的志愿军,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父亲、儿子、丈夫,是愿意用生命守住家门的普通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