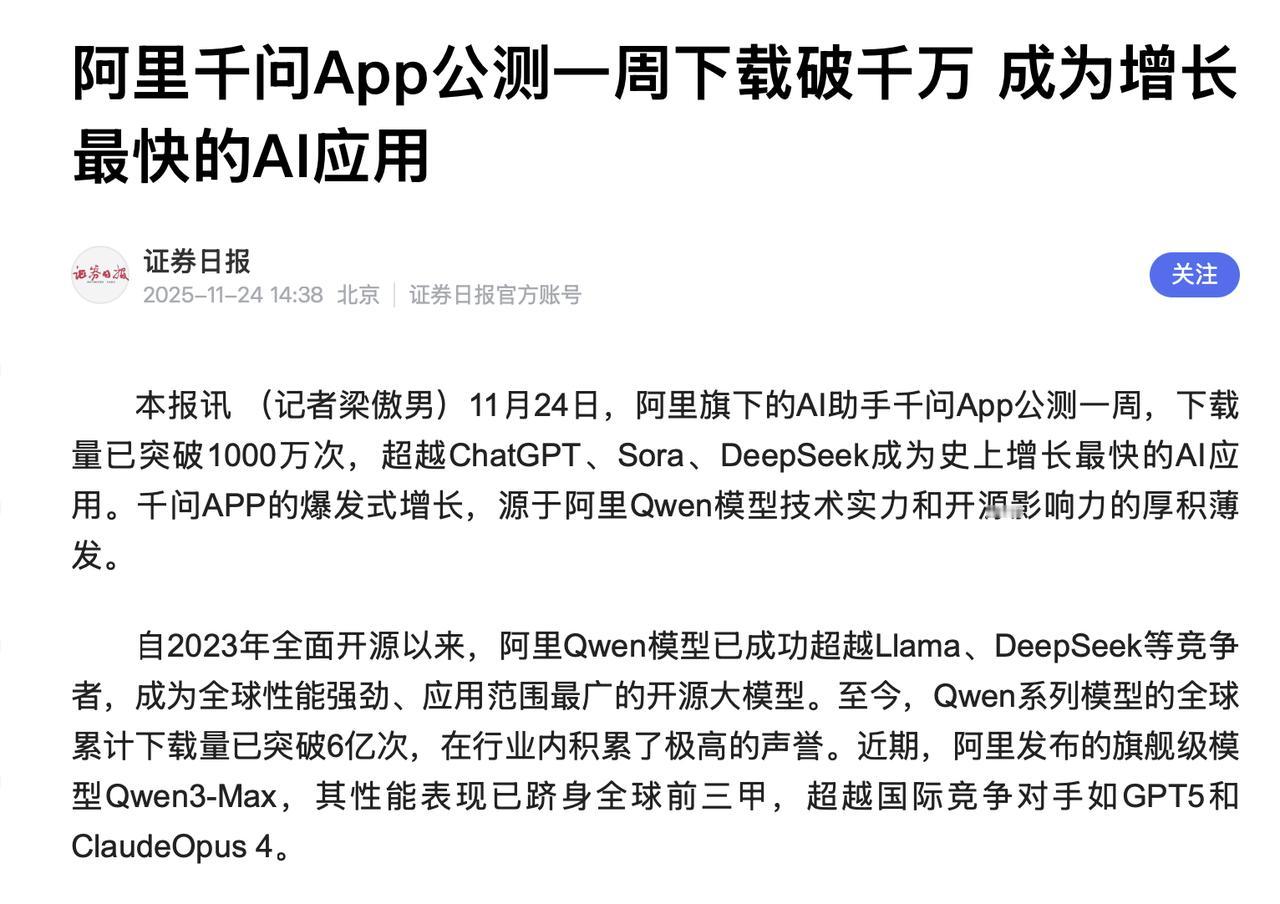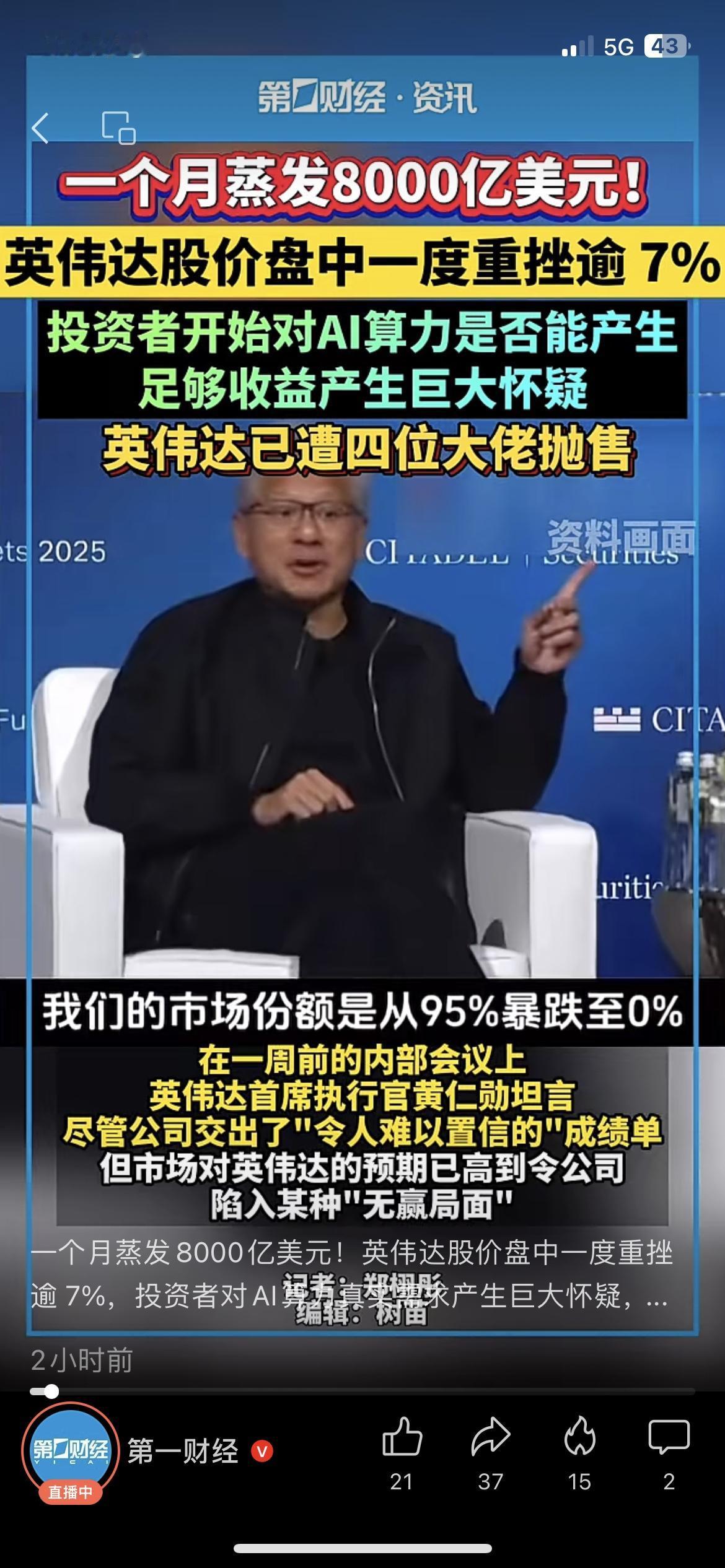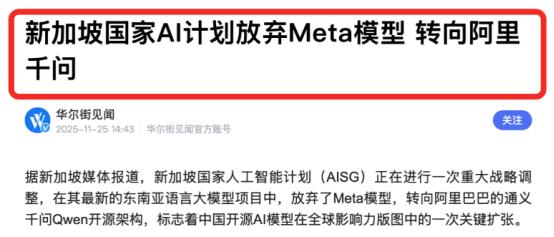在这个被“降本增效”奉为圭臬的时代,我们似乎正在迎来一个完美的梦魇。
Revealera公司最近抛出了一组冷峻的数据:在分析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1.8亿个招聘职位后,他们发现全球岗位发布数量同比下降了8%。这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的寒热交替,如果我们将显微镜对准这具庞大的数据尸体,会发现某些器官正在被定向切除。


只要你的职位名称里带有“专员(Specialist)”二字,你就是那块正在坏死的组织。摄影师、撰稿人、合规专员,跌幅都在28%以上。而另一边,顶着“总监”与“经理”头衔的岗位却在逆势疯涨。
这不仅仅是就业市场的震荡,这是一场关于“人”的定义的重新洗牌。特别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个关于二维码发明的古老故事时,一个令人背脊发凉的悖论浮出水面:AI带来的极致效率,正在抽干人类创新的土壤——那些被视为无用的“噪音”和“错误”。
一、 被折叠的“中间地带”首先,让我们撕开数据的表象。
这并不是一场众生平等的裁员潮。报告显示,高级管理职位(副总裁、总监)仅下跌了1.7%,而基层职位下跌了9%。更讽刺的是,在整体缩水的背景下,能够驾驭AI定义需求的人——那些总监们,需求量反而激增。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职场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折叠”。
过去,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路径是线性的:从整理会议纪要、录入数据、写基础文案做起。这些工作枯燥、低效,充满了重复劳动。但正是在这些被视为“低价值”的劳动中,人类习得了对行业的体感,积累了处理突发状况的直觉。

而现在,AI接管了这一切。它不睡觉、不抱怨、不要求加薪,最重要的是,它产出的初稿质量,往往优于一个磨合期的新人。
于是,企业做出了最符合资本理性的选择:去掉了“中间商”。他们不再需要执行层去试错,他们只需要一个能直接下达精准指令的“总监”,和一个不知疲倦的AI。
但这带来了一个断层式的危机:当基础台阶被抽走,未来的“总监”从哪里来?
这就像是要求所有小学生直接参加微积分考试,理由是“算术题计算器都能做”。企业正在变得像是一个只要30岁以上熟练工的怪兽,却不愿意为20岁的生疏买单。我们正在透支未来十年的人才储备,来换取接下来两个季度的财报好看。这种“杀鸡取卵”的效率提升,本质上是一种代际掠夺。
二、 完美的诅咒:如果当年有AI,就不会有二维码如果说职场断层只是社会分工的问题,那么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创新机制”的毁灭。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讲一个关于“无聊”和“低效”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电装(Denso)公司的流水线工程师原昌宏,每天的工作就是对付条形码。他的工作极其枯燥:给零件贴码、扫码、录入。由于条形码存储信息量极小(只有20个字符),想要追踪一个复杂零件,往往需要并排扫好几个条形码。而且条形码很娇气,稍微磨损就读不出来。
这是一份典型的“专员”工作:重复、低效、易错。
请注意,如果当时电装公司引入了今天的AI,故事会如何发展?
AI会接管原昌宏的工作。AI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在毫秒级读取零件特征,甚至不需要条形码;AI数据库可以无限扩容,不需要在零件上贴满标签;AI绝不出错,不需要午休,更不会因为觉得工作无聊而在下棋时胡思乱想。
在AI的统治下,电装公司的效率将达到极致。原昌宏会被优化掉,或者被转岗。
然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二维码了。
现实中的原昌宏,正是在这种“低效”的折磨中,在午休时与同事下围棋的“摸鱼”时刻,看着棋盘上黑白错落的布局,大脑中那个被压抑的痛点突然与无关的娱乐发生了碰撞:为什么不能把一维的条码,变成像围棋一样的二维矩阵?
二维码(QR Code)诞生了。它不仅解决了零件溯源的问题,更在三十年后支撑起了全球移动支付的半壁江山。
这是一个关于创新的残酷真相:伟大的创新,往往诞生于冗余、低效、无聊和错误之中。 它们是人类为了逃避痛苦、偷懒或者是纯粹的思维游荡而产生的副产品。
如果你用AI填满了所有的缝隙,消灭了所有的“垃圾时间”,让每一个流程都严丝合缝、极致正确,你就消灭了变异的可能。
三、 思维的多样性,恰恰来自“噪音”OpenAI的前核心人物Karpathy最近提出了一个让技术信仰者不安的观点:如果让AI用自己生成的高逻辑数据去训练下一代模型,模型最终会崩溃。
为什么?因为“正确”往往意味着狭隘。
人类思维之所以迷人,不在于它像逻辑门一样精准,而在于它充满了“噪音”。我们会在思考工作时突然想到昨晚的电影,会在写代码时突然对一句诗产生共鸣。这些看似无用的神经元放电,构成了思维在这个世界上的随机游走(Random Walk)。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能跳出局部最优解,找到全新的路径。
现在的AI模型,就像是一个被过度修剪的盆景。它剔除了所有的杂枝末节,只保留了最“应该”存在的形态。它提供的是所有可能答案中概率最高的那一个——也就是最平庸的那一个。
当我们把基础工作交给AI,我们不仅仅是交出了劳动权,我们还交出了在这个物理世界中“手感”磨练的机会。
正如文中所言,随着年龄增长,人类的大脑本身就在做“剪枝”,从1800种可能性收敛到8种。这是生理上的僵化。而现在,我们试图在外部世界用AI加速这个过程。我们在追求一种“工业级的确定性”,其代价是扼杀了“生物级的演化性”。
四、 结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AI?我们也许正在进入一个“无菌”的时代。
所有的文案都通顺流畅,但没有灵魂的毛边;所有的代码都几乎没有BUG,但也没有天才的怪癖;所有的流程都无比顺滑,但再也不会有人因为觉得“贴条形码太烦”而发明出改变世界的二维码。
这场变革对年轻人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切断了“从平庸走向卓越”的通道;而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潜在威胁,在于它用“效率”置换了“可能性”。
未来的AI,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只会背诵事实、执行指令的超级秘书。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模拟人类思维这一“混沌系统”的AI,是那种敢于保留“思考的结构”而非仅仅存储“思考的结果”的AI。
但在那之前,作为个体,我们或许应该警惕那种把自己变成“API接口”的倾向。在这个被算法重塑的世界里,你身上那些低效的、情绪化的、胡思乱想的“噪音”,或许正是你作为人类最后的防线,也是创新唯一的火种。
珍惜你的纠结与痛苦吧,因为AI并没有这些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