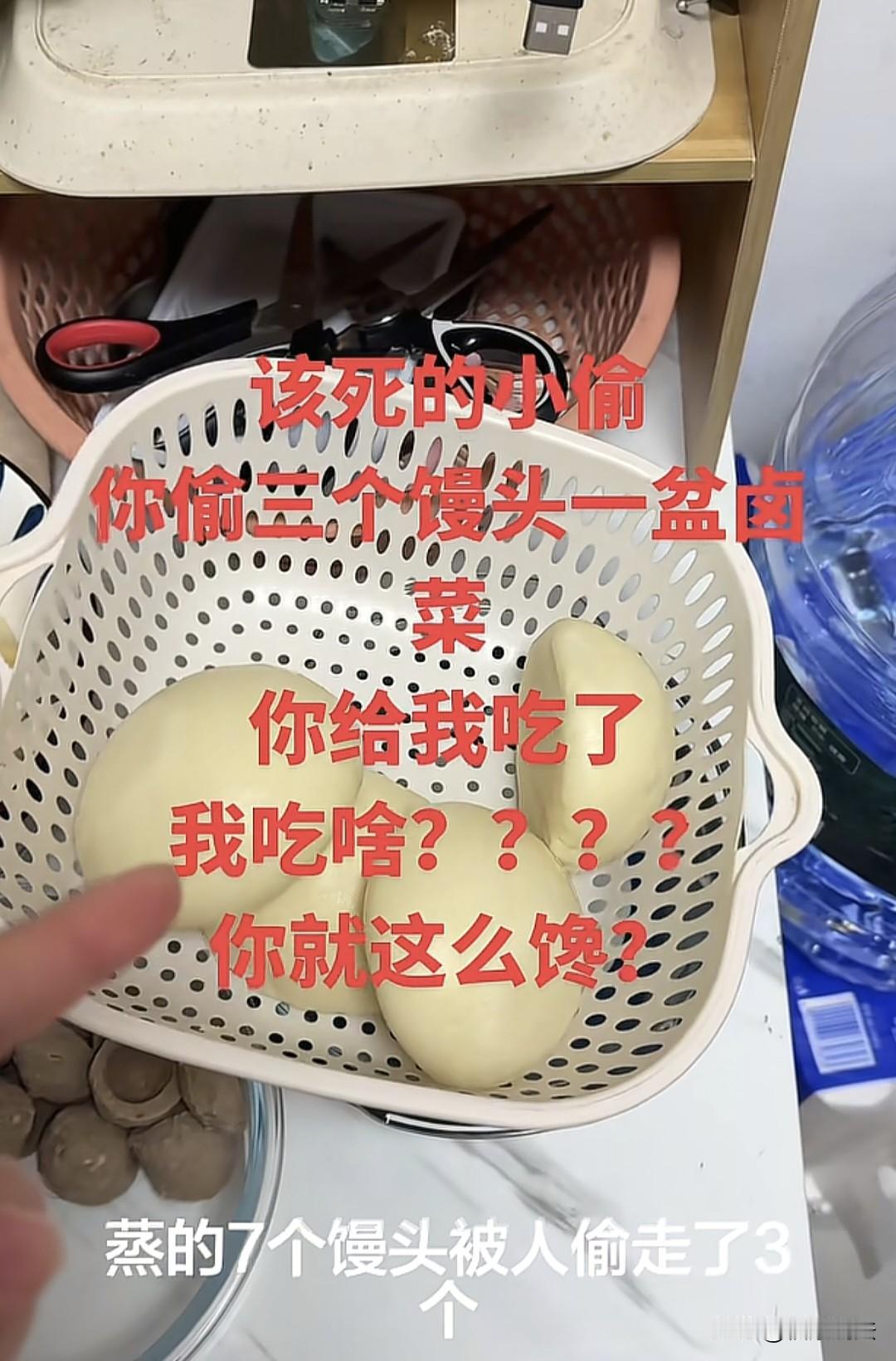父亲被银行贷了款,母亲莫名成了农机主
一我叫韦小江,桂林下面一个小镇上长大的。
具体哪个镇我就不说了,反正你从桂林市区往南开,过了几座馒头一样的山包,拐进一条
一我叫韦小江,桂林下面一个小镇上长大的。
具体哪个镇我就不说了,反正你从桂林市区往南开,过了几座馒头一样的山包,拐进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再沿着一条清得能看见底的小河走上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们那个村子不大,前面靠河,后面靠山,山上全是竹子和桂花树,一到秋天满村都是桂花香。听着挺美是吧?但美归美,穷也是真穷。年轻人要么去了桂林市区,要么去了广东,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小孩。
我爸韦德贵,今年六十一。我妈覃秀莲,今年五十八。
两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我爸最远去过南宁,还是陪我妈去看腰椎间盘突出,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宿,心疼得不是我妈的腰,是那几百块钱的挂号费。
我爸这个人,怎么说呢,老实得有点过头了。
村里人都叫他"韦老好",谁家杀猪请他帮忙,他二话不说就去;谁家红白喜事缺个跑腿的,他第一个到。但你要是借了他的钱没还,他嘴上不催,心里能惦记到过年。
有一回隔壁的老黄借了他两百块钱买农药,说好一个月还,结果拖了三个月。我爸愣是没好意思开口要,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跟我妈嘀咕:"老黄那两百块,是不是忘了?要不你去提醒一下?"
我妈就白他一眼:"你自己借出去的钱,你自己不好意思要,让我去当恶人?"
我爸就叹口气,翻个身,接着睡不着。
就这么一个人,你跟我说他贷了款不还?
我把脑袋拧下来都不信。
二2020年腊月的一天傍晚,我正在桂林市区的出租屋里炒米粉。
锅里的油还在滋滋响,手机就响了。
一看,我爸。
我爸这个人,平时打电话跟挤牙膏似的,能发语音绝不打电话,能打电话绝不打视频。他觉得视频通话费流量,流量就是钱,钱不能乱花。
所以他主动打电话过来,我就知道肯定有事。
一接通,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电话那头,我爸的声音在发抖。
不是冷的那种抖——桂林的冬天虽然湿冷,但还不至于把人冻成那样——是那种慌了神的抖。
"小江……小江啊,出大事了。"
我赶紧把火关了:"爸,咋了?你慢慢说。"
"银行……有个银行打电话来,说我十五年前贷了三千块钱,一直没还,现在连本带利滚到六千多了……"
我拿着锅铲的手停在半空中。
"啥?哪个银行?"
"一个什么商业银行,我也记不住那个名字。人家说是总部信贷股的,先打到咱村委会,村委会把我电话给了人家……"
我脑子飞速转了起来。
十五年前,那是2005年。2005年我刚上初中,家里确实起了新房子。那时候我们那一片好多人家都在建房,我爸也跟风翻新了老屋,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但我记得很清楚,钱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我爸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笔记着,谁家借了多少,什么时候还的,清清楚楚。到我上高中那年,最后一笔借款还清了,我爸还专门买了一挂鞭炮在门口放了。
"爸,你再好好想想,你到底有没有在什么商业银行贷过款?"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
"小江,十五年了……我真记不清了。那时候到处找钱,脑子乱得很。万一真贷了呢?万一我自己忘了呢?"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坏了。
他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就是我爸。一个老实了一辈子的人,别人一吓唬,他第一反应不是怀疑对方,而是怀疑自己。
"爸,你先别急。人家具体咋说的?让你咋办?"
"人家说让我赶紧把钱还了,不然要上什么征信,还说要走法律程序……小江,征信是个啥东西?上了是不是就成老赖了?"
我深吸一口气:"爸,你啥都别管,我来处理。你把那个电话号码发给我。"
挂了电话,我站在厨房里,米粉都糊了也没心思管。
三千块钱的贷款,十五年了才来催?
这十五年你们干啥去了?睡觉呢?
而且偏偏赶在2020年底,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到处封控,出行极其不便,你这时候打电话来催一笔十五年前的旧账?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三第二天一早,我就拨了那个号码。
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声音特别职业化,那种经过培训的标准普通话,一听就是专业催收。
"您好,请问是韦德贵先生的家属吗?"
"我是他儿子。你们说我父亲有笔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方噼里啪啦报了一串:贷款时间2005年8月,金额3000元,期限一年,逾期未还,当前欠款本息合计6284元。
然后她又报了我爸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一个字不差。
我心里一沉。
信息全对,说明系统里确实有这笔记录。
但信息对就一定是我爸贷的?
未必。
在农村,身份信息被冒用这种事太常见了。十几二十年前,基层信贷管理有多乱,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有些信贷员为了完成放贷任务,拿着村民的身份信息批量操作,这种事又不是没被曝光过。
我问她:"当时的贷款合同还在不在?签字是谁签的?有没有留存的影像资料?"
她停顿了一下:"这个……我们是总部催收部门,具体资料需要您到当地网点核实。"
"也就是说,你们连合同都没看过,就开始催收了?"
她没正面回答,只是说:"韦先生,建议您尽快处理这笔欠款,以免影响您父亲的个人信用记录。"
我说:"我们没有贷过这笔钱。你们要是觉得我父亲欠了钱,那就走法律程序,我们法庭上见。"
说完我就挂了。
我以为这事能消停。
结果我想多了。
四从那天起,催收电话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上了就撕不掉。
一天两个是常态,有时候一天四五个。
早上八点一个,中午十二点一个,下午三点一个,晚上七点再补一个。
打给我爸的,打给我的,甚至打到了村委会。
村支书都受不了了,给我打电话:"小江啊,你家那个贷款到底是咋回事?银行天天打电话到村里来,我这也不好跟人家说啥啊。"
我爸更是被折腾得不行。
他这个人,一辈子最在乎的就是面子。银行的电话打到村委会,他觉得全村人都知道他"借钱不还"了。走在路上碰到人,人家可能就是正常打个招呼,他都觉得人家在背后议论他。
有天晚上我妈偷偷给我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小江,你爸这几天又睡不着了。半夜两三点起来,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的。我问他,他也不说话,就坐在那里叹气。"
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爸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东西。现在被人扣了一顶"欠钱不还"的帽子,对他来说,比扇他两巴掌还难受。
又扛了几天,我爸终于撑不住了。
他给我打电话,声音疲惫得像老了十岁:"小江,要不……要不咱就把那六千多块钱还了吧。花钱买个清净。"
我一听就急了:"爸!不是咱贷的钱,凭啥还?六千块钱是不多,但这个账不能认!你今天认了,明天谁都能往你头上泼脏水!"
"可人家天天打电话……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电话那头,我爸的声音带着哭腔。
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被几个催收电话逼得快哭了。
我攥着手机,手指关节捏得发白。
五2021年开春,封控松了一些,我请了假,从桂林坐班车回了老家。
到家第一件事,我带着我爸直奔镇上的银行网点。
网点不大,就在镇政府斜对面,一个两层的小楼,门口挂着褪了色的招牌。
我找到行长,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姓莫,戴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然后提出要求:"我父亲不认这笔贷款。我们要求核验当时的贷款合同和签字资料。如果签字确实是我父亲的,我们二话不说,当场还钱。如果不是,请你们给个说法。"
莫行长听完,表情有点微妙。
不是那种惊讶的微妙,是那种"这事有点麻烦"的微妙。
他没有当场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说:"这个事情年头太久了,资料要从档案库里调,我们需要向上面反映一下。"
"行,你们反映。我等着。"
我留了电话号码,带着我爸回了家。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一周过去了,没消息。
两周过去了,还是没消息。
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消息。
这期间我打了不下十个电话催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那几句:"还在查""还在协调""资料还没调出来"。
但催收电话倒是一个没少,照打不误。
我爸在这种煎熬里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本来就不胖的人,颧骨都凸出来了。头发也白了不少,鬓角那一圈全是霜。
我妈心疼他,又帮不上忙,只能在旁边干着急。有时候半夜听到我爸在叹气,她也跟着偷偷抹眼泪。
我是真的恨。
恨那个不知道是谁的人,用我爸的信息贷了款,拍屁股走了,留下我爸背了十五年的黑锅。
也恨那个银行,连最基本的核实都不做,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催收,把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逼得寝食难安。
六转机出现在四月份。
那天我又打电话到镇上网点,接电话的不是莫行长,是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
我照例问:"我父亲韦德贵那笔贷款,核验结果出来了没有?"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她说:"哦,那个事啊,查清楚了。重名重姓,搞错了。真正贷款的不是你父亲。"
我拿着手机,整个人愣了足足有十秒钟。
"你说什么?"
"重名重姓,搞错了。"她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通知。
我的火"腾"地一下就蹿上来了。
"搞错了?就这三个字?你们折腾了我父亲小半年,天天打电话催收,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瘦了十来斤,头发白了一圈,现在你告诉我——搞错了?"
"这个……确实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给您和您父亲带来了不便,我们表示歉意。"
"不便?你管这叫不便?"我的声音已经压不住了,"我问你,如果不是我们坚持要核验资料,如果我父亲扛不住你们的电话轰炸,把那六千多块钱还了,你们是不是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白收了一笔不该收的钱,账目一平,皆大欢喜?"
电话那头沉默了。
"你们要降低坏账率我理解,但也不能逮着一个老实人往死里薅吧?"
依然沉默。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行,这事我先记下了。但我要求你们给我父亲出一份正式的书面说明,证明这笔贷款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我跟领导反映一下。"
那份书面说明,最后拿到了吗?
没有。
催了好几次,对方要么说在走流程,要么干脆不接电话。
后来我也懒得催了。人家都说搞错了,你还能怎样?总不能为了一张纸去打官司吧?
我爸倒是终于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破天荒地让我妈炒了两个菜,自己倒了二两米酒,吃了两大碗饭。
我妈在旁边看着他,眼圈红红的,嘴上却骂:"叫你瞎操心!叫你睡不着!活该瘦成猴!"
我爸嘿嘿笑了两声,没吭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我心里那口气,一直没顺过来。
七我以为这种荒唐事,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够倒霉的了。
没想到,第二件更离谱的事,说来就来了。
就在上个月,村委会又给我打电话了。
打电话的是村里的文书小覃,跟我同姓,比我小三岁,平时关系还不错。
"江哥,有个事跟你说一下啊。区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在梳理机械台账,发现你妈覃秀莲名下登记了一台拖拉机,无号牌,未审验。上面问现在什么情况,谁在用,用途是什么。"
我当时正在工地上搬水泥——对,我后来没在桂林市区待了,回了县里,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听到这话,手里的水泥袋子差点砸脚上。
"你说啥?我妈名下有台拖拉机?"
"对,登记在覃秀莲名下,身份证号也对得上。"
"小覃,你逗我呢吧?我妈这辈子连电动车都不敢骑,她名下怎么会有拖拉机?"
"我也觉得不对劲,所以才打电话问你。你回去问婶子,看是不是有亲戚朋友买了拖拉机登记在她名下的。"
我挂了电话,脑子里嗡嗡的。
拖拉机?
我家?
打我记事起,我家最大的农具就是一把锄头和一辆手推车。后来日子好过了一点,买了辆电动三轮,我妈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我家也有车了!"
拖拉机?想都不敢想。
我当天晚上就骑着电动车赶回了老家。
八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妈正在灶台前烧火煮猪食,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的。
看到我回来,她还挺高兴:"咋回来了?吃了没?锅里还有米饭,我给你热个菜。"
"妈,先别忙。我问你个事。"
"啥事?"
"你名下是不是有台拖拉机?"
我妈手里的火钳"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扭过头瞪着我,那表情就像我问她"你是不是偷偷买了一架直升机"一样不可思议。
"啥?拖拉机?哪个说的?"
"村委会说的。区农机中心查出来的,登记在你名下,身份证号都对得上。"
我妈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把抄起旁边的笤帚,气得往地上狠狠一摔。
"哪个这么缺德!老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害得人不得安生!咱家祖祖辈辈,哪个买过拖拉机?咱们知根知底的亲戚,几辈子了都没跟拖拉机沾过边!"
我妈这个人,平时脾气好得很,在村里跟谁都笑呵呵的,轻易不发火。但这次是真的气着了,嗓门大得隔壁的黄婶都跑过来看。
"秀莲姐,咋了?跟谁吵呢?"
我妈把事情一说,黄婶也惊了:"啥?你名下有拖拉机?这不是扯淡嘛!"
消息在村里传开了,速度比村头的大喇叭还快。
当天晚上,我大伯、二姑、三叔都知道了,纷纷打电话来问。
大伯说:"不可能是咱家亲戚干的,咱老韦家的人我还不了解?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心眼。"
二姑说:"这肯定是被人冒名了。前些年农机补贴管得松,有些人专门钻这个空子,拿别人的身份信息去套补贴。"
三叔更直接:"报警!这是犯法的事!"
我爸坐在堂屋的竹椅上,一声不吭,闷头抽着水烟筒,"咕噜咕噜"的水声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
我看着他,想起了去年那笔莫名其妙的贷款,心里一阵发堵。
怎么倒霉的事,全让我家赶上了?
九第二天一早,我骑着电动车去了区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态度还行,帮我查了系统。
"确实是登记在覃秀莲名下的,2012年登记的,一台小型拖拉机,当时享受了农机购置补贴。"
"补贴多少钱?"
"按当时的标准,应该是几千块。"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母亲从来没有买过拖拉机,也从来没有申请过任何农机补贴。这台拖拉机是被人冒名登记的。"
小伙子为难地挠了挠头:"这个……时间太久了,当时的经办人可能都调走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把情况记录下来,向上面反映。"
又是"向上面反映"。
这四个字我都快听出茧子了。
"那我母亲名下这台拖拉机怎么处理?能不能注销?"
"这个需要走流程,可能要一些时间。"
"那冒用我母亲身份信息的人呢?能不能查出来是谁干的?"
"这个……我们这边主要负责机械管理,调查的事可能需要您去相关部门反映。"
我从农机中心出来,站在路边,看着远处那几座熟悉的喀斯特山峰,心里五味杂陈。
有人冒用我妈的身份信息,登记了一台拖拉机,领了几千块钱的农机补贴。
领就领了吧,人家领完拍屁股走人,享受得心安理得。
留下我妈,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莫名其妙成了"农机主",还得配合这个调查那个核实。
你说气不气人?
十后来这两件事是怎么收场的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不了之。
贷款的事,银行说搞错了,连个正式的道歉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赔偿。我爸白白担惊受怕了小半年,瘦了十来斤,头发白了一圈,换来一句轻飘飘的"重名重姓,搞错了"。
拖拉机的事,农机中心说在走流程,走了两个多月,也没个结果。我打了几次电话催,对方要么说还在处理,要么说负责人不在。后来工地上活忙,我实在抽不出时间一趟趟地跑,也就搁下了。
我妈倒是看得开,她说:"算了算了,又没少咱一块肉,就是挂个名而已,跟人家计较啥?"
我爸也说:"别折腾了,来来回回的,耽误你干活挣钱。"
你看,这就是我的父母。
被人冒用了身份信息,被银行催收了半年,被莫名其妙挂了一台拖拉机在名下。
到最后,他们不是愤怒,不是追究,而是——"算了"。
因为他们觉得,跟人家计较太麻烦了,太费劲了,太耽误事了。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
吃了亏,忍了。受了气,扛了。被人欺负了,算了。
他们把善良当成了做人的本分,却不知道,这份善良在某些人眼里,恰恰是最好拿捏的软肋。
尾声
前几天晚上,我躺在工地的宿舍里,听着窗外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叫声,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我爸被催收电话逼得半夜坐在堂屋里抽水烟的样子,灶膛里的火早灭了,他就那么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烟筒里的水"咕噜咕噜"响。
想起我妈听说自己名下有台拖拉机时,气得把笤帚摔在地上的样子,嗓门大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想起银行那个轻描淡写的"重名重姓,搞错了"。
想起农机中心那个永远在"走流程"的回复。
我忽然觉得特别心酸。
我的父母,一辈子没害过任何人,没占过任何人一分钱的便宜。
他们种了一辈子地,养大了我,供我上了学。他们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逢年过节杀只鸡,鸡腿永远是留给我的,他们自己啃鸡架子还说"我爱吃这个,香"。
他们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从不跟人红脸。
可就是这样两个人,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当成了软柿子。
因为他们老实,所以银行可以不核实就催收。
因为他们善良,所以有人可以冒用他们的身份去领补贴。
因为他们怕事,所以所有的不公最后都变成了一句"算了"。
我不怪我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长大的,骨子里刻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条。在他们看来,能忍就忍,能让就让,吃亏是福。
但我想对那些占了便宜的人说一句——
你们拿走的不是几千块钱,也不是一个名字。
你们拿走的,是两个老人的安宁,是他们对这个世界仅剩的那一点信任。
你们觉得他们好说话,觉得他们不会追究,觉得他们的善良可以被无限透支。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世上的便宜,没有一样是白占的。
今天你占了一个老实人的便宜,明天这份亏欠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找上门来。
不是我迷信,是我信因果。
我爸常说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
我以前觉得这话太老土了,跟他那个人一样老土。
现在我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