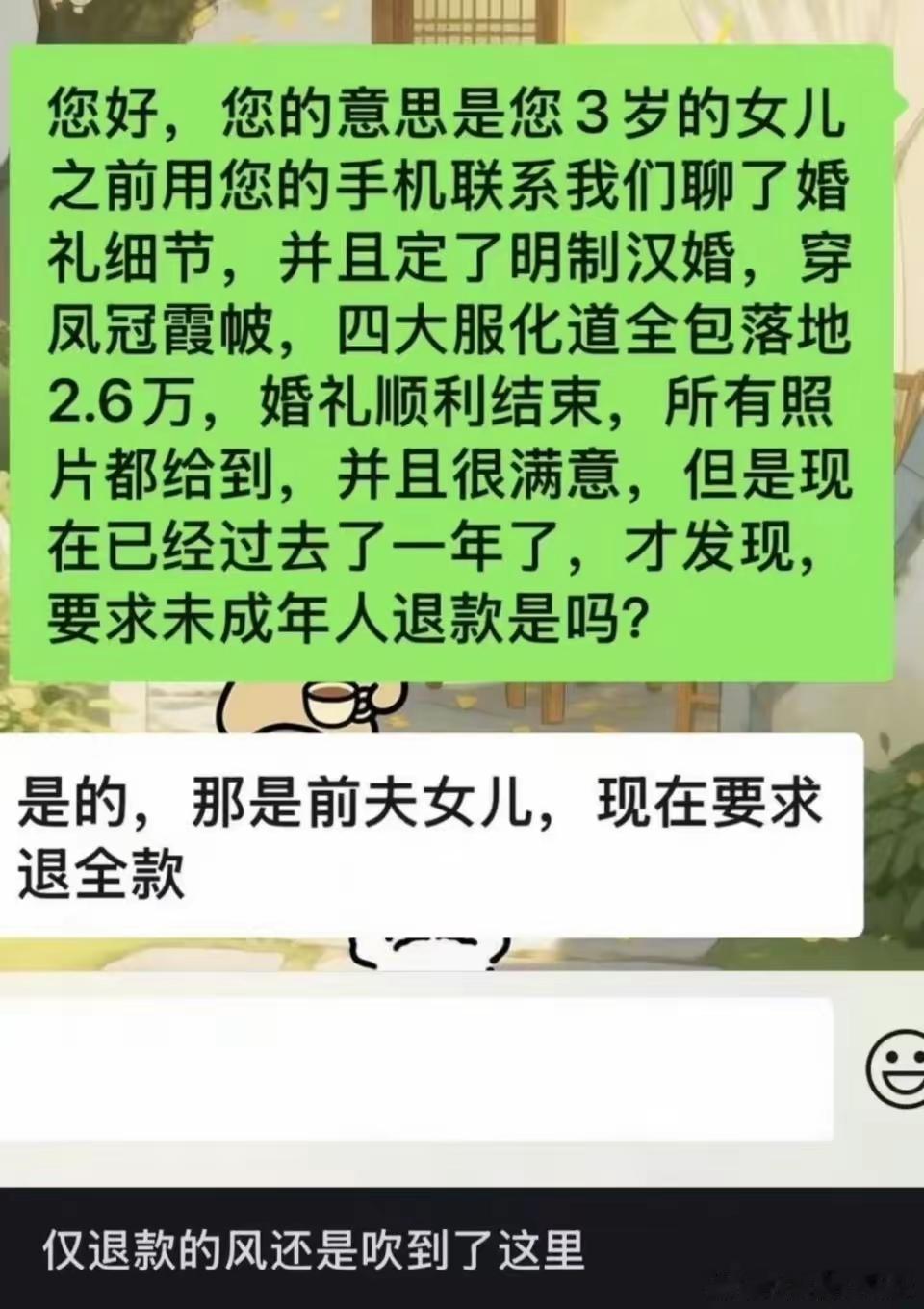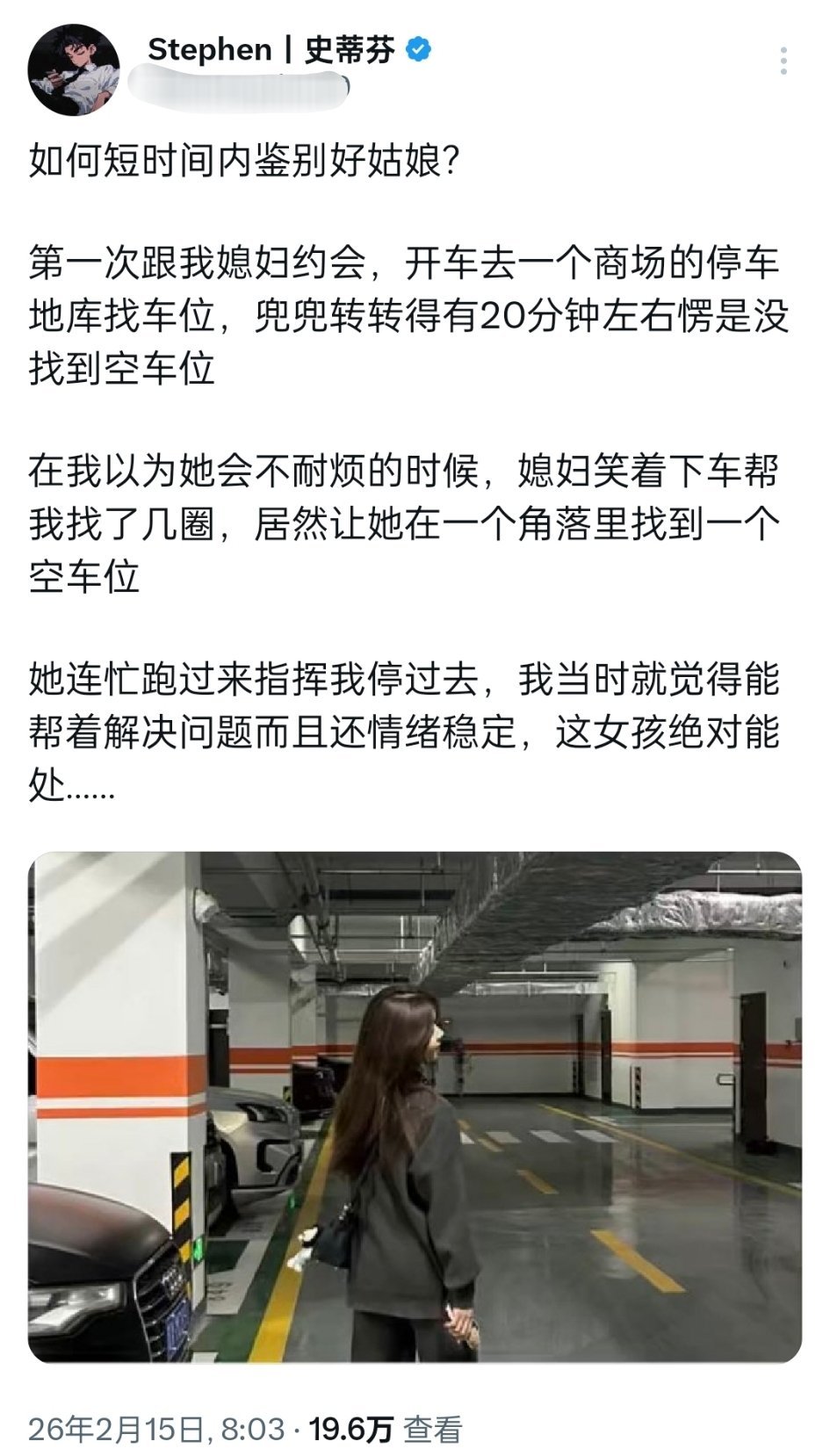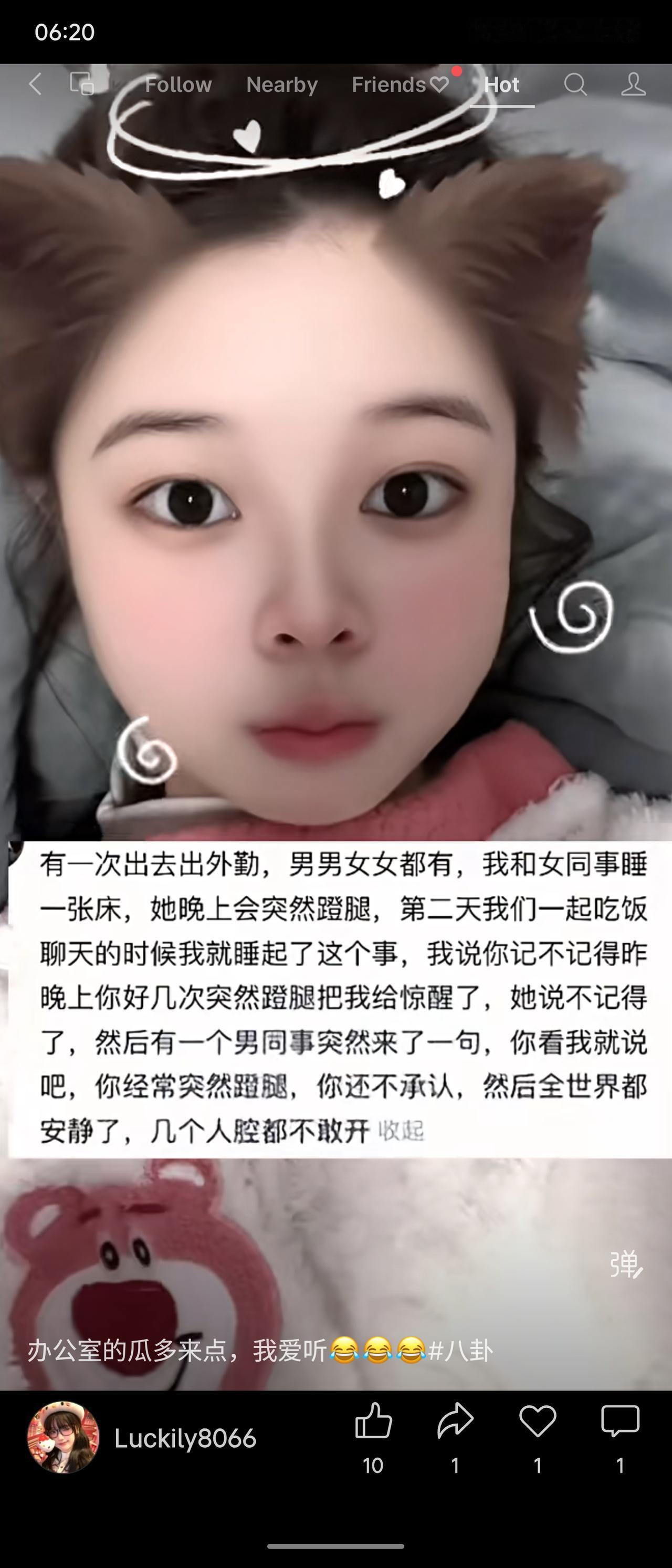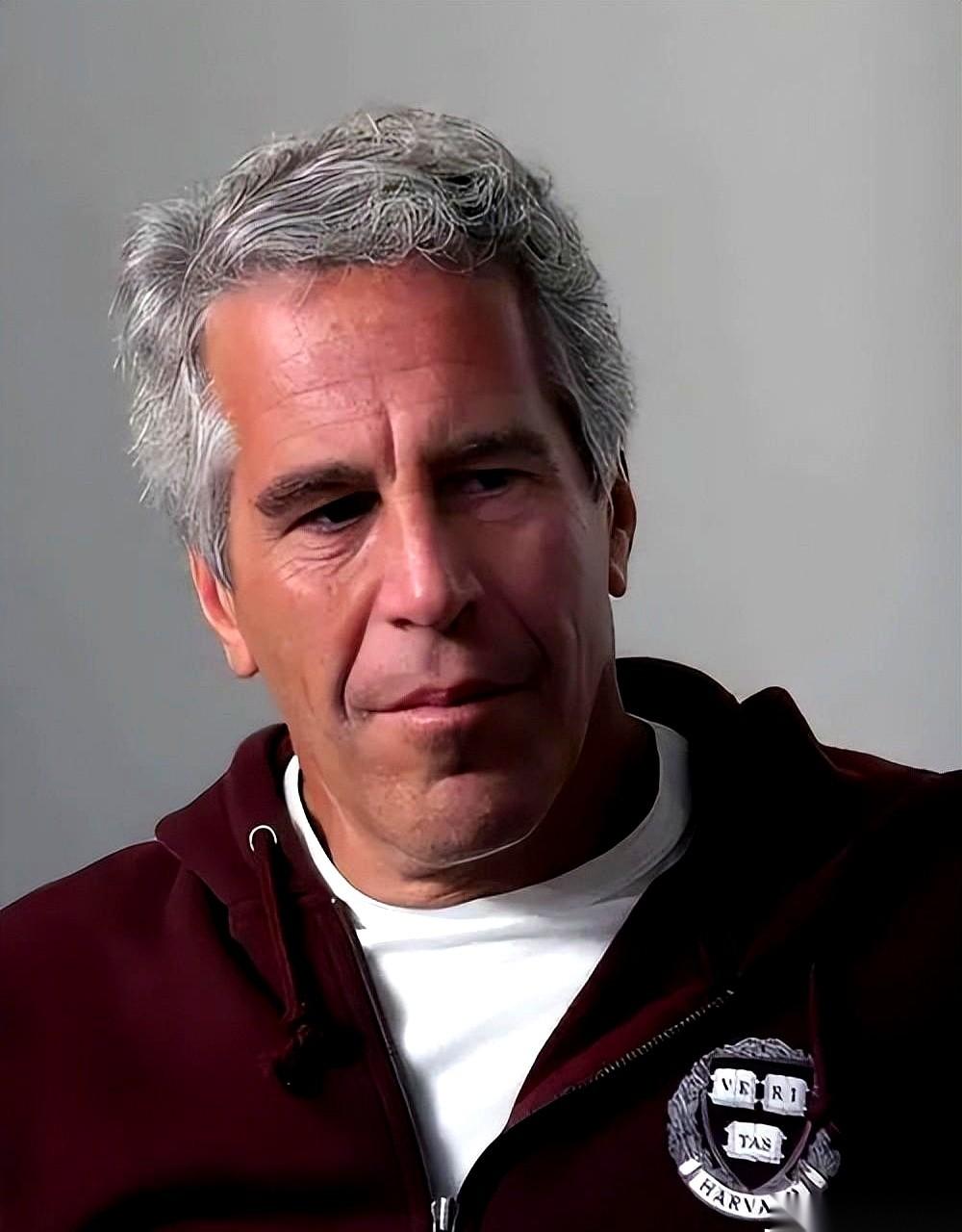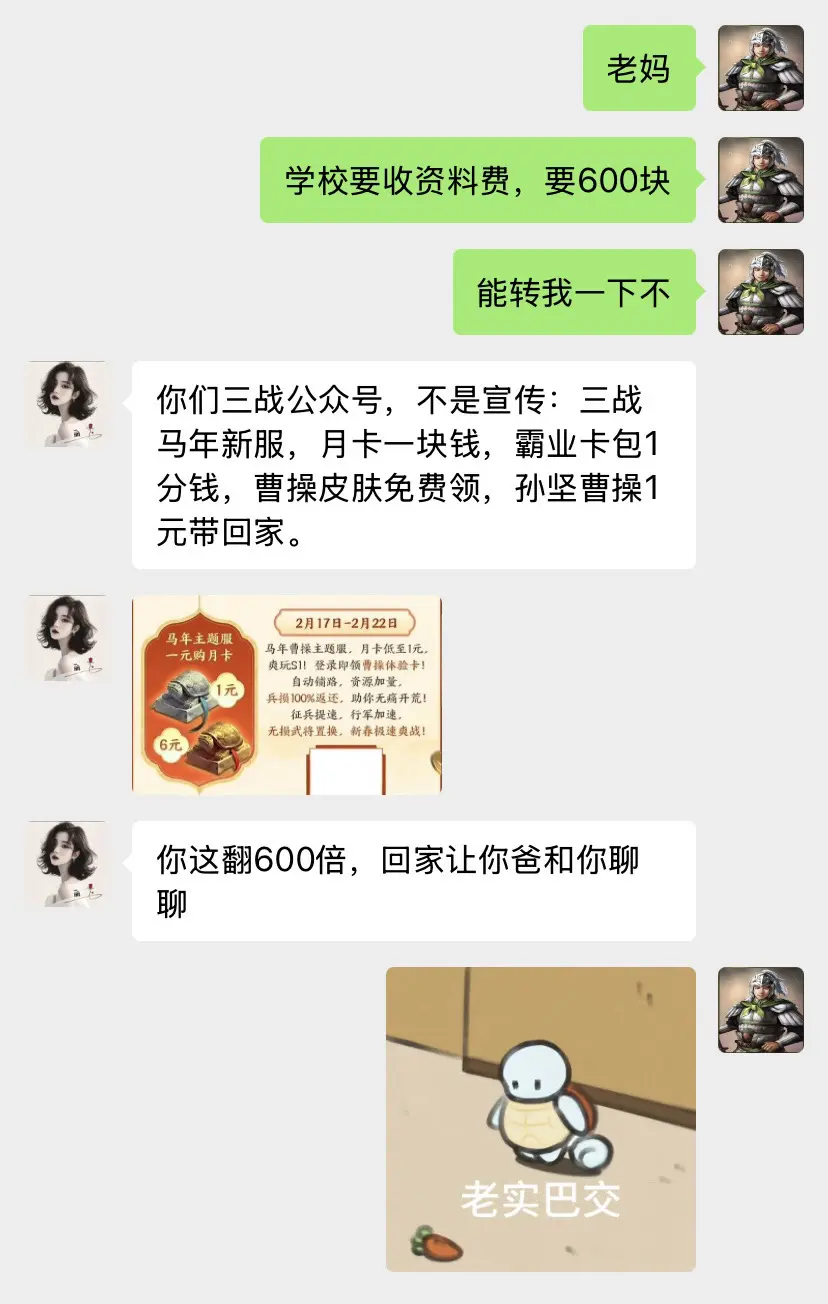她每夜都准时会在人定时从噩梦中醒来。
程少商在长秋宫偏室的软榻上缓缓地睁开眼,帷幔一层又一层,不远处未熄的烛火在铜灯里摇曳着,她混沌地想了好久,这是在哪儿。
是了,只有长秋宫里的安神香丸里混了藿香,这已是第三年了。
程少商挣扎着爬起来,把眼角已经有些干涸的泪痕轻轻擦掉,端起耳杯,把那小半杯的安神茶吞下,苦得她发抖。
矮几上会有她在入睡前给自己在耳杯里盛好的小半杯安神茶,酸枣仁、知母再混着一两甘草和茯苓,她围着被,又想了想,顺手在盒子里翻出了饴糖吃了。
糖块有些硬,刮蹭着她的舌头,她又在咀嚼刚才的梦。
凌不疑又一次死在自己的梦里。
这一次他死得很是哀怨,竟是因为她不肯为他做鱼吃,便推开了她,坠向旁边的洱湖。
“我不记得你这样爱吃鱼啊。”她抱膝笑着,喃喃地数着烛火噼啪的晃影,闭上了眼,“你爱吃羊肉多些..”
梦里的凌不疑总是那身装扮,玄衣金甲,发髻高高地竖起,他总是板着脸不让她吃饼子,后来心软了,又送她蛇皮履,总是搞得她一头雾水。
可这一次再闭上眼,没有那些暗沉沉的火烛光斑,也没有那些喷溅在窗棂上的血迹,瘫倒在地上的尸体,没有漆黑的深渊也没有冬日奔袭的黑马,只有柔和清丽的鸟鸣还有风吹动竹林摩擦树叶的声音。
她再睁开眼,正被熟悉的味道沉沉拢在怀里,热气搁在她肩窝,有些痒。
程少商想动动手,却因为被男人桎梏在怀里不得动弹,她脱口而出,“子晟…”
子晟?他回来了?
她呆了一瞬,现实和回忆正在努力拼凑归位,没有熟悉又暗沉的帷幔,也没有压得让人喘不过气的香丸,没有苦涩,只有那种非常愉悦的安全感。
“醒了?”男人的手自然地抚上她额头,在紧张的确认什么,“终于退烧了。”
“你说了好几晚的胡话,”霍不疑轻轻把头抵在她脖颈,又将她往自己怀里紧了些,“你昏睡了几日,那日懋儿被你吓坏了,嗓子都哭哑了…”
程少商喉咙发苦,勉强拼凑着脑海里的画面,踟蹰了好久,握紧拳头,亦哑声小心问着他,“这是梦吗?”
她太怕了。
霍不疑没有回答,“这一次在梦里,我还活得好好的?”
她动了动,转过身更近些地窝进他怀里,手紧紧揽着他的腰,“又死了。”
霍不疑闷闷笑着,仿佛听她说了个很好笑的笑话,“这次因为什么?”
她终于确定了,她在南霭城郊的竹月湖旁,霍不疑是益州州牧,他们还有个小团子叫霍懋,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希望这个小团子勤谨奋进,虽然捣乱时候更多…
“你..又死了。”她硬邦邦的落下一句回答,“因为我不给你做鱼吃…”
她的热气吐在他胸口,环住他里衣后襟的手一直紧揪着不放手,“梦里我还在长秋宫,半夜只能喝那样涩口的苦茶,我那时候真心恨透了你…”
霍不疑把吻落在她头顶,又向下寻着她的唇,深吻直到她喘不过气才放过她,“我那时也从没想过能活着回来见到你,”程少商昏睡的这几日,于他而言,更像是生肉置于温火中慢慢炙烤,是那种完全不安的钝痛。他想到了他们分开的那几年,他顿了顿,缓声道,“但还好我回来的还够及时。”
“怎么?”
“袁慎盘算的终是差我一招。”
“你想得美,”程少商身子还是发软,她发了好多汗,浑身酸软,但嘴上还是不想认输,“反正现在他还没娶呢。”
“夫人要反悔?”霍不疑慢悠悠道。
“怎么?”她抬起头,眯着眼细细打量着拢自己在怀里的武将的表情,“你怎知我就只吃你这一套?”
“就凭你这三日,日日夜夜唤得都是我的名。”
程少商也笑,在他怀里寻了个更舒服的位置闭上了眼,这一次并没那样怕了。
总归,他都在她身边,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
—疑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