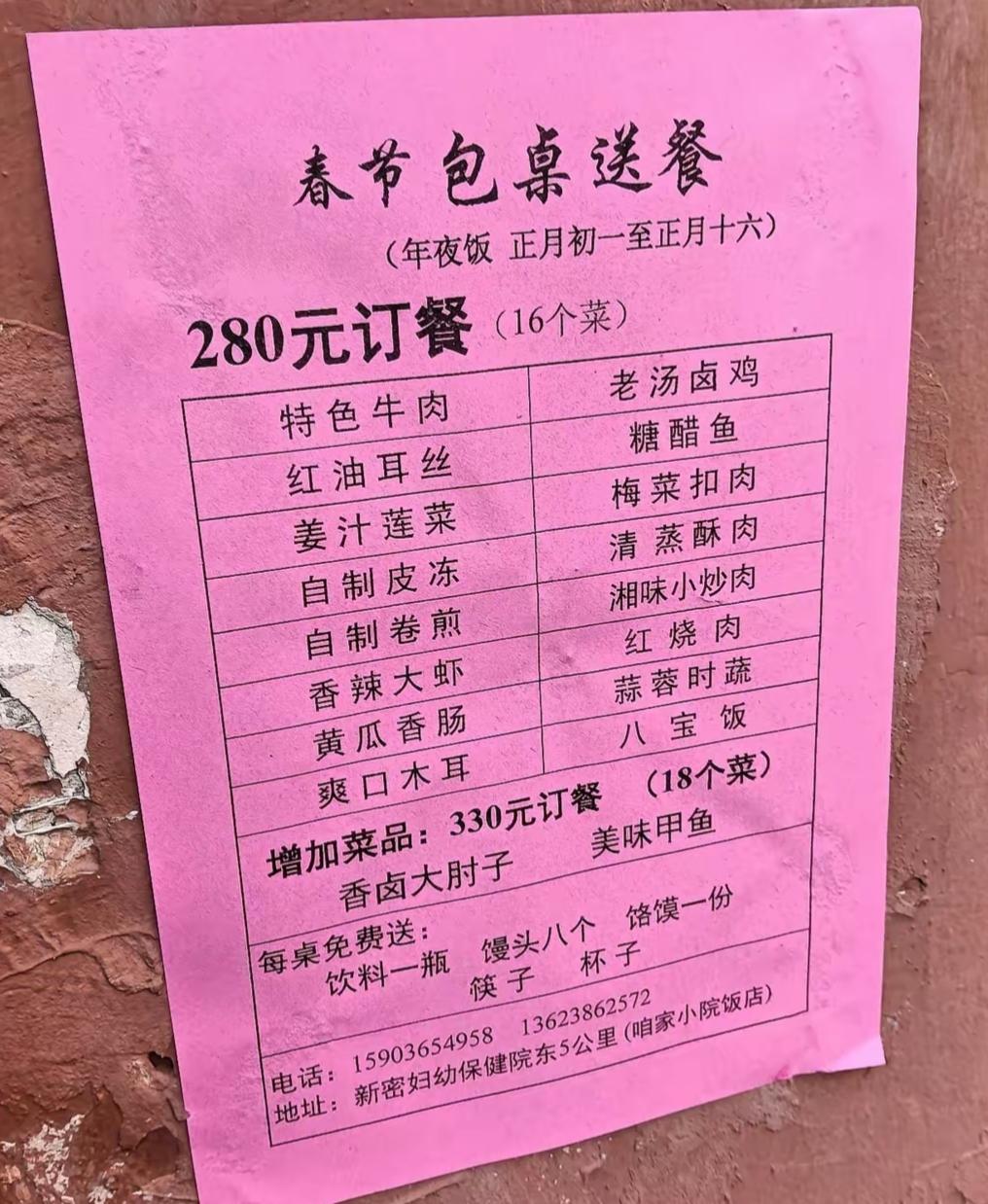1994年,一个英国姑娘坐在成都的小馆子里,对着一碗白米饭发呆。她刚刚吃了一口鱼香茄子,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她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这碗饭,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1994年,那时的成都空气里还没那么多汽车尾气,只有潮湿的煤烟味和炸花椒的霸道香气,扶霞坐在路边苍蝇馆子嘎吱作响的竹椅上,对着一盘鱼香茄子发呆,这位牛津长大、剑桥毕业的高材生,本该在明亮的图书馆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或者回伦敦做个优雅的编辑。 但这一口茄子下去,酸、甜、苦、辣、咸在舌尖上瞬间引爆,那种感觉不亚于脑子里被劈了一道雷,她想不通,同样的蔬菜,在英国是水煮后的尸体,怎么到了这里就成了勾魂的魔法,也就是在那一刻,她把自己的人生剧本撕了。 历史不研究了,她要留在这个充满油烟味的地方当厨子,你得知道这在当时有多离奇,当她跑到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现在的四川旅游学院)去报名时,招生办老师的表情大概比看到外星人还惊讶。 1994年,建校以来从没收过外国人,最后,在这个满是穿白大褂、操着四川方言的中国小伙子的后厨江湖里,硬是挤进了两个金发碧眼的异类,扶霞和她的德国同学沃克,但这姑娘可不是来玩票的,她是拿写博士论文的那股狠劲在学做菜。 每天练刀工切到手指贴满创可贴那是家常便饭,在她眼里,这哪里是做饭,分明是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她随身带着笔记本,这三十年来攒了130多本,别人看热闹,她看门道,她把切菜的刀工视为词汇量,把火候的掌控看作语法结构。 而川菜那神鬼莫测的二十三种复合味型,被她解构成了修辞手法,为了搞懂担担面的秘方,她像个便衣侦探一样天天去面馆蹲点,那个脾气古怪的谢老板,整天阴沉着脸躺在竹椅上,根本不想搭理这个洋鬼子,但扶霞就用那一招:死缠烂打。 今天问辣椒油的温度,明天问芝麻酱的比例,硬是靠着这股子痴迷劲儿感动了谢老板,拿到了独门配比,短短三个月,她死磕下了十六道经典川菜,但这还不够,回到英国后,她发现西方人对中餐的误解简直深得像马里亚纳海沟。 在傲慢的偏见里,中餐被贴上了“廉价外卖”、“油腻不健康”甚至“野蛮”的标签,扶霞坐不住了,她决定当那个打破墙壁的人。 2001年《川菜食谱》出版。这本书不是简单的食谱堆砌,而是一次跨文化的各种翻译工程,最要命的就是中餐里那些玄学词汇——“盐少许”、“油适量”、“火候正好”这种靠中国师傅几十年手感堆出来的经验,西方人根本看不懂。 扶霞做了一件极其硬核的事:她把这些模糊的感性经验,全部换算成了精准的克数、毫秒和科学计量,她告诉西方读者,川菜不只是辣,那是“百菜百味”的艺术,中国人追求的“脆”和“弹牙”是对口感的极致审美。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她像个苦行僧一样笔耕不辍,《鱼翅与花椒》、《中餐革命》接连问世,四座詹姆斯·比尔德奖,这可是餐饮界的奥斯卡,被她收入囊中,连陈晓卿都不得不服,评价她是“拥有四川灵魂的英国女人”。 哪怕到了今天,在伦敦的家里,她的厨房常备着郫县豆瓣酱和汉源花椒,每逢春节,她还会像个老派的中国人一样,按生肖做菜。 鼠年捏个老鼠形状的蒸饺,牛年就炖一锅红烧牛肉,虽然那个教她做面的谢老板的面馆早就拆迁了,当年的成都老街也变成了游客打卡地,但扶霞搭建的那座桥梁却越来越坚固,她用三十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饮食从来不是为了维持生命体征的燃料加注。 在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里,藏着的是对“人”的感官最大的尊重,是活得有温度、有尊严的证据。信息来源:人民网——扶霞 一个“有四川灵魂的英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