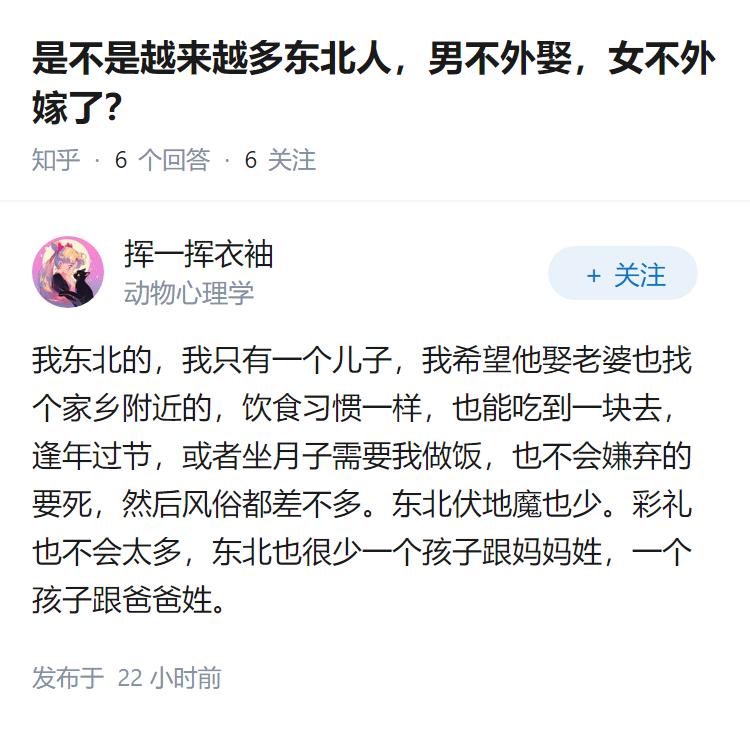褚时健上任头21天,没开一次大会,也没签一张文件。他天天蹲在车间,摸机器、翻库存、听工人骂娘,连谁家孩子上学难、谁家媳妇没热水洗澡都记在小本子上。 别人觉得他慢,其实他在找病根——不是机器坏了,是人不信了;不是没活干,是干了也没人认。 他先拿维修拖沓开刀:故障两小时不报,直接免职。供销科长被停职那天,全厂都愣住,没人再敢把“正在处理”当挡箭牌。 接着挤出钱盖宿舍楼。三栋楼拔地而起,工人搬进带灶台的新房,有人摸着水龙头蹲地上哭了。 后来他押上厂子借261万,从英国买设备。老工人说,第一包紧实的红梅烟出来那会儿,锅炉房门口站满了人,谁也不走。 他没讲大道理,就做几件事:让人信得过、干得值、住得像个人。 玉溪卷烟厂快散架了,谁来都得踩雷,他却只带一壶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