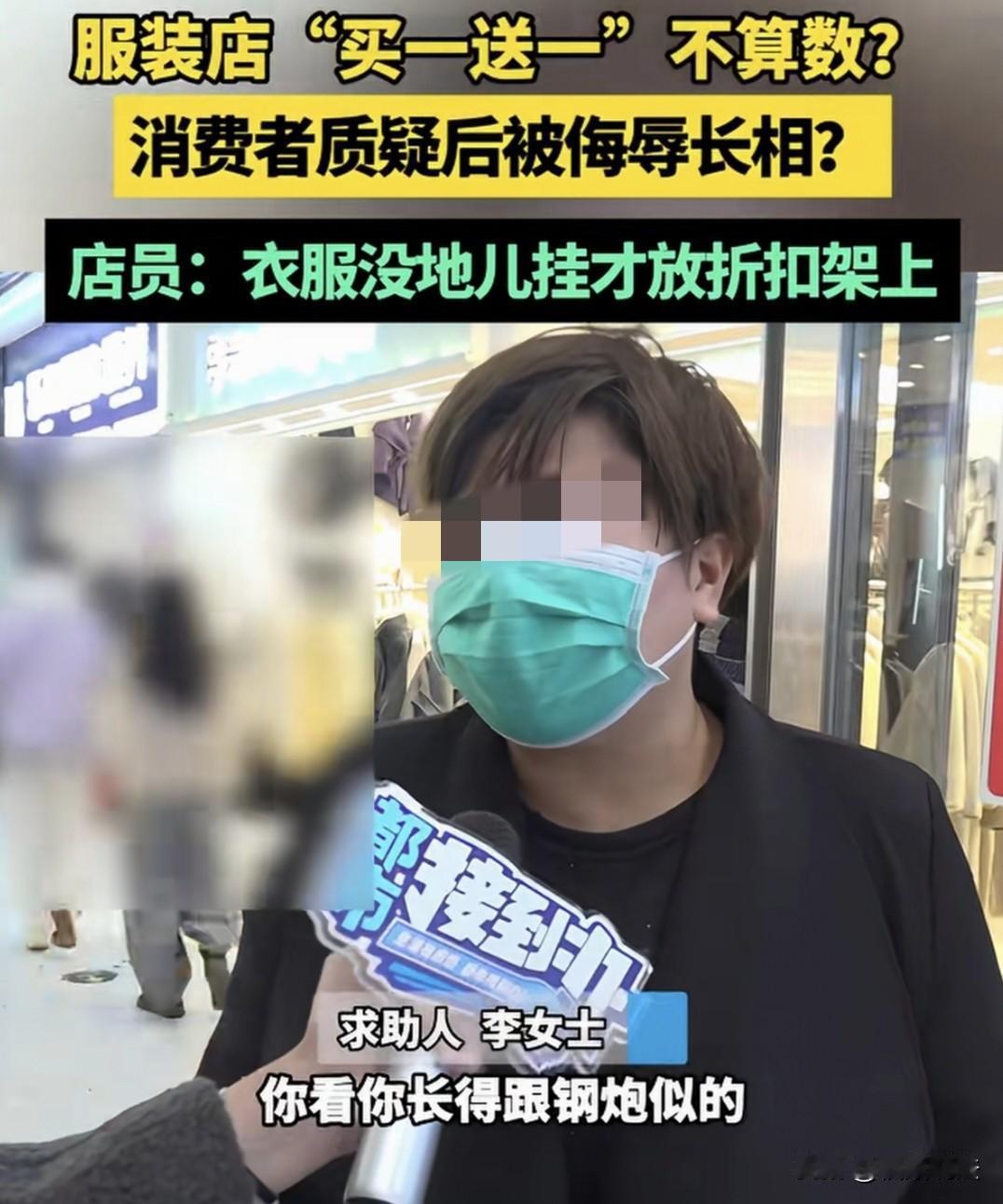2011年,云南省某人民医院,一男子说自己一天刷十次牙,但一张嘴就是伴着铁锈的恶臭味,医生说:“你头里有异物!” 几年前,阿福还是云南元江一个看小卖部、顺带跑摩的的普通人。那时生意尚可,家里虽然不富裕,娶了贤惠的妻子,生活算得上踏实。 2006年一个傍晚,阿福在县城进完货骑摩托回家,半路遇到一名年轻人拦车,说去邻村,愿意付钱搭车。阿福心善,挥手让人上车,还说不用给钱。 车开到偏僻路段,年轻人让停车。车刚停稳,阿福后脑勺就挨了一记重击,左耳根随即传来撕裂般的剧痛。对方亮出匕首,逼阿福交出钱。阿福不肯束手就擒,和歹徒在公路边扭打成一团。混乱中,刀锋刺进下颚,剧痛之后,他眼前一黑倒在地上。 阿福只记得醒来时已经在小诊所里,脸和耳后都是血。医生在昏暗灯光下只看到皮肉伤口,简单清创缝合,没有安排任何影像检查。歹徒后来被抓,案件划上句号,阿福以为只是挨了一顿打,从未想到一截十厘米长的刀刃已经留在颅底。 一段时间后,阿福发现嘴巴像生了锈,张口越来越费劲,吃饭咬不动,曾经爱吃的酒肉也尝不出滋味。紧接着,头痛一次次找上门,那种痛就像有根细钉在脑壳里慢慢拧。嗓子总像卡着什么东西,吞咽困难,鼻血也常在吃饭、睡觉时突然流下来。 阿福和妻子多次去镇上医院和牙科求医,检查结果总被告知没大问题,有时被当成牙病,拔了几颗本来没有大碍的牙。止痛药和消炎药像饭一样往肚子里吞,药效压住了炎症,却把真正的病灶遮蔽起来。几年下来,阿福被折磨得形容枯槁。 最难堪的是那股味道。大约从2010年起,他口中开始散出怪味,像夏天坏掉的肉,又混着金属锈味。慢慢地,整个人仿佛都笼在这股气味里。 小卖部顾客被熏走,生意一落千丈。妻子夜里不得不搬到隔壁房间睡。在外打工的哥哥回家,一进门就被熏得皱眉后退,认定阿福身体里出了大问题,非得去大医院。 于是有了省城医院这一幕。常规检查依旧看不出所以然,直到神经科医生用手指按到阿福左侧下颌深处,阿福像触电一样全身发抖,冷汗直流。医生在皮下摸到异常坚硬的东西,立刻让他做X光和CT。 影像挂上灯箱的那一刻,诊室一下安静下来。黑白图像里,一截扁宽的金属片从下颌骨一路斜刺向颅底,占据头颅相当大的空间,刀尖直指咽后壁,距离颈内动脉和脑干只有几毫米。那更像一张尸检片,而阿福此时却坐在椅子上说着话。 医生把结果告诉阿福时,阿福愣在原地,多年前那场抢劫的碎片记忆一下子拼在一起。那把断柄的匕首并没有完全离开身体,而是在小诊所被忽视后,与血肉共存了五年。 金属在温热体液里缓慢生锈,锈斑侵蚀周围组织,引发反复感染,身体试图用纤维包膜把它包裹住,炎症却在封闭空间内顽固燃烧,那股腐臭正是深处组织一点点坏死的味道。 要想活下去,就只能把这枚“定时炸弹”取出来。对阿福来说,恐惧不止来自手术风险,还有昂贵费用和随时可能失败的结果。阿福一度从医院逃回家,觉得自己撑了这么多年,也许还能熬下去。 最后,是妻子的坚持、家人的眼泪和医院同意减免部分费用,让阿福重新回到手术室。阿福在同意书上签下名字时已经明白,继续拖下去,只能在恶臭和疼痛中慢慢耗尽生命,不如赌一次。 无影灯下,主刀医生在显微镜辅助下沿着事先反复演练的路径,一点一点分离与刀刃黏连的组织。每挪动一毫米,都必须避开密集的神经和血管,一旦失手,就是大出血或瘫痪。 几个小时后,那截锈迹斑斑的金属片终于被器械夹出,落入弯盘发出一声轻响,手术室里的人几乎同时松了口气。 术后,折磨阿福多年的头痛和腐臭迅速消退,小卖部里不再有那股刺鼻的气味,阿福重新可以痛快张嘴吃饭,说话声音也变得清亮。乡亲们都说阿福命大,一把刀在脑袋里待了五年,人竟然没死。 医生则把这个病例当成教材,提醒自己,面对长期说不清原因的疼痛,不能轻易说“没事”。那截被忽视的刀刃终于被取出,那五年的惊心动魄和一次次被误读的求救信号,却会像下颚那道疤一样,永远刻在阿福和许多人的记忆里。

![[点赞]2024年,浙江一女子反复发烧一年多,为了治病花了80多万不见效,结果](http://image.uczzd.cn/478482308589917091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