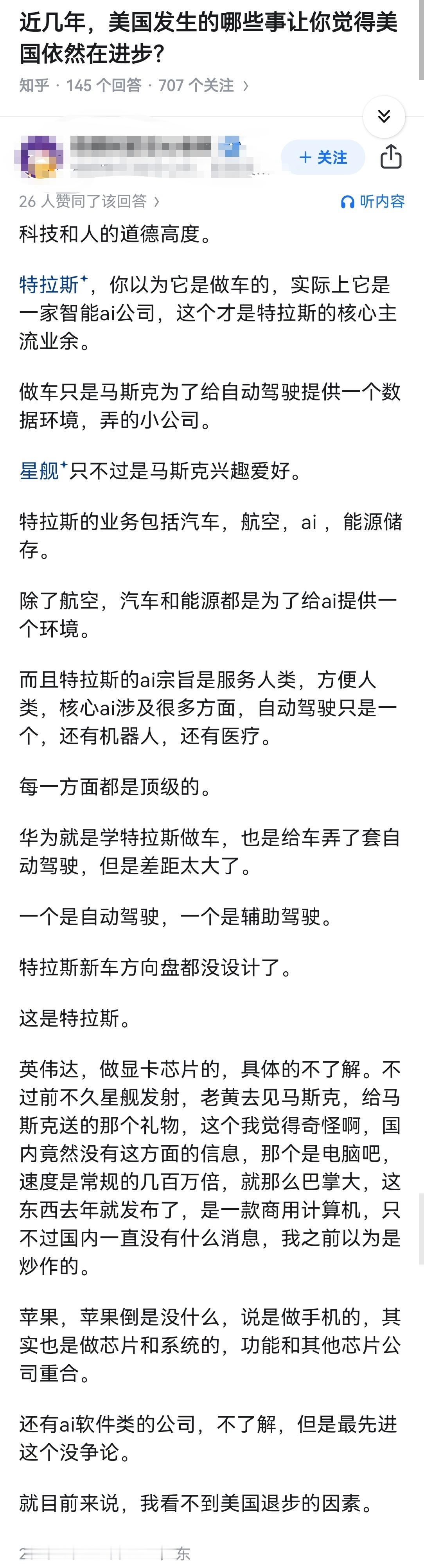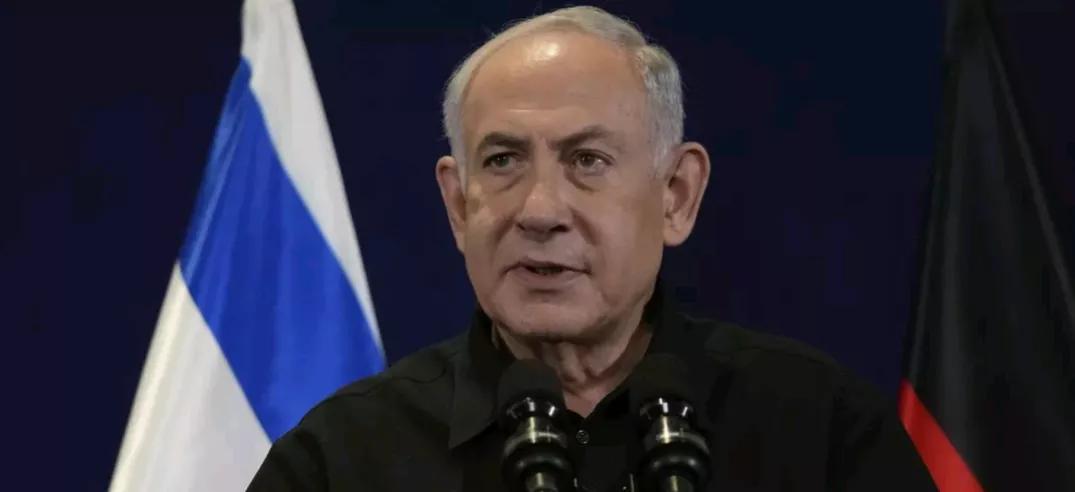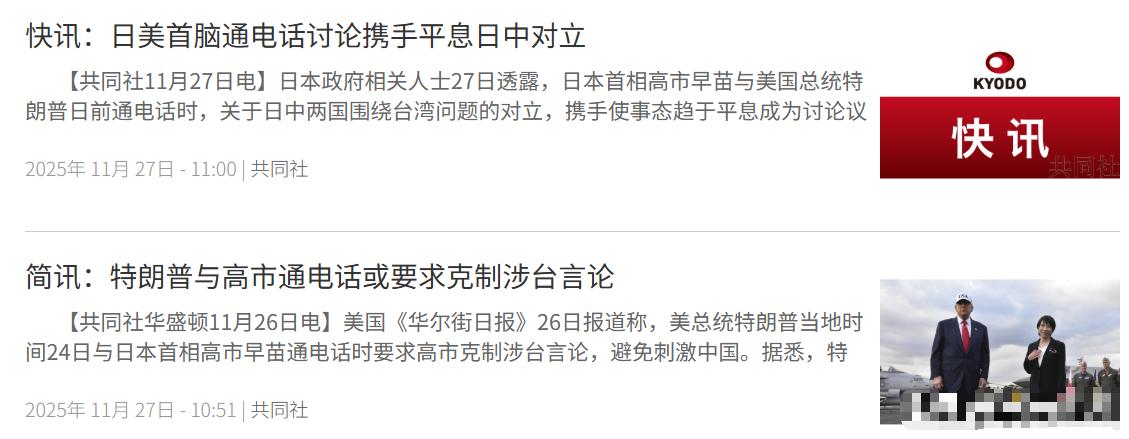英国能够称霸只是因为印度? 当欧洲列强在北美为皮毛打架、在非洲为部落征税头疼时,唯有印度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印钞机,用血泪喂养着大英帝国的每一寸扩张。 1765年普拉西战役后,东印度公司的账本开始疯狂跳动:孟加拉农民的田赋从莫卧儿时代的30%飙升至80%,丰年不增赈、灾年不减税,1770年的大饥荒饿死1000万人,英国人却在伦敦用搜刮的粮食期货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敲骨吸髓的税制,让印度每年向英国输送的财富,相当于3/4个《辛丑条约》赔款——当同时 期北美殖民地还在为茶叶税暴动时,印度农民连反抗的力气都被饥饿抽干了。 当曼彻斯特的蒸汽织机开始轰鸣,英国需要的不仅是棉花,更是一个能吞下所有工业品的无底洞。1813年英国议会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印度瞬间沦为自由贸易的屠宰场。 本土棉纺织工的白骨铺满恒河平原,达加城人口从15万锐减到3万,而英国棉布的倾销额30年增长20倍。 更狠的是铁路计划,英国人强迫印度用财政担保修建5万公里铁路,每英里造价是美国的9倍,却只为把曼彻斯特的布头送到最穷的村庄。这些钢铁动脉像吸管,把印度内陆的粮食、棉花吸干,再塞满英国的工厂和仓库。 金融绞索则是英国人的终极武器。三家管区银行在印度放高利贷,农民为缴税不得不借债,负债率高达99%,一个村庄的欠款竟相当于千户年收入。 汇兑银行垄断外贸结算,从孟买到利物浦的每一包棉花,都要经过伦敦金融城的层层扒皮。 最精明的算计是殖民地公债——英国用印度的税收抵押,发行4.5亿英镑债券,每年坐收4%利息,这些钱又被投入印度铁路和种植园,形成“吸血-投资-再吸血”的闭环。 据统计,1765到1900年,英国从印度抽走的财富达64.82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时期全球GDP的1/3。 对比其他殖民地,更显印度的不可替代性。北美殖民地闹独立时,英国每年倒贴100万英镑军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开发成本远超收益。 非洲部落分散,征税成本比税收还高。唯有印度,能用200万英镑的行政成本,榨出4400万英镑的净收入。 当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去加拿大时,路易十五或许不懂:英国真正的命根子,是印度农民背上的田赋、孟买码头的棉花、加尔各答银行的账本。 当然,英国的海军和工业革命并非不重要,但这些力量的底色都是印度染红的。18世纪英国海军的扩张,本质是为保护印度航线,从好望角到马六甲,每一座炮台都用印度税收建造。 工业革命的技术迭代,离不开印度市场的需求刺激——兰开夏郡的织机,每转动一次都在回应印度村庄的敲门声。 就连英国的“自由”价值观,在印度都变成了刺刀下的掠夺逻辑:当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兵用印度土兵镇压起义时,伦敦的政客们正用印度的财富,在议会辩论“文明使命”的高尚性。 历史的残酷在于,英国的称霸从来不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神话,而是一场精准的吸血手术。当维多利亚女王戴上“印度女皇”的冠冕时,王冠上每一颗宝石都沾着印度农民的血。 北美殖民地会独立,加拿大草原会荒芜,但印度不会它像被钉在案板上的巨兽,任由英国宰割了两个世纪。 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制度或技术有多优越,而是因为印度的富庶与脆弱,刚好填补了帝国扩张的所有胃口。 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英国的全球霸权才真正开始崩塌,那些曾被印度财富掩盖的缺陷,终于在失去供血后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