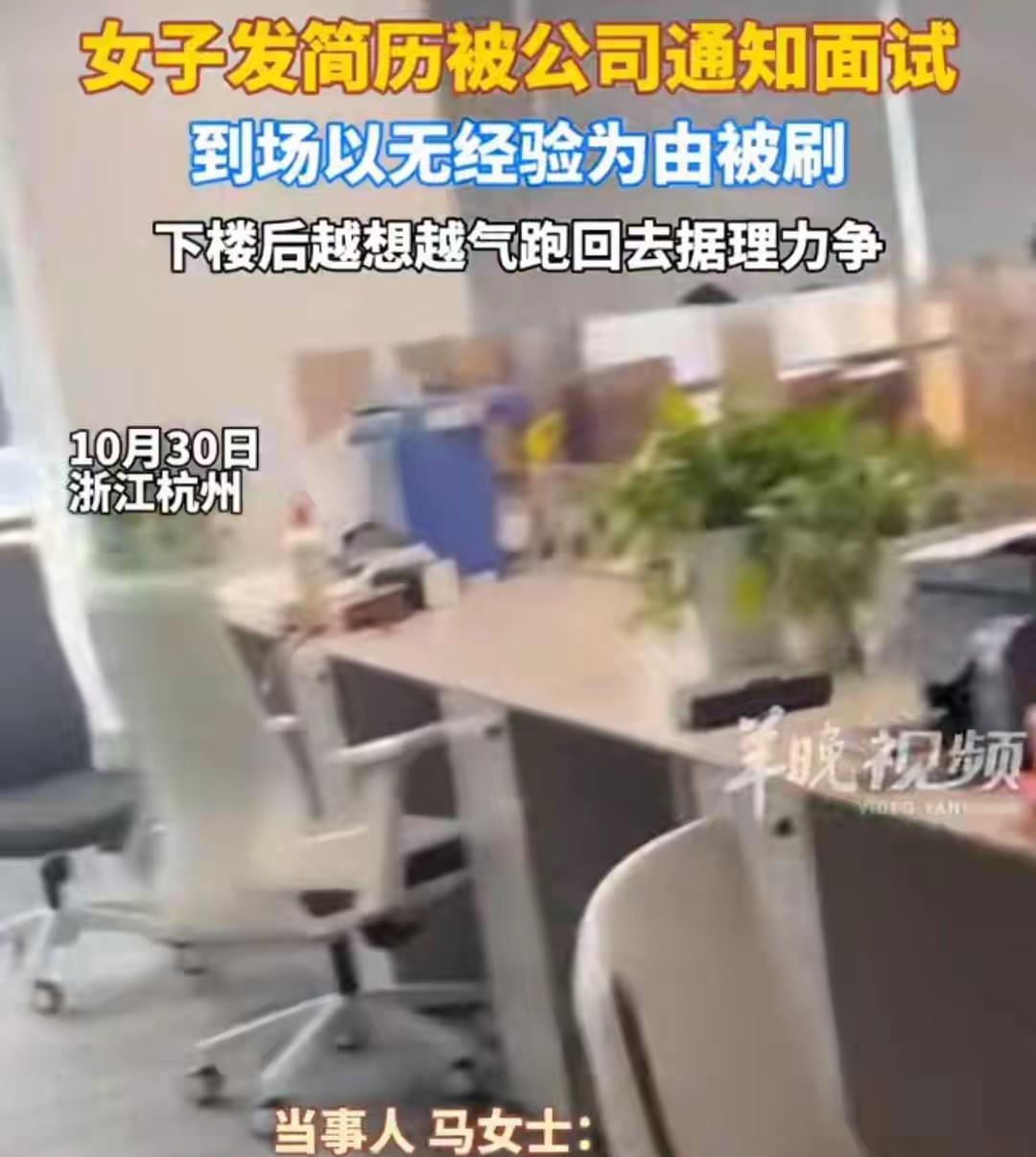90岁的杭州老人李大惠,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
他是一位“镜面人”,心脏长在右边,内脏器官与常人相反。这种极为特殊的生理情况,出现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他出生于抗战年代,求学于新中国,做过10年中学教师,从事过水利制造行业,获得过国家专利,曾负责15万吨啤酒生产规模扩建工程。
这个秋天,他在捐献申请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想再有人像我这样遭罪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大惠在江西康复医院做X光检查时,医生跟他说:“你的心脏长反了”。但他平时也没觉得不舒服,就没放在心上。
1993年的一场手术,让他有了捐赠遗体的念头。
那一年,他突发阑尾炎被送到了医院,术前,他提醒医生自己是“镜面人”,但主刀的年轻医生并未重视,仍按常规在右下腹寻找阑尾。久寻无果后,出血量逐渐增加,手术陷入僵局。
后来,主任医生赶来,在腹腔中央开了一个大切口才找到盲肠,整场手术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
那次手术,给李大惠留下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
后来,他去体检时,常有年轻医生围着他说,“教科书里的案例终于见着活的了”。
说起这些经历,李大惠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想啊,我这身子骨特殊,要是百年后能捐给医学院,让更多医生摸清‘镜面人’的身体结构,就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遭罪了。”
李大惠出身于“杏林之家”,大姐、大姐夫是江西知名的医生,妹妹一生扎根基层医疗,家族里还有一位孙辈,如今是杭州市中医院肾内科医生。
“家里人都懂医,知道遗体捐献对医学教育和研究有多重要。”李大惠说,家人的职业让他对“奉献”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
30多年前,遗体捐献渠道并不顺畅,他多方打听,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机构,只好暂时搁置了心愿。如今,在各方的协调与努力下,他的心愿终于得以完成。

当他把捐献遗体的想法告诉家人时,小女儿李萍一点都没觉得意外:“我爸向来有主见,一辈子老实本分、乐于助人,做出这个决定,太符合他的性子了。”
在钱塘区义蓬街道仓北村,李大惠是出了名的“公道人”,邻里闹矛盾,都爱找他评理。
“他做的决定,我们都信得过,更会全力支持他。”李萍说。
远在日本读博的外孙女也打来电话:“外公,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捐献遗体,为医学做点贡献。”
遗体捐献流程,82岁的老伴冯玲亚比李大惠还门清:“申请书怎么填、找谁对接,我都问得明明白白的。”
不过,她也在悄悄担心:“他身体这么好,万一我走在他前头,后续的事,怕帮不上忙。”
以工业报国
1958年,23岁的李大惠考入江西轻工业学院机电工程系机械制造专业预科班,理想是成为“李工”,“以工业报国”。
上课时,他总是坐在第一排,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当时,南昌钢铁生产基地缺人手,他主动报名去了一线,背着炸药雷管往山里跑。好几次,让老师同学躲在安全区,自己孤身去排除哑炮;铸造车间最苦最累,他裹着满是油污的工作服,一待就是一整天,勤工俭学的工资全部用来买了专业书。
凭着这股拼劲,他成了院务委员和系学生会主席。
1962年,李大惠在毕业的前一年,被下放回乡务农。
回到家乡后,他成为了头蓬中学的一名老师。当时,这所计划迁址到新围垦地上的学校尚是一片空白,他亲手设计了学校图纸,规划了教室、办公室、厨房、公厕等设施,还有室外大操场、球场和学农基地。办校事情繁琐,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载着大队书记去跑建校手续。最终,新校在众人的努力下建成了。

成为乡村教师后,李大惠的生活稳定了下来。30岁,经人介绍,他与冯玲亚结为夫妻,两个人鹣鲽情深,共同度过了60年的幸福婚姻,并抚养了两个女儿。
“当老师安稳,但我心里还是念着机械制造。”1973年夏天,萧山围垦农机修造厂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攥着邀请信,连夜收拾行李跑到了工厂。
车间里没有像样的制图工具,他就用硬纸板剪出模具;技术资料一片空白,他拉着冯玲亚当助手,让她帮忙描图、整理数据,自己趴在桌上画图,经常画到通宵。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李大惠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大展身手,他参与设计的4ZN-12自吸式泥浆泵,拿了省科技成果奖,独立研发的自吸微型泵捧回了国家专利证书,是当时“最小最轻水泵”。他也因为成绩突出,被省农机学会和中国沼气协会吸纳为会员。
后来,李大惠又去萧山啤酒厂主持了15万吨规模的扩建工程,站在轰鸣的车间里指挥施工。他还在传化负责厂房修建,在省高科技示范园区的工地上晒得黝黑。
随山河入海
回顾一生,李大惠一直很“卷”,直到退休,他才放慢脚步,背着相机去旅游,自学剪辑和电脑制图。

今年年初,凝结李大惠7年心血、近5万字的自传出版,记录了他平凡但精彩的一生。
书里有家人对他求学的托举、有对老伴多年陪伴的感恩、有怀抱“工业报国”理想却又多年沉浮的酸甜苦辣。
对身后事,李大惠也有自己的想法:将骨灰撒向山川河海,回归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