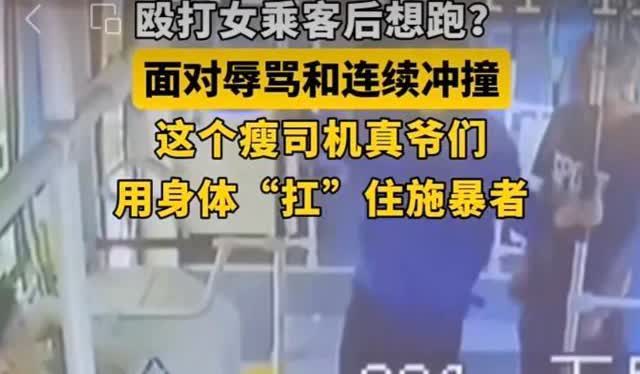我坐动车回老家,一位美女坐了我的座位,我提醒她:美女这是我的座位。 她抬起头时,我看见她眼下的乌青,像被夜色浸过的棉絮。“不好意思。”她起身时动作有些迟缓,右手下意识往小腹按了按,帆布包里滚出个药盒,布洛芬的字样在车厢灯光下晃了晃。我把药盒捡起来递过去,她指尖的温度比矿泉水瓶还凉。 放行李时,她的箱子卡在行李架缝里,拉链崩开个小口,露出半截婴儿襁褓。“我来吧。”我托着箱底往上推,她踮脚去拽拉链,发梢扫过我手背,带着点淡淡的艾草味。“谢谢你。”她重新坐下时,脸色比刚才更白了些,额角沁出层细汗。 动车刚过长江,她突然弯下腰剧烈咳嗽,手死死攥着座位扶手,指节泛出青白。我从包里翻出包纸巾递过去,瞥见她手机屏幕亮着——聊天记录停留在凌晨三点,最后一条是:“妈,我带小宝回家过年,您放心。” 广播报站时她猛地惊醒,慌乱地摸向腹部,脸色瞬间褪成纸色。“怎么了?”我扶住她发抖的胳膊,感觉她体温烫得吓人。“我……我好像要生了。”她的声音碎在急促的呼吸里,帆布包滑落在地,露出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小袜子,粉白相间的,像两只刚破壳的小鸡。 周围的乘客炸开了锅。有人喊找列车员,有人翻急救包,我蹲下去捡散落的婴儿用品,发现包底藏着张皱巴巴的产检单,预产期就在三天后。她咬着嘴唇往座位底下缩,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淌:“本来想赶在年前到家……” 列车员带着急救箱跑过来时,她已经开始发抖。“下一站要四十分钟。”列车员看着她的样子急得直搓手,“谁懂点护理?”我突然想起妻子生产时护士教的呼吸法,蹲在她面前按住她的手:“跟着我吸气,慢慢数到五。”她的指甲掐进我手背,却在听到“呼气”时努力放松,像株在风雨里拼命稳住根须的小草。 后排的大姐把羽绒服铺在地上,前排的大叔搬来行李箱当枕头。她疼得哼出声时,我就给她念手机里搜来的顺产知识,念到“产妇要补充能量”,穿校服的小姑娘递来巧克力,戴眼镜的大哥拧开保温杯:“刚泡的红糖水,我闺女坐月子时喝的。” 她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像要捏碎骨头:“我男人……在工地上摔断了腿,我想让孩子……在老家出生。”血顺着她的裤腿渗出来,在羽绒服上洇开朵暗红色的花。我突然想起妻子生儿子那天,也是这样攥着我的手,产房外的阳光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 广播里传来紧急通知,列车将临时停靠中途站。她被抬上救护车时,突然抓住我的衣角:“帮我……拿一下包。”我跟着跑下车,看见救护车顶上的红灯在站台的雪雾里明明灭灭,像她刚才眼里的光。 三天后,我在老家收到个陌生包裹。里面是双婴儿鞋,鞋底绣着对小老虎,还有张字条,字迹歪歪扭扭:“谢谢您,小宝平安出生了,是个男孩。他爸说,等他能走路了,就教他给您鞠躬。” 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妻子抱着儿子喂奶粉,小家伙的手攥着我的手指,软乎乎的。我突然明白,所谓双向奔赴,不一定是朝同一个方向奔跑,有时是你帮我扶一把摔倒的人,我替你圆一个未说出口的愿。就像这列载着归心的动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却在某个瞬间,因为一份突如其来的善意,让彼此的旅途都暖了几分。 生活本就是无数个擦肩而过,那些愿意为陌生人停下脚步的瞬间,才让这趟单程列车,有了不孤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