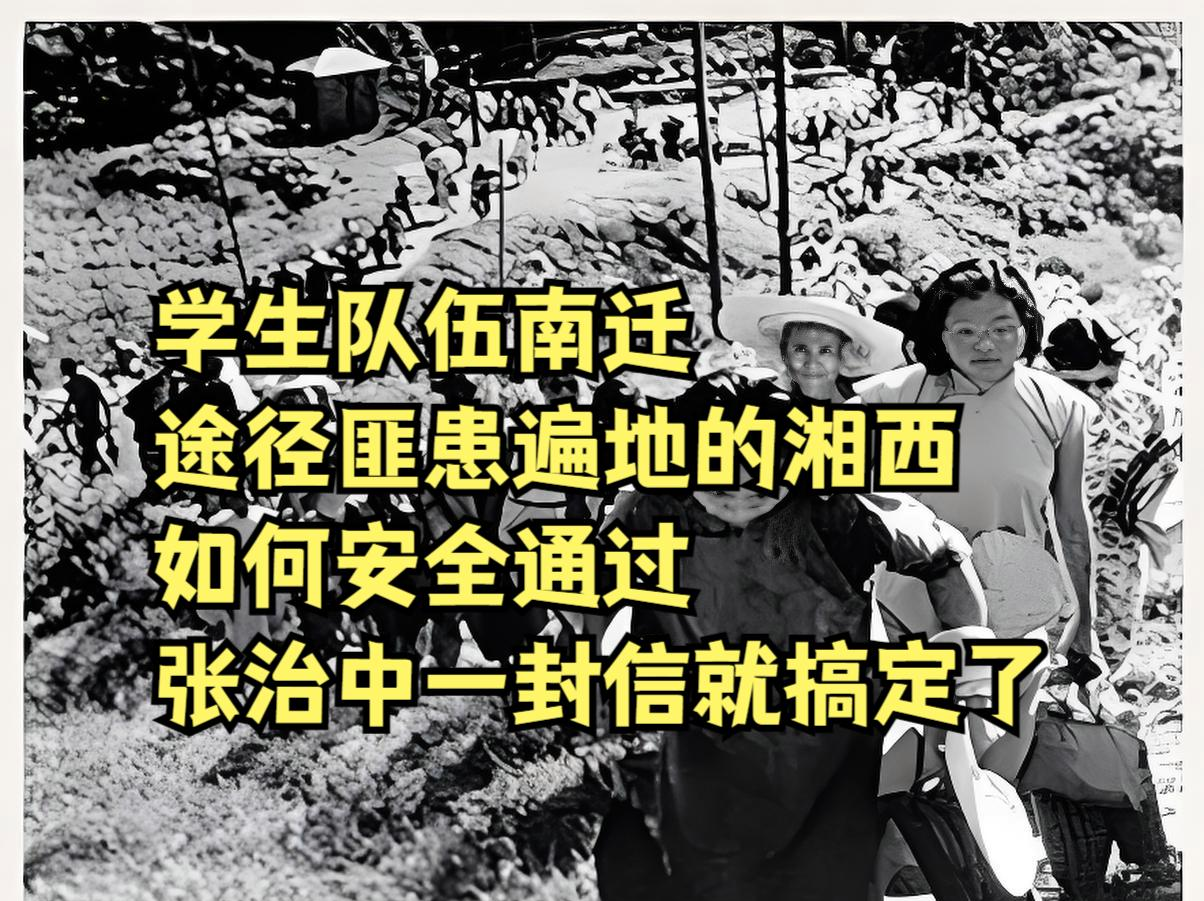1938年早春时节,有三百多名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们要穿越那土匪到处都是的湘西地区,听上去这简直就像是去送死,然而他们却偏偏平平安安毫发无损地走了过去,他们不是依靠枪支,而是凭借着一封信。
一封写给土匪的信动身之前,湖南省的主席是张治中,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是谁都想象不到的。他把信纸展开,朝着沿途的那些土匪头子,一个一个地去写信,给他们的称呼是“好汉”。信里面讲,这些学生乃是国家读书的种子,他们要前往昆明继续念书,诚恳地请求各路好汉,从民族大义这个层面来看,能够给他们一条活路。
信的落款那儿,张治中规规矩矩郑重其事地盖上“绥靖主任”的官印。这枚印清清楚楚是一种警告:倘若谁触动了学生,全省有着正规编制的军队就会深挖土地达到三尺深度,铲平山寨。以恩惠与威严同时施加,分寸把握得精准恰当。
这一批信件叫专人骑着快速奔跑的马送出去了,没有人晓得土匪们接到信件之际是怎样的神情,仅仅清楚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证实,他们的确认可了。
山沟里的枪声旅行团踏入湘西地域之后,最为惊险的那一晚于荒山野岭进行宿营,夜深人静之际,附近山沟当中忽然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子弹呼啸着将夜空划破,学生们被吓得蜷缩成一团,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那一个夜晚,显得格外漫长,有人已然在开始想象土匪冲进营地的那种场景,有人偷偷地把最为重要的笔记本塞进贴身的衣服里面,一直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枪声才慢慢地逐渐停歇下来。
破晓之后去打听一番才晓得,压根就不是冲着他们而言的——乃是两拨土匪在互相火并争夺地盘。他们彼此打得极为惨烈,然而对于近在咫尺之处的学生队伍却仿若视而不见。那一封张治中的信件,变成了无形的结界,将凶险给阻挡在了外面。
八公斤的极限定好的规定是每人限重乃是八公斤,这可是出发之前就已然定下的铁律。闻一多先生往背包里塞进去的是画板以及颜料,李继侗教授所携带的是地质锤还有标本盒,学生们是尽可能地进行精简,有的人仅仅带了两双草鞋和几本课本。
第一天,经过急行军之后,接近所有学生的脚底板,都磨出了血泡。草鞋撑不上两天,就烂到没法再穿,于是有人干脆光着脚,踩在泥泞的山路上。脚上被磨出的血泡破了之后结痂,痂掉了以后又磨出新来的泡,如此反复不停。
食物是黑面饼以及硬饭团,咬一下腮帮子好痛。居住之处是破庙、戏台,铺垫之物是爬满跳蚤的稻草。然而他们慢慢发觉,人疲惫到极点之际,虱子爬过脸也能呼呼酣睡。
荒野里的课堂这支队伍并未因赶路而将书本搁置一旁,闻一多先生一路前行一路作画,把湘西黔东的山水以及少数民族的服饰全都纳入了画本之中,遇到特殊的地质构造时,曾昭抡教授便蹲在路边,把石头当作粉笔,在地上画给学生观看。
李继侗领着学生敲着石头采集标本,将路边的岩层视作活的黑板,袁复礼教学生辨认沿途的植物,告知他们哪些可食用哪些有毒,晚上宿营之际,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边,有人拿出本子记录当天的见闻,有人整理采集的标本。
以往于课堂之中呼喊“读书救国”,始终感觉颇为抽象,历经全程,每一步皆踏于华夏大地之上,他们方才切实领悟这四个字所蕴含的分量。
溃兵与饼干旅行团在行进到达云南宣威之际,碰到了一队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的川军,那些士兵身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脸部以及身体上存有尚未愈合的创伤,模样显得狼狈凄惨至极。
然而当他们辨认出这乃是西迁的学生队伍之际,有个军官眼眶泛红地走了过来,吩咐士兵将仅存的压缩饼干取出来。学生们加以推辞不愿接受,那军官却坚决地把饼干塞到他们手里,声音颤抖着说道:“你们活着抵达昆明去念书,比起我们打胜仗还要厉害。”。
就在那个时刻,那些溃败的士兵和学生全都陷入了沉默。拿着武器的人是为了保卫国家,拿着笔的人是为了追求学问,在这片已然破碎的土地之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相互守护着?句号随意可为,问号加强语气。
金表退回去在1938年4月接近尾声的时候,有那么一支队伍,队伍里的人面色呈现出菜色模样,身上衣衫破旧不堪,就这样的一支队伍来到了昆明东郊。队伍人数有三百多个,他们历经三千五百里路程,耗时六十八天,结果是零伤亡情况出现,并且零掉队现象发生,此情况使得整个昆明城都为之轰动了。
那些来自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他们为了表达对一路护送的中将团长黄师岳的感激之情,凑集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购买了一块金表,并且准备好了五百元的路费,然后郑重其事地送到了他的面前。然而,黄师岳却将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还另外附上了一封信。
信件之中写明,护送青年学子前往西部迁移,虽说有困苦但却有着荣耀之感,是为国家守护读书的种子啊,只是感觉畅快和荣耀。一路行进过来已经受到情深意厚的招待,再收下厚重的礼物内心实在不安,确实没有办法坦然地去接受。
三千五百里的路途,张治中的信件,土匪之间的那种默契,川军的饼干,黄师岳的那块金表,以及那些送草鞋的苗家老妇人。在这乱世之中身为读书种子的他们,是经由无数双手的托举,方才抵达昆明的。
若假设你身为往昔队伍当中的一名学生,于历经走完这三千五百里路程之后,内心最渴望向何人表达一声谢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