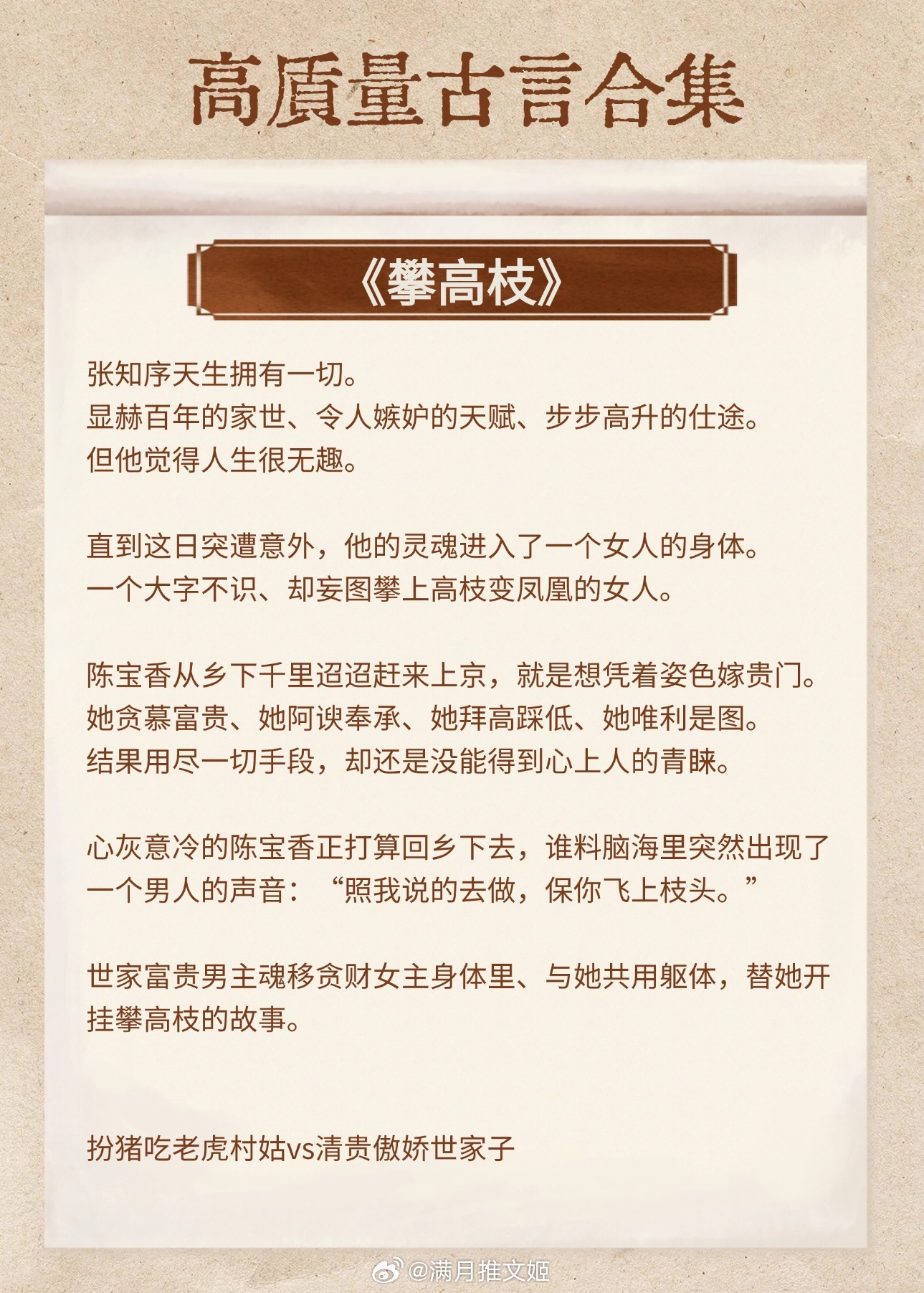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一书的正文没有汉字,我们读者面对书内的英译篇章必须自行推测作品的原文是什么。
书中第四章有一节题为:Leaders of the Jian’an Period: The Three Caos (p.52), 其中用到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为实例。

赵子昂书曹操《龟虽寿》
我们拿曹操《观沧海》《龟虽寿》的原作来对照张译文,发现《观沧海》《龟虽寿》都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作结,而张隆溪教授的书本中却都没有相应的译文。
由于“幸甚……”这两句都在原诗的结尾处,一旦被割舍,就像是诗篇被断尾。本文题目上所说的“断尾”就是这个意思。
《观沧海》《龟虽寿》属于《步出夏门行》题下组诗,《观沧海》《龟虽寿》之外的另外两篇也都使用“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作结。为什么?
如果“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有其重要性,那么,张隆溪教授选择略去不译,理由是什么?
书中还引用曹操的另一乐府名篇,但是,这名篇的题目也被张教授略去,仿如“无题之作”。乐府诗的篇名,是不可译的(untranslatable)吗?
曹操诗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翻译过程中有所损耗(loss/attrition),这些损耗会带来什么影响?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歌以言志……”也见于《龟虽寿》,为什么?
《观沧海》《龟虽寿》等四篇均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作结,为什么?这两句,有何重要性? 我们先读一读张隆溪教授的《龟虽寿》英译版本:
Though the sacred tortoise lives long,
Its allotted time will be spent.
The flying serpent rides on mist,
Will come down to ashes in the end.
The old stallion lying in its stable
Still dreams to run a thousand miles.
A lofty man in his old age
Still wants to weather all the trials.
The time for waning and waxing
Is not all set by heaven.
Cultivating oneself and longevity
Will be one’s own blessing. (Zhang 2023:54)
以上英译诗篇,原作《龟虽寿》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的第四解。下面,我们征引第四解的全文:

元边武书曹操《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由此可见《龟虽寿》汉语原作有十四行,而张教授的英语翻译只有十二行。读者心中生出疑问:张教授不译末二行,原因何在?张教授书中没有交代。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是可有可无的吗?如果为了节省英文版文学史的篇幅就把“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删弃,妥当吗?
其实,《步出夏门行》的四解都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收尾,这是有原因的。这一现象与汉代乐府诗的创作传统密切相关,它涉及文体形式上的规范。
汉代乐府诗(尤其是用于祭祀、宴乐的“乐府歌辞”)在演唱时往往有固定的格式,部分篇目会在结尾加入类似“套语”的句子。据说“套语”可以配合音乐节奏,或者点明演唱主旨。
曹操《步出夏门行》出现重复的诗行,一般认为属于乐府诗之形迹。
曹操《步出夏门行》属于乐府旧题,创作时沿用乐府诗的格式规范。“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正是这类套语的典型。

小川恒男《六朝乐府译注》
此外,曹操撰有《秋胡行》二首,共享了九次“歌以言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曹操集》,1974年版,页11)。
《秋胡行》二首的内容如下: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
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
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
负揜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
惶惶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
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
沉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
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辞赋依因。
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
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飖八极,与神人俱。
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
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
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
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万国率土,莫非王臣。
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
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
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
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从功能上看,“歌以言志”这类句子可能是音乐表演的“提示语”,提示以某种音乐来配合诗篇的情感高潮。
不过,我们目前只有诗篇的文字,我们没有音乐方面的资料可供考究,因此,“提示语”之说,只供参考而已,不能作实。

乐府诗体制的“活化石”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存在,反映了乐府诗形式上的延续性。
曹操的乐府诗虽有创新(例如突破传统题材、融入个人胸襟),但是,沿用旧题的作品仍保留了乐府的体制的若干特征。
《步出夏门行》各篇章结尾使用统一套语,能体现组诗的整体性(陈庆元《三曹诗选评》,上海古籍2018年版,页25)。
周仕慧判定“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是“与音乐或曲调相关的套语”(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页111)。

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换言之,“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是乐府诗体制的活化石。这套语为后人研究汉代乐府诗的演唱形式、文本结构提供了直接证据,也说明了曹操的创作既继承传统,又融入个性(年迈而壮心未已),展现了“借古题写今事”的文学创新。此外,“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与《观沧海》《龟虽寿》两首诗的主旨也是契合的。
是不是凡属《步出夏门行》题下的诗篇皆有相同的篇末套语?这问题有待研究,例如:王运熙、王国安评注《汉魏六朝乐府诗评注》第62页所录无名氏《步出夏门行》,全篇上下并没有“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之类的诗行。
王运熙、王国安说:“诗语意似未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陇西行》四句(“凤凰鸣啾呼”四句)挪补于《步出夏门行》之末,但是,对诗末是否应有“套语”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的解说。
《乐府诗集》明确记载《陇西行》“一曰《步出夏门行》”,二者同属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相和歌辞,郭茂倩《乐府诗集》编入第二十六卷至第四十三卷,共计十八卷 )。
乐府诗人沿用前人之句,还有其他例子。

《汉魏六朝乐府诗》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一》之中,录有乐府古辞《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页384)。此诗末五句,全为唐人陆龟蒙《江南曲》所沿用:
鱼戏莲叶间,参差隐叶扇。
鵁鶄鸀鳿窥,潋滟无因见。
鱼戏莲叶东,初霞射红尾。
傍临谢山侧,恰值清风起。
鱼戏莲叶西,盘盘舞波急。
潜依曲岸凉,正对斜光入。
鱼戏莲叶南,欹危舞烟叠。
光摇越鸟巢,影乱吴娃楫。
鱼戏莲叶北,澄阳动微涟。
回看帝子渚,稍背鄂君船。
可见,原本《江南》古辞的后部每一句均被陆龟蒙衍为一解(陆诗共五解。收录在《乐府诗集》第二十六卷,页390)。
《乐府诗集》第二十六卷中,乐府古辞中“公无渡河”之句,也在不同诗篇中套用(《乐府诗集》,页378、页379)。

《乐府诗集》第二十六卷

怎样对待乐府套语?
对于诗篇沿用乐府套语,其他学者是怎样看待的?
ZONG-QI CAI (蔡宗齐)主编的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 Poetic Culture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T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有《龟虽寿》的英译文:
THOUGH TORTOISE LIVES LONG
Though the tortoise lives long,
Time will come when it meets its end.
Though the dragon can rise high in the mist,
To dust it will eventually turn.
The old steed may be in the stable,
Its heart gallop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A hero may get old,
Never will his ambition abate,
One’s days can be long or short,
Yet all is not up to heaven.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nd your fair share will be prolonged.
How great is my fortune!
I sing of it in this song.(p.105)
上引英文版的最后两行是:How great is my fortune! / I sing of it in this song. (p.106)。这反映译者兼撰稿者(XINDA LIAN 连心达) 没有忽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 Poetic Culture
笔者再查阅其他学者的《观沧海》英译,得知:Burton Watson 笔下的Viewing the Ocean也没有漏掉原诗的最后两行(See Burton Watson trans,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5):
East looking down from Chieh-shih,
I scan the endless ocean:
waters restlessly seething,
mountained islands jutting up,
trees growing in clusters,
a hundred grasses,rich and lush.
Autumn wind shrills and sighs,
great waves churn and leap skyward.
Sun and moon in their journeying
seem to rise from its midst,
stars and Milky Way, brightly gleaming,
seem to emerge from its depths.
How great is my delight!
I sing of it in this song.
Burton Watson的How great is my delight! / I sing of it in this song. 和连心达的译文 How great is my fortune! / I sing of it in this song可以拿来并排对比。我们发现:两个译本的语义差别不大。连心达用my fortune比较贴近“幸甚”的常用字面意义。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1984)
国人李正栓的英译,也没有放弃“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读者可以参阅李正栓的《汉英对照乐府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第173页、第175页、第177页。李正栓似乎将“幸甚至哉”当成“举杯祝酒”的标记:

按李正栓这种阐释,“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幸甚”成了“喜甚”(所以值得喝一杯然后唱歌),结句形成诗篇的自我指涉。
以上所论Burton Watson、连心达、李正栓三家的翻译,都有sing...。这样一来,曹操诗篇(乐府诗)和歌曲的关系,读者可以自行想象(参看本文之末的“附记一”)。

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2006年版。

题为“行”的作品(乐府诗的体裁)
套语之外,诗题本身也有值得注意之处——曹操沿用了不少乐府旧题。
沈德潜《古诗源》收录了曹操《短歌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篇(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90-93)。这些篇名之中都有“行”字。
明代梅鼎祚所编纂的乐府诗集《古乐苑》相和歌平调曲下有所平调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
曹操《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等“四解”,是以乐府旧题所谱写的一组诗章,属于《步出夏门行》(又名《陇西行》),为汉乐诗“相和歌”之瑟调曲。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相和歌辞”被编入卷二十六至卷四十三(中华书局版,页371-636)。
曹操所遗诗篇之中又有《短歌行》两首,被收入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
篇名中的“行”,似是一种乐府体裁(或者类别)的名称。有学者指出,《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中,以“行”为题的诗多达460首之多(周仕慧《乐府诗题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43)。

周仕慧《乐府诗题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汉魏乐府诗题常见“歌”“行”“吟”“怨”“弄”等字(例如《古艳歌》《白头吟》《梁甫吟》《玉阶怨》《江南弄》),一般认为是标示音乐形式或节奏类别的文体名称。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读者参看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的《乐府诗的曲名本事题名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一章。
王运熙直接称乐府诗《薤露》《蒿里》《豫章行》《雁门太守行》等为“曲调”(页329)。
据说,“行”本义为某种乐曲(或谓“行”与“进行”有关,但这是按字面义来阐释,有望文生义之虞),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来研究音乐上的课题,这里“乐曲名(进行)”之说,仅作为参考。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东汉以后,文人沿用旧题写诗,“行”似乎转为诗体标记,成为乐府诗题的固定后缀。周仕慧《乐府诗题名研究》有专立一节考释“行”,结论是:“行”诗是汉乐府诗中重要的一类,“行”与“永”通,二字互训。“永”即歌咏,这是汉人以“行”命名乐府的原因。

周仕慧专立一章讨论乐府诗题“行”
曹操又撰有《薤露》诗,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七。
曹操《薤露》又作《薤露行》,例如:明代钟惺的《古诗归》将曹操的《薤露行》与《蒿里行》并称为 “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我们推测:钟惺所见的底本,诗题作《薤露行》。
沈德潜(1673-1769)《古诗源》也收录曹操《蒿里行》(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92)。
余冠英选注《三曹诗选》中华书局2012年版引作《薤露行》、《蒿里行》。王运熙、王国安评注《汉魏六朝乐府诗评注》也相同(页8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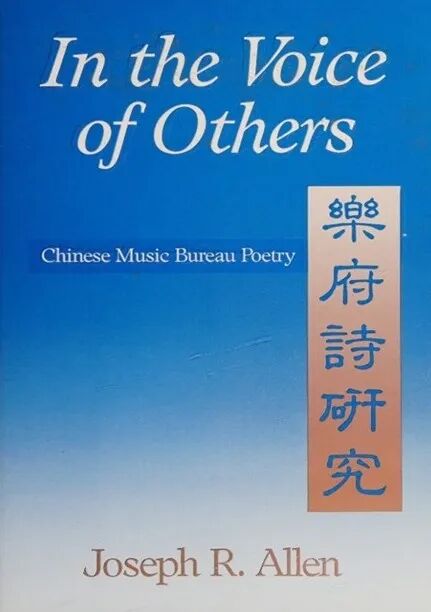
In the Voice of Others Chinese Music Bureau Poetry

篇名上所带的“行”被翻译者忽略
乐府诗篇的篇名上所带的“行”,似乎常被现今的翻译者轻视甚至无视。
英语世界没有相应的文体名称,所以,乐府的“行”似乎就难以翻译(关于“可译性”的探讨,请读者参看:洪涛《“无韵之离骚”之外,又有无韵之文赋——猛批不可译论,结果如何?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九)》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年8月18日 )。
曹操《短歌行》有Stephen Owen的英译(Owen称《短歌行》为SHORT SONG。似乎是用一个Song兼“歌”和“行”),参看 Stephen Owen, ed. and trans.,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 Norton, 1996), pp. 280–281。
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人译作Pipa Xing (translated by Gan Siowck Lee)。这情况大概反映译者不愿意使用ode、ballad等词语。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
在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中,《短歌行》的内文有英译,但是这首诗没有题目——就连Short Song之类的题目张隆溪教授也没有提供给域外读者,只称《短歌行》为his famous drinking song (Zhang 2023:53)。
称为drinking song,是就曹操《短歌行》的内文写饮酒而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
然而,drinking song若用来描述乐府诗中的《短歌行》类别,就不见得合适了——乐府诗题以《短歌行》大概是指诗文配合音乐,诗的内文未必皆写饮宴喝酒,例如,曹操《短歌行》第二首的内容就和饮酒没有关系。
《短歌行》本为汉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传统功能多与宴饮、娱乐相关。曹丕打破这一窠臼,将其转化为纯粹的抒情载体,通过“去酒化”处理,使诗歌摆脱了场景限制,更专注于个体心灵的刻画。曹丕的《短歌行》收录在《乐府诗集》卷三十(相和歌辞・平调曲),内文如下: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
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神灵倏忽,弃我遐迁。
靡瞻靡恃,泣涕连连。
呦呦游鹿,草草鸣麑。
翩翩飞鸟,挟子巢枝。
我独孤茕,怀此百离。
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人亦有言,忧令人老。
嗟我白发,生一何早。
长吟永叹,怀我圣考。
曰仁者寿,胡不是保。

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曹丕《短歌行》全诗表达丧亲之痛,以“白发早生”的生理变化,具象化内心的创伤,呼应“忧令人老”,却无片言只字提到借酒消愁。
总之,《步出夏门行》《短歌行》所涉“行”的体裁标记,竟然像是在一些英语出版物中“不存在”。
如果怀着借文学史书向域外读者介绍中国文体(指“music bureau” poetry)发展为撰写目的,那么,单纯靠翻译恐怕是难以达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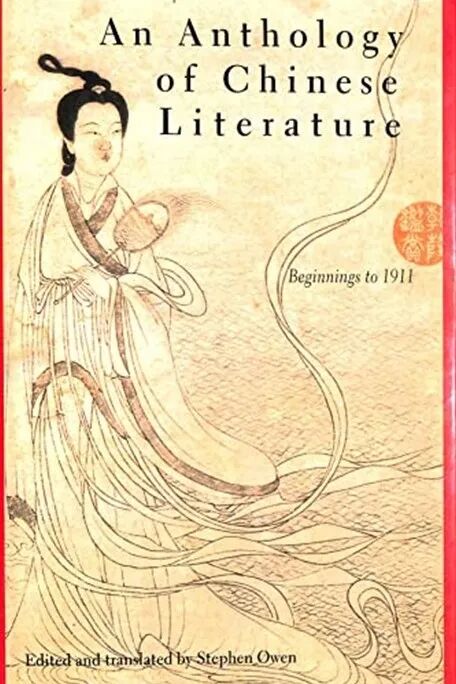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以“行”为题者,杜甫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也属于乐府诗(据孙洙《唐诗三百首》“七言古诗”之后录有“乐府十六首”)。
高适的《燕歌行》也是一样。在题旨方面,高适的《燕歌行》与曹丕的《燕歌行》大不相同(我们也许可以假设《燕歌行》至唐仍存曲调,或者诗中“燕地”正好配合诗题)。
唐诗歌行体可能脱胎自六朝乐府的题材、叙事传统与六朝歌行(鲍照《拟行路难》、庾信《燕歌行》)的体式:以七言为主,杂用长短句;篇幅灵活,抒情叙事并重;辞藻华丽,气韵流畅,李白《长干行》和白居易《琵琶行》都是好例子。

“解”指什么?——体裁上的意义
上文我们提到《龟虽寿》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的第四解。《观沧海》是第一解。这个“解”,张隆溪教授没有提到。
“解”指什么?
《乐府诗集》卷二十六记载:“凡诸调歌辞,并以一章为一解。《古今乐录》曰: ‘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乐府诗集》,页309-310)。
可见,“解”与乐歌的“声”相关。“声”和音乐相关。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
张隆溪教授只讨论曹操的诗文,自然没有必要谈及音乐。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指出《西门行》古辞第四解和第六解之中,有些诗句和《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的前四句和后四句相同,周仕慧认为这种相似性反映“多沿袭少创新,实际上都是乐府诗中的套语,……”(页146)。
周仕慧还提到“艳”的演唱机制影响到歌辞文本的结构、主题情感基调(页147)。郭茂倩说得较直白:“……大曲又有艳……艳在曲前。”或即相当于现在的序曲。
不过,乐府诗的“艳”在作品的体制上有没有形态上的特点?关于这方面,我们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进一步的探讨。

贾晓英、李正栓《乐府诗英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步出夏门行》中的“夏门”。原是洛阳北面西头的城门,汉代称夏门,魏晋称大夏门。
曹操此篇《步出夏门行》,《宋书·乐志》题作《碣石・步出夏门行》。从曹操诗的内容看,与夏门似无关系,曹操应该只是借古题写时事。
曹操是汉末乐府诗创作的重要推动者,现存诗歌中,绝大多数为乐府诗,而且具有鲜明的乐府特征:如曹操《蒿里行》《薤露行》本为汉代挽歌(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2014年版页327),曹操借其题目书写汉末战乱。汉朝挽歌《薤露》如下:
薤上露,何易曦,
露曦明朝更复落。
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首挽歌见于《乐府诗集》第二十七卷《相和歌辞》,涉及人生之生死问题(生命脆弱、人死似不复生)。汉朝挽歌《蒿里》:
蒿里谁家地?
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蹰。
蒿里,是死人葬地。歌词说的是:死这事是无关人之贤愚,死是最平等的。
鬼伯做事最公正,死亡时间到了鬼伯不会让人拖延不死。以下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英译《薤露》和《蒿里》:

《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
Dew on the Onion Grass (Han funeral song)On onion grass the dewdries quickly in the sun,dries in the sun but tomorrow
it will settle again at dawn;
when a person dies he is gone,
never to return.
The Graveyard (Han funeral song)Whose yard is it, the graveyard ?where they muster souls of good men and fools;and the Wraith Master drives them without respite,man's doom doesn't waver a moment. (Owen 1996:278)
换言之,《蒿里》《薤露》歌词泛论人生的处境 (general / universal)。

袁武绘《曹操观海图》
然而,曹操的《蒿里行》则特写汉末之事(specific),全诗如下: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写汉末混战杀戮之残酷,和王粲 (177-217)《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异曲同工。再如,曹操《薤露行》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侧重写外戚何进和宦官张让等相互谋杀及其后果;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侧重写董卓弑逆,致使宗庙化为废墟。
曹操《蒿里行》《薤露行》写战火带来生灵涂炭的恶果,内容仍与丧亡有关。篇名若加“行”字,应有提示之用意。
论者指出,晋朝及晋以后,《薤露》作为葬礼中的丧歌来用的情况还是很多的(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83)。

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有些诗篇的篇名向来不省略“行”字,例如曹操撰有《苦寒行》,此诗反映汉末动乱中军旅征战生活。诗末用白描手法,写出了行军途中的生活艰苦之情形,抒发叹息、忧郁、思归之情。
《苦寒行》这篇名,未见有人省为“苦寒”。西晋陆机(261—303)也撰有乐府诗《苦寒行》,是模拟曹操同名乐府诗而作,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三・相和歌辞八・清调曲一(此外,还有杜甫的《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
曹操一些作品因缺乏明确的乐府旧题依据,又或者体制、内容与传统乐府差异较大,被认为不属于严格的乐府体,例如《秋胡行》、《善哉行》。
曹操《秋胡行》二首“晨上散关山”篇、“愿登泰华山”篇,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六・相和歌辞十一・清调曲四,页524。

元末左克明编《古乐府》(明代新安王文元校刊本)
虽然曹操《秋胡行》题为“行”(乐府诗常见体裁),但是内容偏向游仙、哲理,且句式灵活,与传统乐府的叙事性、纪实性有别(秋胡本事:秋胡戏妻,其妻愤而自尽),更接近文人自创的咏怀诗,只属于“因声作曲”类(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页332)。
曹操《善哉行》三首见于《乐府诗集》卷三十六・相和歌辞十一・瑟调曲一,部分篇章侧重抒发个人情志(如“痛哉世人,见欺神仙”),虽沿用“行”体,但是弱化了乐府的社会现实主题,更具个人化抒情色彩,后世学者对其是否为纯粹乐府体存在争议(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王运熙认为,汉末魏初乐府诗“因调填词”情况占少数(王运熙《乐府诗述论》页335)。他的意思是当时的乐府诗还是和旧题材有关联。

结论: 文人乐府诗
张隆溪教授引录的曹操诗篇三首都和乐府诗相关。张隆溪教授告诉读者:Many of his poems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Han “music bureau” poetry and folksongs。不过,有“活化石”之称的乐府诗特征,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的曹操部分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这样评说曹操诗:“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 。

晋写本《三国志》残卷
从“皆成乐章”看,南朝初,曹操的诗篇和音乐的关系(可成乐章)裴松之似乎仍熟知。
可是,张教授把《观沧海》《龟虽寿》的一部分文体特征(例如套语)割舍了;曹操的《短歌行》,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中,连个正式的题目都没有,遑论“行”这个乐府诗标记。
这情况,可以是因为有意割舍,也可能是出于无意间遗漏。
由于曹操诗篇中乐府诗套句被刊落、原有乐府古题的文体标记被抹去,所以“借古题”没有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得到呈现。于是,用文学史书向域外读者介绍中国文体的目标,完全落空了(张伯伟说:“文学史的核心命题是文体。”语见其《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新论》一文,载《人文中国学报》2009年第15期)。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英语世界的读者,单单读到“music bureau” poetry这名称,怎能了解“music bureau” poetry 情况是怎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
曹操的诗歌以乐府体为主,其创作拓展了乐府诗的题材和表现力,是“借乐府写时事”的典范。总体而言,乐府体是曹操诗歌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注意,这里说的是“内容以外”的形式。
另一方面,在题材、体制上曹操的诗作已超出传统乐府的范畴,带有更多的文人诗个性化特征(曹操写的是他身为汉末领袖的所见所感所想)。
张教授自言撰写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目的是“尽量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接受访谈时所说;文稿2025年刊出)。曹操借乐府古题写出来的诗篇,是民间乐府诗向文人乐府诗发展的明证,这点为什么没有得到张教授的重视?其缘由令人费解。
乐府诗是西方所无,曹操诗篇保留乐府诗的部分形态 (例如:题目用“行”者甚多),自有其特异处,若为强调“中西之同”而将之强行埋没,能说得过去吗?有什么理由?

张煜《新乐府辞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附记一:以视听结合的方式重现曹操《短歌行》
本文讨论到曹操《短歌行》。《短歌行》和乐曲有怎样的关系?
1994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电视剧《三国演义》第37集“横槊赋诗”中,明确呈现了曹操在赤壁战前夜宴上吟唱《短歌行》的情景。
电视剧中的场景:曹操在长江大船上设宴,横槊而立,先以朗诵方式逐句吟诵《短歌行》,随后由杨洪基演唱的配乐版《短歌行》响起,形成“朗诵+合唱”的复合表现。
电视剧镜头:鲍国安饰演的曹操手持长槊,时而指向江月,时而挥向水面,配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等诗句,展现其横槊赋诗的经典形象。

1994年央视电视剧《三国演义》咏唱《短歌行》
在2010年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三国》中,曹操只是诵出《短歌行》。此剧没有采用配乐演唱的形式,而是用台词直接呈现原诗内容。
纯粹口诵《短歌行》这处理方式与1994年央视版《三国演义》中杨洪基配乐演唱的版本形成鲜明对比。
以上所述电视剧剧情,都是依据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情节(第四十八回)将曹操《短歌行》安排在赤壁战前出现(关于张隆溪教授论《三国演义》和赤壁战,请参看洪涛:苏东坡的“周郎赤壁"、史家的书法、小说家的反讽手法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六)。
附记二:《龟虽寿》的诗句
本文讨论到曹操《龟虽寿》。
2017年首播的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张永新执导),于和伟饰演曹操。剧中六十五岁的曹操以旁白的形式提及“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直接用《龟虽寿》的诗句,大概是取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意,以配合垂暮之年的形象。
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逝世,享寿65。一般认为,《龟虽寿》不是曹操日薄西山时的作品。

李可染书曹操诗
附记三:世界文学、“异”的因素
张隆溪教授曾经呼吁世人不要太过强调中西文化之异(来源:中国新闻网2024年8月1日;另可参看洪涛:“毫无影响力”的中国诗篇,怎么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六)。
关心“世界文学”的学者,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谢森说:“‘异’的因素作为东西方文化互通有无的基本条件,不仅不被‘世界文学’所排斥,而且被寄予了极高的肯定和尊重。”(引自谢森《从歌德到顾彬的‘世界文学’观》一文,见陈跃红、张辉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2012年版页149)。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一期
乐府诗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诗歌体裁,植根于中国的音乐、文化与社会传统,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完全对应的文学形式。
乐府诗的独特性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政治的深层关联,也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文学功能、创作机制上的根本差异。
翻译者如果刻意掩盖曹操乐府诗的体裁特征,恐非得宜。
附记四:音乐文体与李白《静夜思》
清人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将李白《静夜思》安排在“五言绝句”之后。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乐府杂题”录有李白《静夜思》:“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1274)。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
乐府诗在《唐诗三百首》之中没有独立成卷,而是分散在四体之后(五古、五绝、七古、七律之后),例如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五言古诗”三十五首之下有“(五言)乐府十一首”,十一首中包括李白的《关山月》、《子夜歌(四首)》、《长干行》;在“五言绝句”中,有李白的《玉阶怨》、《静夜思》(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48年版页40-43、页283-284。邹孟洁《唐诗三百首研究》,花木兰出版社2016年版)。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新乐府序》中明确说到:“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页1262)。这定义颠覆了传统乐府“入乐可歌”的标准,将乐府从音乐文体转化为文学体裁。
我们似乎可以推想: 郭茂倩对诗篇“被于声”的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不过,他说的“其辞实乐府”,我们认为信息量不足。
《静夜思》的选本中的位置反映:有些乐府诗体在唐代可以超越音乐束缚,成为一种兼具题材深度与艺术灵活性的文学样式:“新乐府”。

《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唐天宝大历年间,杜甫乐府诗以“即事名篇、自立新题”见称(方铭主编《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页263),与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前后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