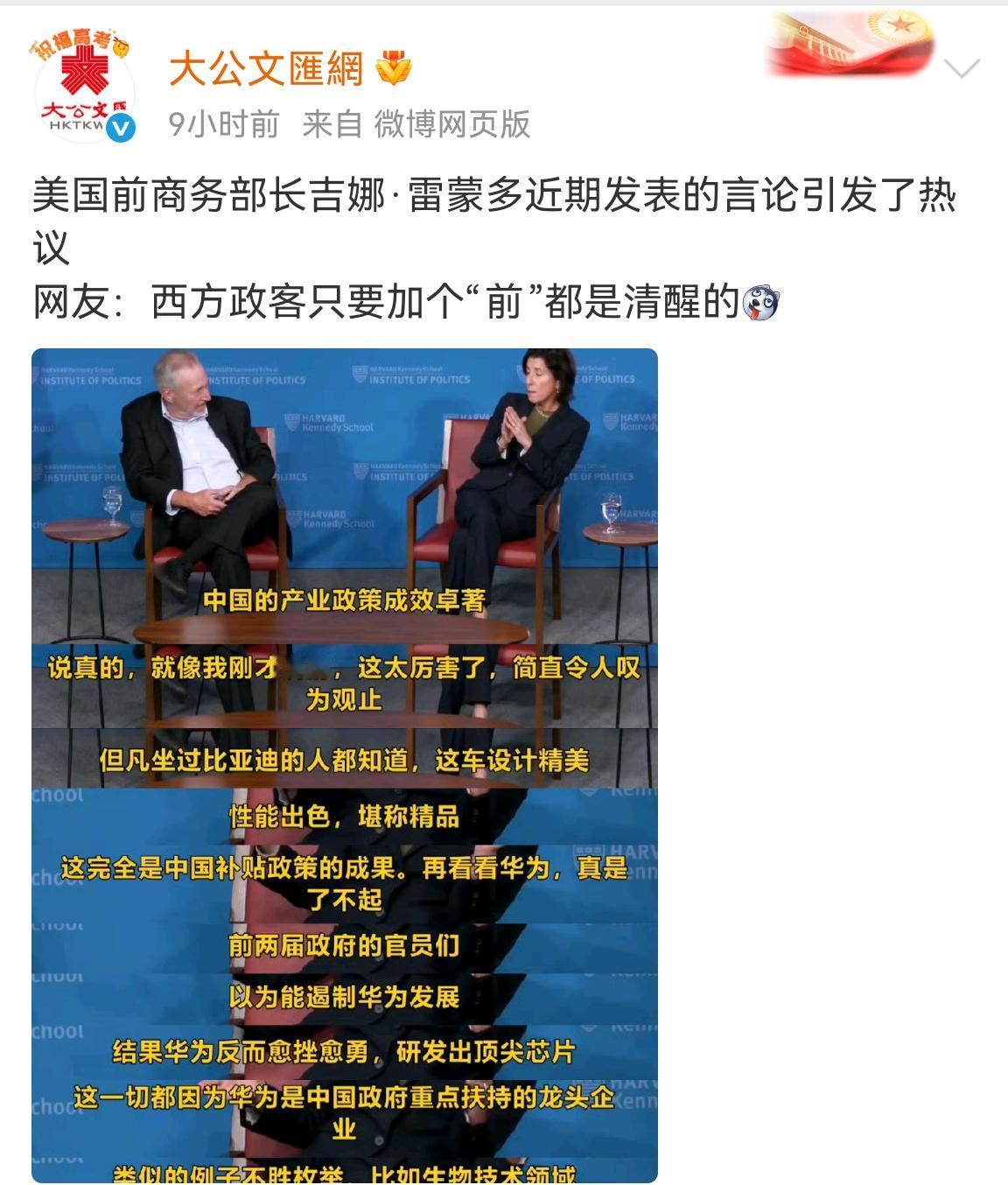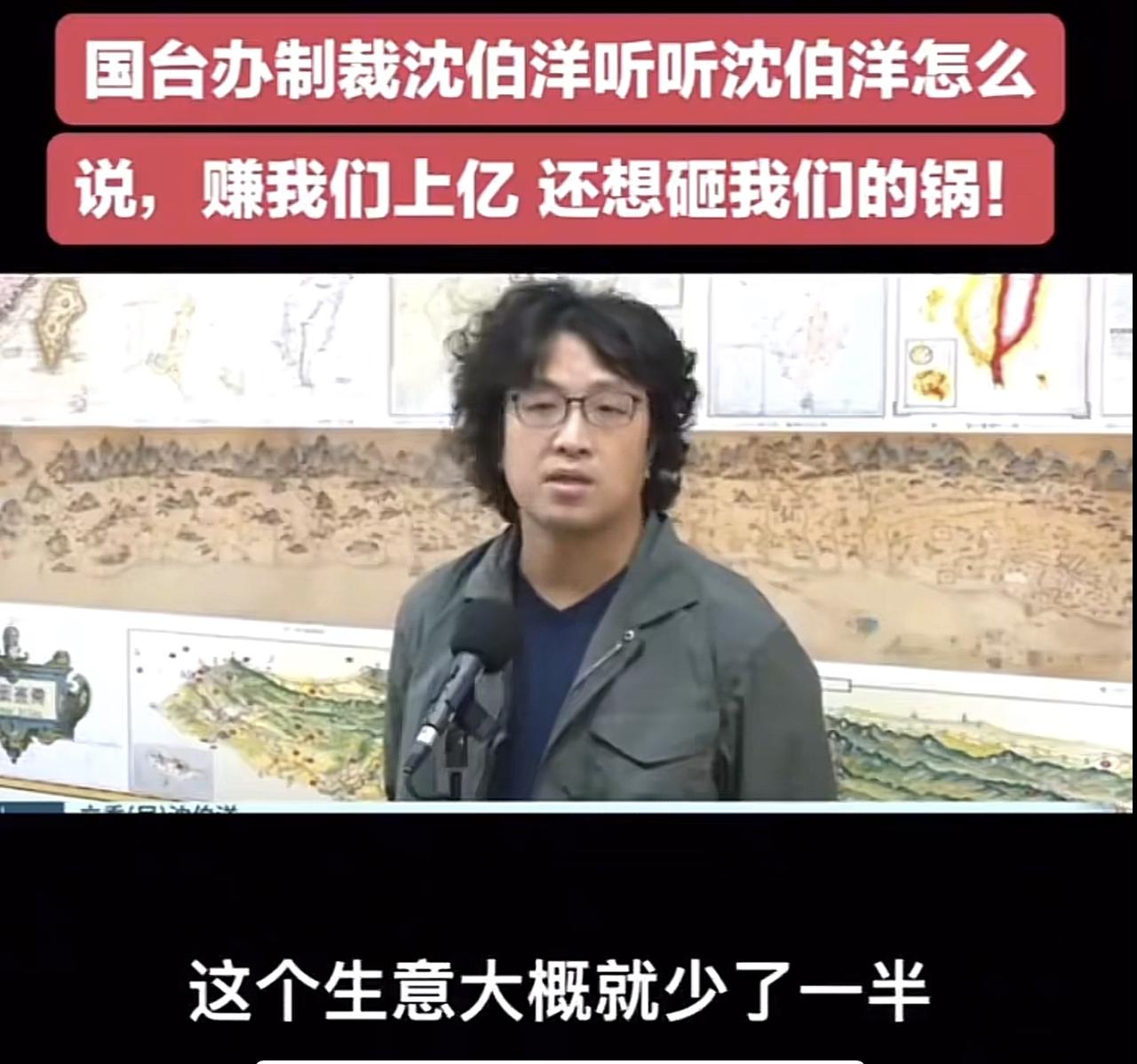2016年11月8日,台江县看守所,一位民警把嫌疑人黄德坤的指纹送进系统。几秒后,屏幕闪红,一组沉睡十八年的比对数据被激活。这场意外,让尘封多年的“凯里两案”突然开口。
谁也没想到,眼前戴着黑框眼镜、刚因经济问题被纪委调查的正科级干部,竟与1998年震动贵州的两起命案指纹吻合。连续十八年,警方几乎年年重新翻卷,却始终差那临门一脚,如今破案的契机却来自一次普通的升迁审查,命运的讽刺味道扑面而来。
镜头倒回到1998年10月17日深夜。凯里市电影放映公司楼道,副所长安坤提着公文包上楼。灯光昏黄,脚步声回荡,他并不知道楼梯拐角处蹲着童年玩伴黄德坤和潘凯平。哑铃、匕首、六十四式手枪——这一连串冷冰器具,在数分钟后带走了他的生命与配枪。
抢到枪的两人原本盯上运钞车,却发现全城戒备陡然升级,硬撞无异于找死。火气难消,目光又落到银行支行行长乐贵建家。乐家住在418医院家属区,高档家电一应俱全,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城足够诱人。两人暗暗踩点,寻找下手的破绽。
12月1日傍晚,他们拎着装满青菜的礼品袋敲开乐家大门。室内刚要寒暄,枪声与尖叫便搅作一团。隔壁邻居刘巧云冲进来,被黄德坤一枪击倒;接着匕首起落,支行长一家三口全部遇害。留下煤气泄漏的假失火现场后,两人带着现金、首饰和纪念币逃离,手段残忍到了极点。

警方迅速并案处理。弹道显示:乐家现场的弹壳正是安坤配枪所出,凶手掌握警用武器,反侦查意识强。可惜当时信息化手段有限,案情像被蒙上厚厚灰尘,只能暂列悬案。专案组来来去去,所有线索终被时间拖得支离破碎。
此后十八年,黄德坤没有远走,他就躲在凯里人的视线里。2000年前后,他给凯里经开区领导洪金州开车。洪仕途顺畅后,黄也跟着水涨船高,先在城管系统拿编外工资,再转劳务派遣,最后戴上正科级帽子。借棚改东风,他的话语权陡增,一手拆迁,一手工程,出入皆众人前呼后拥。
外界看去,这是个典型“能人”——能吃苦、敢摆平、善“沟通”。有人私下议论:“德坤这小子混得真开。”可没人知道,他真正的倚仗不是“手腕”,而是十八年前那把被丢进清水江的六四手枪。那段往事,他不敢提,连梦中都遮掩。
2015年,他又有机会调任更重要岗位。组织部门例行审查,账目问题首先暴露。跟他配合多年的会计被带走,牵出多笔拆迁补偿款去向不明。黄德坤直觉风声不对,却没想到关键点会落在指纹上。看守所录指纹是常规动作,他却再也无法躲过。
指纹一出,专案组连夜重启。六十四式手枪经清水江打捞取证;潘凯平也被控制。面对铁证,昔日发小相对而泣。黄低声嘀咕:“对不起……我赔。”潘抓着头发说:“我怕黑,十八年快疯了。”庭审现场,两人求生欲极强,可受害者的家属和那座小城的阴影再不会散去。

凯里市民至今记得1998年冬天的恐慌。有人夜里听到风吹铁皮声,便以为劫匪又回来了;有人干脆把孩子送到贵阳读书,只因“凯里不安全”。多年后,这些情绪随着城市扩张似乎淡了,可悬案没破之前,街头巷尾仍会冒出一句:“枪手什么时候抓?”
破案靠指纹,听上去像小说桥段,实则是技术进步叠加偶然巧合。最讽刺的一点:为了更高的官位、更好的前途,黄德坤主动配合组织手续,把自己送上了法庭。若不是这次升迁,他或许还能在体制内继续“混”,甚至再进一步。
有人问,十八年里他为何敢留在原地?答案简单:他笃信自己足够了解警方流程,也相信案卷随年月尘封。“案子过了追诉期怎么办?”一个老刑警冷冷甩话:“命案永远没有追诉期。”那一刻,黄德坤的侥幸彻底粉碎。
2020年,一纸终审判决落槌,黄德坤、潘凯平两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此,“凯里两案”终于画上句号。街头不再有警车深夜闪灯,案卷归档,冷灰封裹,却提醒后人:枪声沉寂,但正义不会缺席。
这桩案件让人看到三层意味。其一,技术发展让隐藏再深的恶也会露底;其二,权力并非护身符,反而可能成为自掘坟墓的铲子;其三,友情、金钱、欲望相互纠缠,若没有底线,沦为悲剧只是时间问题。遗憾的是,安坤和乐家四口再无声息;所幸的是,他们的冤沉石终于被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