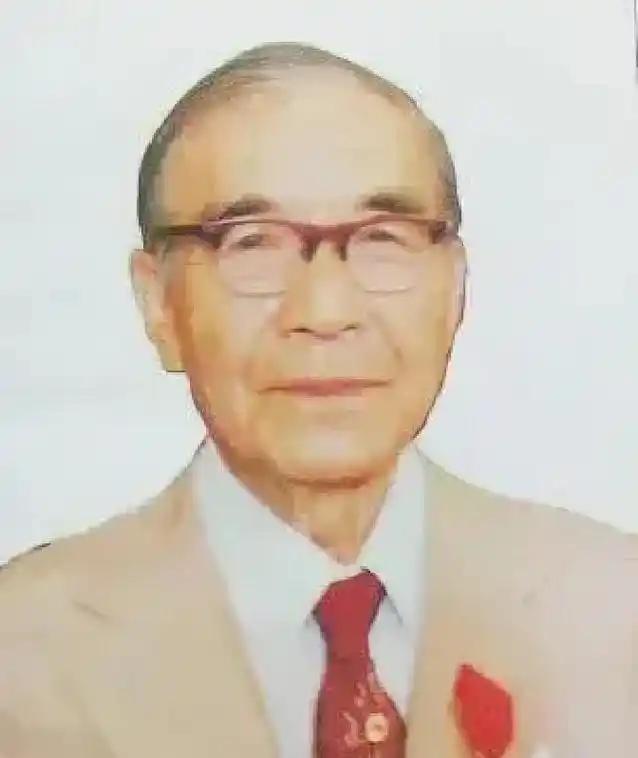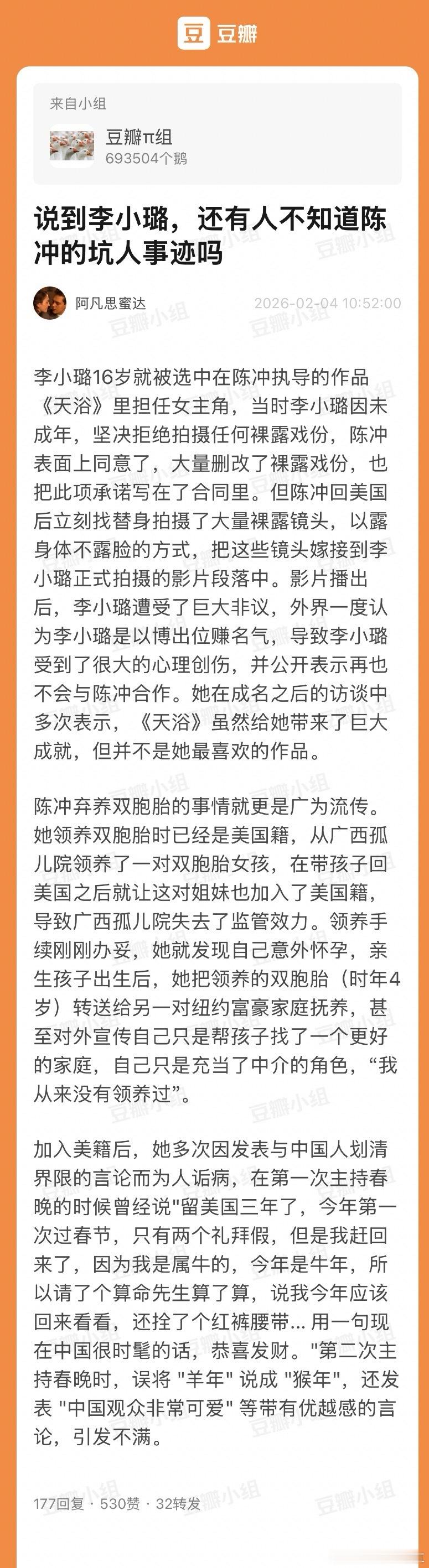资深保姆倾尽心力照顾自闭症小少爷,年终仅得一袋旧衣服,年轻管家拿十万年终奖,保姆离职后雇主带着厚礼跪求救绝食的孩子
......
01
腊月二十八,苏家别墅的空气里飘着昂贵的松露味,还有我身上还没散去的油烟味。
我在厨房忙活了整整六个小时,炸了二十斤丸子,蒸了八笼年糕。
腰像被大铁锤砸过一样,直不起来。

苏太太坐在那张据说值三十万的意式真皮沙发上,正在做手部护理。
旁边站着新来的男管家,小陈。
小陈今年二十六,长得白净,嘴甜得像抹了蜜,更重要的是,他会像哈巴狗一样讨主人欢心。
“太太,您这皮肤真是绝了,十八岁的小姑娘都比不上。”
小陈一边给苏太太递水,一边夸张地赞叹。
苏太太笑得花枝乱颤,眼神里满是受用。
我擦了擦手上的水,局促地站在客厅角落,等着这一年的“年终奖”。
按照惯例,苏家每年年底会发一笔奖金。
第一年我拿了两万,第二年也是两万。
今年小少爷澄澄的情况好了很多,我寻思着,怎么也不会少于这个数。
毕竟,这一年我几乎是住在澄澄房间里的。
“小陈啊,这半年辛苦你了。”
苏太太慢条斯理地从爱马仕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了过去。
小陈眼睛瞬间亮了,但他是个戏精。
他没有马上接,而是假装推辞了一下。
“哎呀太太,这怎么好意思,照顾家里是我分内的事。”
“拿着,这是你应得的。”
小陈这才双手接过,当着我的面,故意拆开了信封的一角。
那一叠粉红色的钞票,厚度惊人。
小陈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声音提八度:
“天呐!十万!太太,您这也太……”
“只要做得好,苏家从来不亏待人。”
苏太太轻飘飘地说道,眼神扫了我一眼。
我心里猛地一跳。
十万。
小陈才来了半年,平时也就是浇浇花,指挥钟点工打扫卫生,或者给苏太太开开车。
真正脏活累活,尤其是照顾那个随时会发疯的自闭症小少爷,都是我。
我期待地看向苏太太。
我不贪心,哪怕没有十万,给我三万也行。
女儿王悦明年想考研,正是用钱的时候。
苏太太终于把目光彻底落在了我身上。
她指了指脚边。
那里放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系着口,看起来鼓鼓囊囊的。
“李姐,这是给你的。”
我愣住了。
没有信封?
没有红包?
只有一个垃圾袋?
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太太,这是……”
“哦,这是我去年清理衣柜淘汰下来的一些旧衣服。”
苏太太漫不经心地看着自己刚做好的指甲,“都是大牌子,有的吊牌还没摘呢。”
“我看你平时也不出门,穿得土里土气的,这些衣服你拿去穿,正好。”
“还有几件羊毛衫,稍微有点缩水,你瘦,也能凑合。”
那一瞬间,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冻住了。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太太,今年……没有奖金吗?”
我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
这话一出,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苏太太皱起眉头,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笑话。
“李姐,做人要知足。”
“这些衣服当初买的时候,一件都不止几千块。”
“这一袋子加起来,怎么也值个五六万了,不比现金强?”
小陈在旁边嗤笑一声,插嘴道:
“就是啊李姐,你也太不懂行了。”
“太太这是心疼你,想让你过年穿得体面点。”
“你那种地摊货的气质,平时穿这些大牌也是浪费,现在白送你还挑三拣四。”
我看着小陈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拳头死死攥紧。
指甲掐进了肉里,生疼。
体面?
拿主人家不穿的旧衣服,装在垃圾袋里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给我,这叫体面?
我伺候了这家人三年。
澄澄发病咬人的时候,是我让他咬着胳膊不松口,生怕他伤了自己。
澄澄半夜尖叫撞墙的时候,是我整夜整夜抱着他哄。
苏太太那时候在哪里?
她在美容院,在牌桌上,或者在国外度假。
现在,她用一袋垃圾,买断了我一年的血汗。
我深吸一口气,把眼泪憋回去。
我是穷,但我也是个人。
我想转身就走,把那个垃圾袋踢翻。
可是我想到了王悦的学费,想到了房租。
我是底层人,底层人的尊严,在钱面前,有时候不得不弯腰。
但我记得,弯腰是为了以后能直起腰。
我没有说话,默默走上前。
弯下腰,提起了那个黑色的垃圾袋。
袋子很轻,但在我手里却重若千钧。
我甚至透过袋子口,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霉味。
“谢谢太太。”
这四个字,我说得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在割我的喉咙。
苏太太满意地点点头,摆摆手:
“行了,回去过年吧,初七早点回来。”
“澄澄离不开人,你知道的。”
我提着袋子转身,走到玄关。
背后传来小陈谄媚的声音:
“太太,您真是太仁慈了,也就是您心善,对保姆都跟亲人似的。”
亲人?
我冷笑一声。
推开别墅沉重的大门,外面的寒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
我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苏家别墅。
这一刻,我伺候了这家人三年的心,彻底凉透了。
02
回到我那个不足三十平米的出租屋时,已经是晚上九点。
屋里开了暖气,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雾。
女儿王悦正坐在小桌边包饺子,电视里放着热闹的春晚预告。
看见我推门进来,王悦立马跳了起来。
“妈!你可算回来了!”
她跑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
看到我提着那个黑色的大垃圾袋,她眼睛亮了亮。
“妈,这是苏家发的年货?这么大一包!”
“是海鲜?还是进口水果?”
王悦一边说,一边把袋子拎到桌上,迫不及待地解开系带。
我没来得及阻止。
或者说,我也没想阻止。
有些屈辱,既然受了,就得让人看清。
哗啦一声。
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被倒了出来,堆在桌子上,甚至压扁了几个刚包好的饺子。
王悦愣住了。
她拿起最上面的一件粉色羊绒衫。
那是一件香奈儿的款式,看着挺高档。
“妈,这……苏太太送你衣服了?”
王悦有些疑惑,“这颜色也太嫩了吧,你能穿吗?”
她翻过衣服背面。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在羊绒衫的后背处,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焦黑破洞。
那是被烟头烫出来的。
而且是很久以前烫的,周围的毛线都起球发硬了。
王悦的手抖了一下。
她不信邪,又拿起下面的一条真丝裙子。
裙摆上,赫然有一大块褐色的污渍。
像是红酒,又像是发霉后的霉斑,散发着一股陈旧的霉味。
再往下翻。
领口泛黄的衬衫、掉了一只扣子的大衣、甚至还有一只穿变形了的单只高跟鞋。
这就是苏太太口中“值五六万”的赏赐。
这就是所谓的“体面”。
王悦的脸色从疑惑变成了震惊,最后变成了通红的愤怒。
她猛地把手里的破衣服摔在地上。
“妈!这是什么意思?!”
王悦的声音都在颤抖,“这是把咱家当垃圾回收站了吗?”
我脱下羽绒服,挂在衣架上,语气出奇的平静。
“这是今年的年终奖。”
“那个管家小陈拿了十万现金。”
“苏太太说,我年纪大了,穿不了好的,别浪费。”
“砰!”
王悦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饺子皮乱飞。
“欺人太甚!”
“妈,这活咱不干了!”
王悦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是心疼,也是屈辱。
“凭什么啊?那小陈才去几天?你会做的他会吗?”
“那孩子发病的时候,他在哪?他在旁边玩手机!”
“上次你去接孩子放学,雨那么大,他开着车经过都不带你一程,害你淋感冒了三天!”
“现在发钱了,他是功臣,你是乞丐?”
王悦抓起那袋衣服就要往外冲。
“不行,我去给他们送回去!”
“我去问问那个阔太太,她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这钱咱不要了,但这口气不能不出!”
我一把拉住女儿的手臂。
王悦力气很大,但我抓得更紧。
“悦悦,别去。”
“妈!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王悦回头看着我,眼泪哗哗往下掉,“人家都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
我把女儿拉回来,按在椅子上。
看着地上那堆破烂,我心里竟然没有刚才那么痛了。
也许是痛到了极致,也就麻木了。
“不去,是因为人家觉得我就值一袋垃圾。”
“你去闹,人家只会报警,说我们敲诈勒索,说我们嫌贫爱富。”
“那个圈子里的人,有一百种方法让你闭嘴。”
我蹲下身,一件一件把地上的衣服捡起来。
动作很慢,很轻。
就像我在捡起自己碎了一地的尊严。
“上周,客厅那个明朝的花瓶碎了。”
我一边捡一边说,“其实是小陈擦架子的时候碰掉的。”
“但他跑去跟苏太太说,是我拖地的时候撞到的。”
“苏太太查都不查,直接扣了我五千块工资。”
“那时候我就知道,在这个家里,真相不重要,谁会讨好主子才重要。”
王悦愣住了:“妈,这事你咋没跟我说?”
“说了有什么用?让你跟着上火?”
我把最后一只高跟鞋塞回垃圾袋,打了个死结。
然后提起袋子,走到门口,打开门,直接扔进了楼道的垃圾桶里。
动作干脆利落。
那一刻,我像是扔掉了过去三年的委屈。
回到屋里,我看着女儿哭红的眼睛,笑了笑。
“悦悦,你说得对。”
“咱不伺候了。”
“妈这双手,能蒸馒头能带孩子,离了苏家,饿不死。”
王悦一把抱住我,嚎啕大哭。
“妈,我养你!我明年不去考研班了,我去兼职,我养你!”
我拍着女儿的后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傻孩子,书还是要读的。”
“妈是为了尊严走,不是为了赌气。”
“今晚我就写辞职信。”
“不过,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初七我去交接,咱们走也要走得干干净净,不落人口实。”
这一夜,窗外的鞭炮声很响。
我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睡得格外踏实。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为苏家受的最后一次气了。

03
我不恨苏太太,也不恨小陈。
恨需要力气,他们不配。
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忘记。
躺在床上,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一桩桩一件件。
导致我心态彻底崩塌的,其实不是这袋旧衣服。
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的根源,是三个月前,澄澄的五岁生日宴。
那场宴会,苏家可是下了血本。
请了全城的名流,光是那个五层的翻糖蛋糕就花了八万。
苏太太穿着高定礼服,像只骄傲的孔雀。
她想向所有人展示,她的儿子虽然有点“特别”,但被照顾得很好,像个小王子。
但我知道,澄澄最怕人多,最怕吵。
宴会开始前,我就提醒过苏太太:“太太,澄澄状态不太好,最好别让他出来太久。”
苏太太当时正在补妆,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
“李姐,今天是好日子,你别乌鸦嘴。”
“让他出来见见世面,要是敢闹,就是你没教好。”
结果,宴会进行到一半,意外发生了。
礼炮“砰”的一声炸响。
澄澄受了惊,尖叫一声,直接掀翻了面前的蛋糕车。
八万块的蛋糕,糊了一地,也糊了旁边几位贵妇一身。
现场乱作一团。
澄澄发病了,他在地上打滚,抓起蛋糕乱扔,嘴里发出野兽一样的嘶吼。
甚至,因为极度惊恐,他失禁了。
尿液顺着他的小礼服流到昂贵的手工地毯上。
所有的宾客都捂着鼻子后退,眼神里满是嫌弃和嘲笑。
苏太太吓傻了,站在那里只会尖叫:“啊!我的裙子!快把他拉开!”
小陈呢?
小陈本来站在澄澄旁边,蛋糕倒的时候,他躲得比谁都快。
看到澄澄尿了,他嫌恶地皱着眉,退到了三米开外,假装去招呼客人。
只有我。
我想都没想,直接冲上去,跪在满是蛋糕和尿液的地毯上。
我不顾澄澄的抓挠,死死抱住他。
“澄澄不怕,婆婆在,婆婆在。”
我贴着他的耳朵,一遍又一遍哼着那首他最喜欢的摇篮曲。
我的头发上沾满了奶油,衣服上蹭到了尿,脸上被澄澄抓出了三道血印子。
那一刻,我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富人眼里,肯定像个疯婆子,像个小丑。
但我不在乎。
我只感觉怀里那个颤抖的小身体,慢慢平静了下来。
半小时后,澄澄终于在我怀里睡着了。
我一身狼狈地抱着五十多斤的孩子上楼。
当我把澄澄安顿好,正在卫生间里用手搓洗那条沾满屎尿的裤子时。
楼下传来了掌声和欢笑声。
我隐约听到苏太太的声音:
“哎呀,真是吓死我了,多亏了小陈管家指挥有方,及时控制了场面。”
“是啊是啊,小陈这孩子真机灵。”
“来,小陈,这杯酒敬你,你是苏家的功臣。”
我在哗哗的水声中,听到了小陈谦虚的笑声。
那天晚上,苏太太给了小陈两万奖金,说是压惊费。
而我?
苏太太嫌弃地看着我那一身脏衣服,皱着眉说:
“李姐,你也太不注意形象了,刚才那样抱着孩子滚,丢死人了。”
“赶紧去洗洗,别把味道带到房间里。”
那天我洗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澡。
皮肤都搓红了,还是觉得自己身上有股味儿。
不是屎尿味。
是那种被人当成透明人、当成工具的酸臭味。
那天晚上,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这个豪门里,会干活的不如会演戏的。
有些付出,在他们眼里是理所当然的贱命。
而有些表演,在他们眼里却是值得嘉奖的才华。
我看着窗外的月亮,摸了摸脸上那道已经愈合的伤疤。
那是澄澄留给我的纪念。
也是我必须要离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