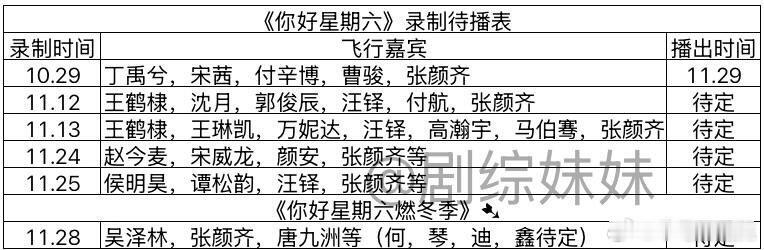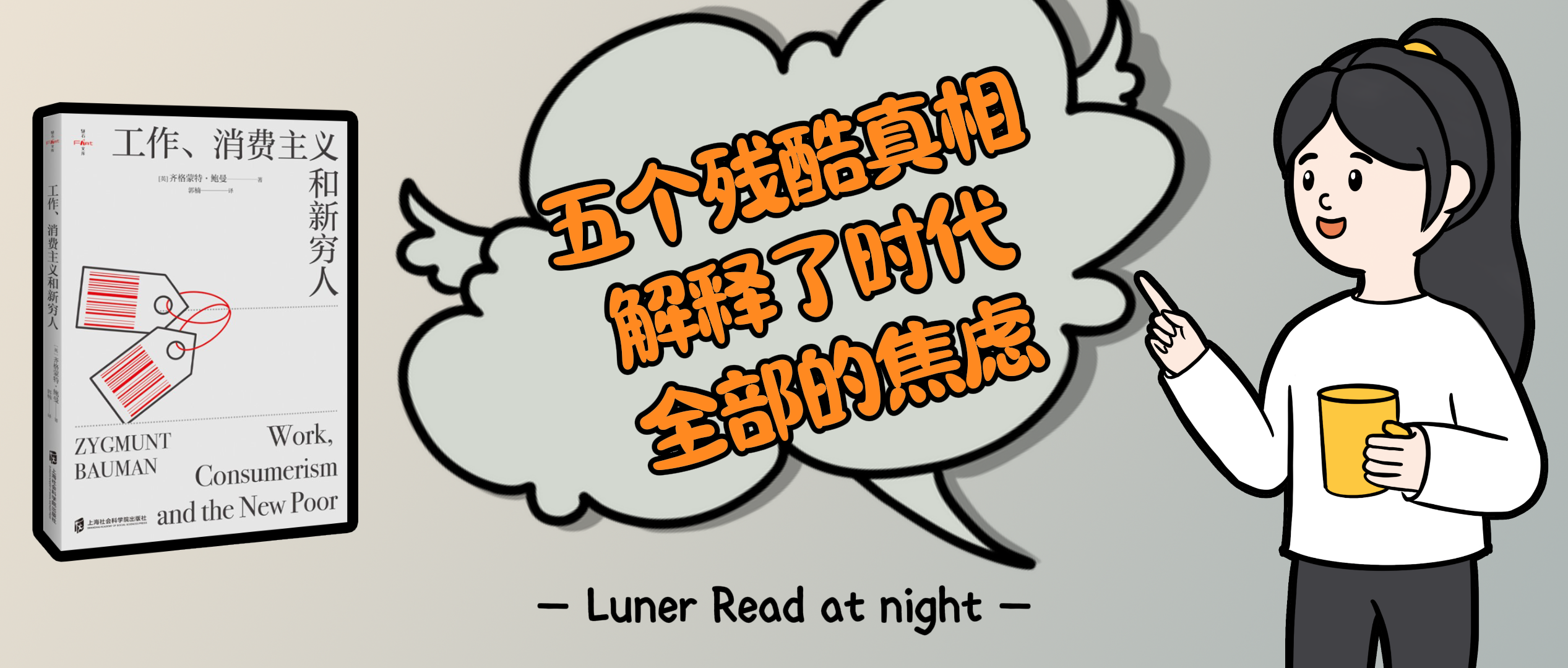
我们为何如此焦虑?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却也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焦虑。我们疯狂工作,“内卷”无处不在,因为我们害怕被淘汰;同时我们又都被巨大的消费浪潮裹挟着,在快乐消费和担忧被掏空之间反复拉扯。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焦虑与不安。
社会学大师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他深刻的著作《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揭示了当代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撕开了现实的迷雾,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我们身处的社会。
1. “工作伦理”并非美德,而是一种规训工具我们从小被教导“努力工作是一种美德”,并将这种“工作伦理”视为天经地义的信条。然而,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念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在工业革命初期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规训工具。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悖论:这场所谓的“道德运动”,其目的竟是为了重新植入一种被工业体系本身所摧毁的工作态度。
在工业化之前,工匠与自己的事业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亲密的关系。工作本身就是意义的来源。然而,工厂体系的诞生彻底瓦解了这种关系,使劳动变得疏离而无意义。
因此,“工作伦理”的核心目的并非提升个人道德,而是为了训练和约束那些习惯了自由散漫生活的前工业时代工匠和农民,强迫他们放弃传统,适应工厂严格、单调、由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它是一场旨在恢复那份已逝去的工作热情的道德运动,但这一次,是在工厂主掌控的纪律之下。
这一观点颠覆了我们对“努力”的传统认知。它揭示了我们内化为个人追求的“工作伦理”,其背后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控制与服从的权力斗争,它优先考虑的是生产效率和秩序,而非个体的幸福与自由。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2. 你不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鲍曼的第二个核心洞见是: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一个“生产者社会”转变为一个“消费者社会”。这一转变的底层逻辑,是从规训转向了诱惑。
在以工厂为核心的生产者社会,社会整合的主要方式是规训。其理想模型是“圆形监狱”(Panopticon),通过严格的纪律和监控,将人塑造成顺从、守纪的生产者。人的主要身份和价值由其工作(生产能力)决定。
在以市场为核心的消费者社会,社会整合的主要方式是诱惑。它不再依靠强制,而是通过创造无尽的欲望和提供“即时满足”来运作。社会要求其成员成为永不满足的消费者,不断地选择、购买、体验和抛弃。
这一转变深刻地重塑了现代人的心理。理想的消费者必须是冲动的、没有耐心的、容易兴奋也容易厌倦的。我们的身份认同、生活目标甚至人际关系,都开始围绕着消费来构建。工作本身也开始被“美学”标准评判——它是否“有趣”、“有意义”、能否带来“满足感”,而不再仅仅是谋生手段。我们不再由生产来定义,而是由消费来定义。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3. “穷人”的新定义:一个有缺陷的消费者既然社会的主要角色变成了消费者,那么“贫穷”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鲍曼指出,今天的穷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业者”,而是一个“有缺陷的消费者”(a flawed consumer)。
过去,贫穷主要意味着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而今天,贫穷意味着无力参与消费市场这场永不停歇的游戏。然而,这种新贫困带来的痛苦,远不止物质匮乏,其核心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折磨——无聊。
消费者社会的终极承诺就是逃离无聊,它通过源源不断的新奇商品和体验来提供刺激。因此,无力消费的人不仅被剥夺了物质享受,更被判处了一种存在主义的极刑:被困在整个社会都在拼命逃离的“无聊”状态中。
这种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的痛苦,表现为一种慢性的烦躁、羞愧和自尊受损。在一个崇拜兴奋和新奇的文化中,被迫忍受单调和无所事事,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性羞辱,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所抛弃。
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4. 从“失业后备军”到“过剩人口”这是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现实。鲍曼指出,在生产者社会,即便失业者也对经济体系有用。他们是“劳动力后备军”,一旦经济复苏,随时可以重返工厂。因此,福利国家的部分功能就是为了维持这支后备军的良好状态。
然而,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经济增长越来越不再依赖于大规模的劳动力。工作岗位被自动化取代或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因此,大量的失业者不再是暂歇的“后备军”,而被视为“过剩的”(redundant)或“多余的”人口。
这个概念的转变是极其残酷的。“失业”暗示着一种暂时的、可以被解决的状态;而“过剩”则暗示着一种永久的、无用的、被社会体系彻底抛弃的状态。他们不再是系统运转的必要组成部分,反而成了系统的负担。
“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的……就所有现实意义而言,如果他们不存在,经济会更好。
5. 从“社会福利”到“社会安全”:当贫穷成为一种罪鲍曼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因果关系:正因为穷人失去了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经济功能,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问题(如贫困)正在被系统性地重新定义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过去,致力于公民福祉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将穷人视为需要集体帮助的弱势群体。而现在,随着穷人被视为经济上的“过剩人口”,他们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需要被监视和控制的“危险阶层”。
这种转变催生了从“社会国家”向“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的转型。其讽刺之处在于,一个社会越是通过“灵活”的资本主义变得富裕,就越倾向于削减福利开支,同时将巨额资金投入到警察、监控和不断扩张的“监狱产业”中。
其最终结果是,贫穷本身被污名化,甚至被视为一种潜在的犯罪。那些无法在消费游戏中获胜的人,不仅被视为失败者,更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对他们的管理,也从社会政策的范畴,转移到了刑罚的范畴。
贫困从社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刑法学和典狱学问题。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未来?鲍曼的这五个洞见,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刻变革,以及我们既有观念的严重滞后。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一个由消费主导、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里,工业时代的工作伦理和对贫困的理解不仅已经失效,甚至被巧妙地转变为一种指责受害者的工具,将系统性的问题归咎于个人的“失败”。
当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已是挣脱的第一步。当我们开始质疑游戏的规则,并尝试按照自己的节奏行走时,我们便已在开辟新的路径。最终的解脱,或许不在于抵达一个没有焦虑的乌托邦,而在于我们终于能直面无边的焦虑,并依然选择清醒、共情且勇敢地活着,在不确定中,为彼此点亮意义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