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音乐迷。所以,这个英那个郎亦或其他什么歌手我一概无感。因此,这里这个听后感应该不存在喜欢哪一方而抨击哪一方了,纯粹是直觉抒发而已。
曾经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歌或什么诗词,我答曰那要看我当时是什么心情 。如果某个人特别喜欢哪个类型的歌或者诗词,那一定是当事人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处在那种心情之中了。

图片源自网络
实际上,换位思考,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某个创作者接连创作某种类型的作品,那么ta一定是处在某种相同心境的亢奋之中而不能自拔、自洽。ta得发泄出来才能平复心情。依此心理学原理,刀郎创作《罗刹海市》、《颠倒歌》应该也属于此类吧。
但真的从头到尾听听,尤其是听听《罗刹海市》,无论怎么说都有点像是泼妇骂街了。只是这家伙不知怎么地,就突兀地在末尾宏观地高度了一下——也许是想附庸风雅吧。所以我说这更像是“泼妇穿着盛装骂街”了。但无论表象上多么想装扮地深刻一些,这也只是在装腔作势,根本掩饰不了其泼妇骂街的本质属性。
事实上,作者既不是屈原那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人,也非鲁迅般“呐喊”的斗士,更是把几十年来数量庞大的普通听众都鄙为“马户”——不知道自己一直在听着一头“驴”唱歌了。如此,岂不是在暗示“公道不在人间”而在这个发泄郁闷的作者那里吗?!要知道,刀郎所言的“驴”可不是只为误认其为马的马户唱歌的,还有不计其数的马户的同胞们也在听着作者所言的那头“驴”唱歌呢。所以,我们由此可见,这个作者是多么地猖狂和自负、以致于ta终于也变成了ta自己在这首歌里要鞭挞的、用“驴”隐喻的那些个能够决定是非的“门阀”了。从这个角度上看,刀郎自己又何尝不是一只“驴”呢?

图片源自网络
其实,从历史唯物主义而非虚无主义的角度上看,“权威”或“门阀”之所以成为权威或门阀,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其自身早期的奋斗脱不了关系——权威或门阀的形成也有其自身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过程的。而作者之所以是个另类,那也只是千万分之一的概率。人们不可能为了这种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就修改常规性的质量评判标准。否则,危险真是太大了,十有八九是要出事故的。
基于这样的认知惯性,谩骂除了喻示着谩骂者的酸葡萄心理和像阿Q一样的精神胜利法以及由此在喜欢发泄的人群当中所引发的一些涟漪和鼓噪之外,其实根本就改变不了任何导致“权威”形成的常规性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在管理学当中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提不出问题解决方案的议论跟发牢骚没有二样。”而牢骚终归是个负面的情绪,它躲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现在,牢骚以街头小曲的形式成为了心有郁结之人的宣泄小调。而街头小曲就是街头小曲,街头小曲怎么可能成为誓师大会或其他类似场合激励人们重新出发的号角呢?哪怕是朋友小聚这种场合,在没有共同嘲讽对象的情况下,谁又喜欢用谩骂来庆祝欢聚一堂的缘分呢?这与其乐融融的氛围不搭啊!(想想央视春晚结束曲的那个演唱场景吧)
当然,社会的宝塔结构决定了这种街头小曲受众颇巨——毕竟喜欢发牢骚的人群数量要远远地多于喜欢埋头苦干的人之数量啊!更何况魔鬼比天使离灵魂更近呢!再加上商业运作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带节奏者)看到了新冠三年之后人们被限足的很多情绪有发泄的需要而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所以,现在出现聚众围观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种街头小曲跟当年昙花一现的“跳舞毯”一样,不会因为其易于发泄和容易用来表达不满而成为经典永流传的。因为,人们无法靠牢骚过日子——毕竟想快乐地活着那就总是要振奋点精神的。而这一点,是刀郎的《罗刹海市》所无法满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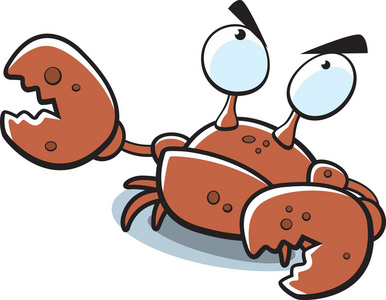
图片源自网络
总之,街头小曲的命运是由其内容决定的:如果是愤懑者聊以自慰的泻药,那就一定与喜怒哀乐的抒情离了十万八千里了,更是与情怀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的就是,我一直有个观察或观点:心中充满爱的人,再怎么搜肠刮肚,也找不出多少刻薄的语言;心中无爱或爱少的人,当然就为刻薄的语言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如果这种人处心积虑地要为如何表达刻薄更解气而做长期的研究那就走火入魔了。不管怎么说,一个人是否包容、是否真诚地为别人的成功鼓掌,绝对体现了一个人灵魂与品德的阶位高低。耿耿于怀者往往就输在了这个方面。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