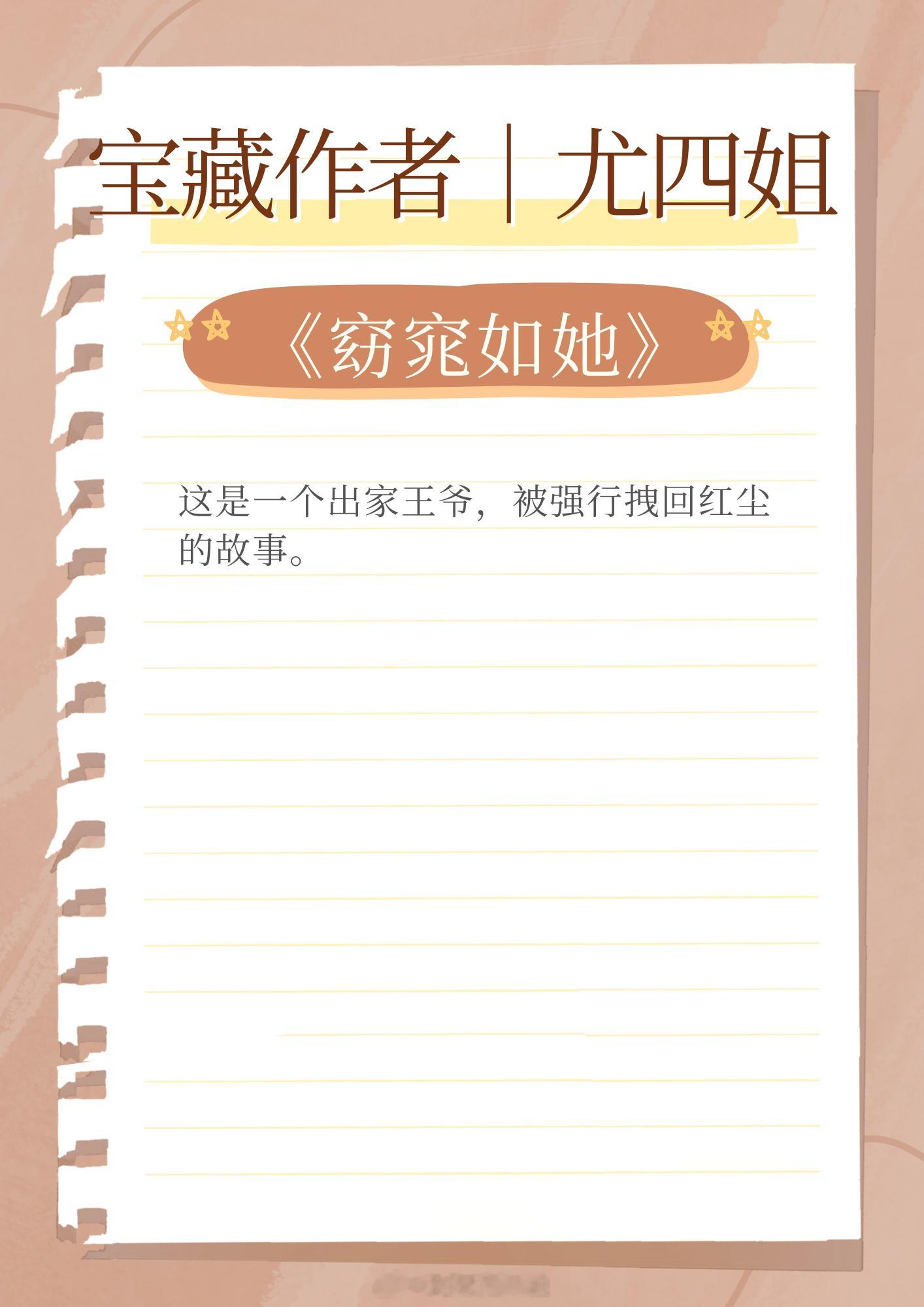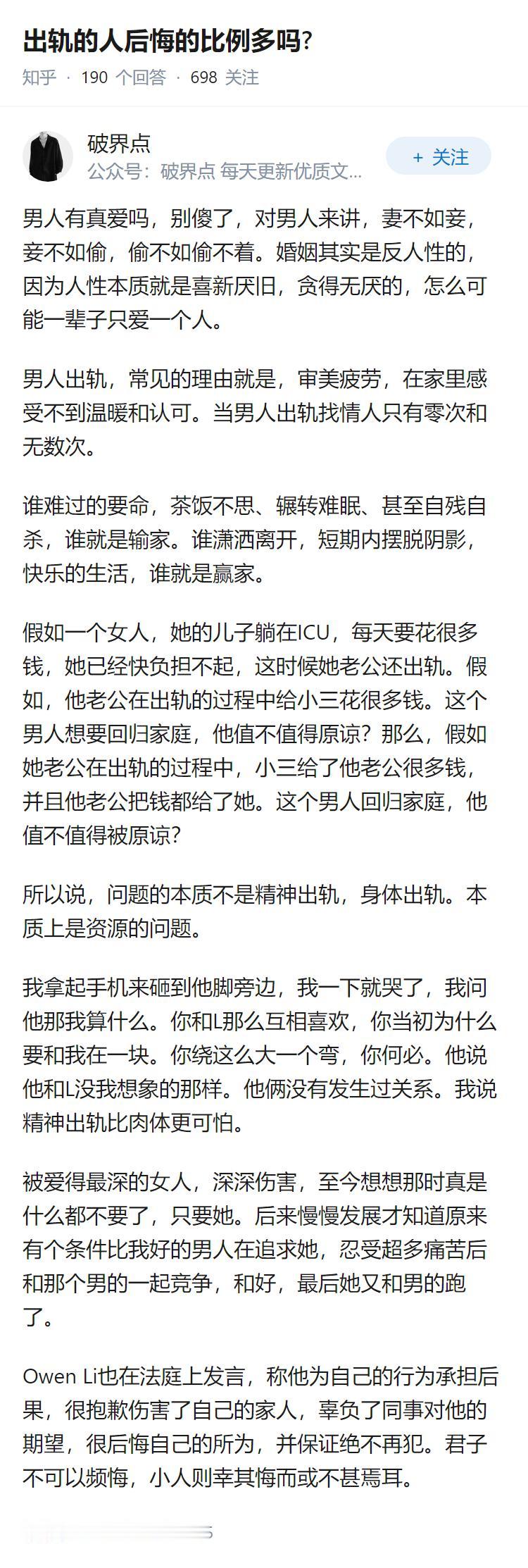夫君哄我拿出十里红妆,给乡里捐了一座书院。
转头,他却牵着表妹的手站在匾额下,得了万民称颂的功德。
乡亲们喊她“活菩萨”,他顺势将这位贤内助迎进门,贬我为妾。
看着两人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二话不说,扔下和离书,打包走人。
没了眼中钉,表妹喜滋滋地要去库房清点家产。
谁知账本一开,掉出来的却是一叠叠按了手印的契书。
她颤抖着念出声:“承诺为乡里再修一座宗祠,三座石桥……”
此时她才明白,我让出的哪里是正妻之位。
我让给她的,是徐瑾帆为了博名声,许下的那倾家荡产也填不完的无底洞。
1
虽然是匿名捐赠,但我心系青云书院,还是悄悄去看了。
夫君徐瑾帆曾言之凿凿:“晓晓,你商贾出身,满身铜臭,站上去只会污了书院的清誉。这钱你出,名声我帮你积,咱们夫妻一体,不用分得太清。”
我信了。
只因当年他落魄时,曾握着我的手在红烛下起誓:“晓晓,待我青云直上,定不负你当年的糟糠之恩,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那时的他眼中满是赤诚,我不疑有他,便傻傻赔上了整颗真心。
为了他的仕途,我倾尽十里红妆,变卖铺面,换来了这座宏伟学府。
可当红绸落下的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
只见那鎏金的功德碑上,赫然刻着:【徐瑾帆携贤妻林月儿,造福桑梓】。
没有我的名字。
取而代之的,是他那位寄住在府上的表妹,林月儿。
高台之上,徐瑾帆正紧紧牵着林月儿的手,接受着万民跪拜。
林月儿一身素衣,弱柳扶风,眼角含泪。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徐大人清正廉洁!”
“徐夫人真是活菩萨转世啊,为了咱们孩子的学业,竟然变卖嫁妆!”
我死死盯着台上那对神仙眷侣,指甲掐进了掌心。
变卖嫁妆?
林月儿那个穷秀才爹,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给她留下,她哪来的嫁妆可卖?
她头上那根素银簪子,还是我上个月赏她的!
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灼热,徐瑾帆终于看见了人群中的我。
他眉头瞬间拧成了死结,没有半分心虚,反倒满眼嫌恶。
典礼一结束,他便在后堂拦住了我。
“你来做什么?”他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责备,“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这种充满文人风骨的场合,是你这种满脑子生意经的妇人该来的?”
我指着外面的功德碑,气得发抖:“徐瑾帆,那一万两白银是我出的!那是我的嫁妆!为什么碑上刻的是林月儿的名字?”
徐瑾帆不耐烦地挥了挥袖子,“月儿是读书人家出身,只有她的名字刻上去,才配得上青云书院的风骨!写你的名字?让全天下的学子都知道这书院充满了铜臭味吗?”
林月儿捏着帕子,轻咳一声:“表嫂,你别怪表哥。我其实也说了,做善事不留名。表哥是心疼我,才非要把名分给我。若是表嫂在意这虚名,我去让人铲了便是……只是怕坏了表哥在士林中的名声。”
徐瑾帆立刻心疼地护住她,转头对我怒目而视:
“你看看月儿,这才是大家闺秀的气度!再看看你,张口银子闭口钱,俗不可耐!”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做了一个极大的决定。
“既然乡亲们都认月儿是徐夫人,为了保全我的官声,也不能再改了。”
“正好,月儿知书达理,更能辅佐我的仕途。今日起,便抬月儿为平妻,对外宣称她是正室。”
“至于你,”他施舍般地看了我一眼,“你既然不懂文墨,就安分做个妾室,管好后院的俗务便是。只要你听话,徐家少不了你一口饭吃。”
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个花着我的钱,还要贬我为妾的男人,心中的爱意瞬间化为灰烬。
我想起曾陪他寒窗苦读,红袖添香的日日夜夜。
原以为是举案齐眉,却原来,只是我一人的独角戏。
2
“姐姐,名分不过是虚妄。”
林月儿依偎在徐瑾帆身侧,手里还捧着卷《女德》,轻飘飘地劝道:“只要能陪在表哥身边,红袖添香,又何必计较名分位置?我就不在乎这些俗礼,只要表哥心里有我,便是没名没分做个通房,我也是甘愿的。”
徐瑾帆听得一脸动容,握着她的手感叹:“晓晓,你学学月儿!这才是淡泊名利的高洁性情!你那满身的铜臭气,若是能有月儿一分风骨,我也不至于让你退位让贤。”
我气极反笑,“不在乎名分?”我冷眼看着这两人,“既然不在乎,那功德碑上为何刻的是你林月儿的大名?既然甘愿做通房,那干脆别当正妻了阿?”
“你——不可理喻!”徐瑾帆怒喝一声,“月儿是为了保全我的颜面!倒是你,斤斤计较,简直是个泼妇!”
“好,很好。”
我不想再听这些令人作呕的废话,从袖中掏出和离书,狠狠拍在桌案上。
“既然你们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分为虚妄,那这徐府的俗气正妻之位,我不要了!”
“但我带来的十里红妆,哪怕是一个铜板,我也要全部带走!”
徐瑾帆扫了一眼和离书,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他轻蔑地看着我,甚至还有闲情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白知晓,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你一介商贾之女,离了我这官身庇护,谁还会多看你一眼?拿和离来威胁我?你以为我会怕?”
林月儿也在一旁掩嘴轻笑:“姐姐,快别闹了。表哥如今是乡里的红人,你这般胡闹,只会让外人看笑话。赶紧给表哥认个错,这事儿就算揭过去了。”
“认错?”我盯着徐瑾帆,“徐瑾帆,我就问你,签,还是不签?”
徐瑾帆被我的眼神激怒了,一把夺过和离书,提笔就在上面挥洒自如。
“签!你以为我不敢!”
他将笔重重一掷,墨汁溅在桌上,正如他此刻的嚣张气焰。
“白知晓,你别后悔!今日你走出这扇大门,日后就是跪在门口求我,我也绝不会再让你踏进徐家半步!”
他指着门外,满脸的不屑:“至于你那些嫁妆,那些俗物摆在府里我都嫌脏了地方!带着你的臭钱滚!我看你离了我,能活出什么人样来!”
拿到签了字的和离书,我小心翼翼地收进怀里。
这一刻,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徐瑾帆,记住你说的话。”
我转身,对着门外早已候着的二十个精壮家丁,厉声喝道:
“来人!动手!”
“除了这宅子的空壳,凡是我白家的东西,连个茶碗都别给他们留下!”
3
“搬!”
随着我一声令下,徐府瞬间灯火通明。
从紫檀木的太师椅,到库房里堆积如山的绫罗绸缎,再到博古架上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甚至连厨房里那口上好的铜锅,都被我的人利落地打包装车。
我带来的,我便要带走。
我赚的,更是一个铜板都不会留。
天还没亮,原本富丽堂皇的徐府,就只剩下了四面徒有其表的空墙。
我坐在马车上,看着手里那厚厚一沓地契和银票,冷冷一笑,吩咐车夫:“走。”
听留守在那边看笑话的老管家回来说,第二天一早,林月儿是被人搀扶着,喜气洋洋地去接管中馈的。
徐瑾帆为了安抚她,特意将掌家的对牌和库房的钥匙,当着全府下人的面交到了她手里。
“月儿,从今往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徐瑾帆一脸深情,“晓晓满身铜臭,只知钻营,这徐府的内务被她搞得乌烟瘴气。如今你来当家,定能让这府邸多几分书香雅气。”
林月儿感动得眼眶微红,接过钥匙时手都在抖,那是激动的。
她以为她接住的是泼天的富贵,是后半生享之不尽的荣华。
她迫不及待地屏退左右,颤抖着打开了那象征着徐府财富的黄花梨木大箱子。
然而,预想中金银满箱的画面并没有出现。
随着箱盖掀开,飘落出来的不是银票,而是一叠叠按着鲜红手印的契书。
林月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她慌乱地抓起那些纸张,越看手抖得越厉害,最后竟带着哭腔念出了声:
“承诺……为城南李家修宗祠一座,预算纹银三千两……”
“承诺……为乡里再架三座石桥,以便百姓通行……”
“承诺……施粥三年,每日耗米五石……”
这一桩桩,一件件,全是徐瑾帆平日里为了博取“大善人”、“清流”的美名,在酒桌上豪言壮语许下的承诺!
以前,这些天文数字般的开销,都是我默默填平的。
林月儿看着箱底那仅剩的几两碎银,整个人如遭雷击,脸色惨白地看向一旁的徐瑾帆。
“表……表哥?这些……都要钱?”
徐瑾帆正负手而立,沉浸在自己两袖清风的得意中,闻言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自然是要钱的。修桥铺路乃是大功德,咱们徐家既然受乡里爱戴,这点付出是应该的。”
他瞥了一眼面无人色的林月儿,眉头微皱,似乎对她的惊讶感到不满:
“以前这些俗务都是晓晓处理的,我只需负责在外应酬。如今你是当家主母,既然坐了这个位置,这些钱自然该你想办法。”
“月儿,你不是最懂我的志向吗?总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让我失望吧?”
林月儿捏着那几张薄薄的契书,看着徐瑾帆那副甩手掌柜的嘴脸,两眼一黑,差点当场晕过去。
她终于明白,我让给她的哪里是正妻之位。
我让给她的,是徐瑾帆为了博名声,许下的那倾家荡产也填不完的无底洞!
可还没等这对神仙眷侣从巨额债务的打击中缓过劲来,债主们就上门了。
4
“徐大人!徐夫人!吉时已到,咱们李氏宗祠的修缮款,您二位看什么时候给拨下来?”
徐府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
我特意挑了这个时辰,倚在不远处的马车旁,手里抓着一把瓜子,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出好戏。
林月儿哪见过这阵仗?
她强撑着那副清高架子,试图用她那一套文人风骨来忽悠这群大老粗。
“各位族老,”她捏着帕子,柔柔弱弱地开口,身子却不住地往徐瑾帆身后躲,“修缮宗祠乃是大事,需得沐浴焚香,静待机缘。谈钱未免太过俗气,不如先让大家回去修身养性,缓上一缓……”
“缓?”领头的族老脸色顿时垮了,一口唾沫差点吐在台阶上,“白夫人在时,那可是说一不二!上午许诺,下午银子就拉到了工地上!怎么你这新夫人一上位,就要赖账?”
“就是啊!不是说活菩萨吗?怎么比白夫人这商户女还抠搜?”
这一声声议论,像巴掌一样扇在徐瑾帆脸上。
他脸色铁青,正欲发作,眼角余光却瞥见了我。
林月儿顺着他的目光看来,顿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她几步冲到我面前,指着我大声喊道:
“是她!是姐姐!这宗祠的事儿,当初是姐姐应下的!如今姐姐虽然和离了,但这承诺不能不认啊!姐姐,你快把钱拿出来,别让表哥为难!”
众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我身上。
徐瑾帆也挺直了腰杆,似乎觉得只要把锅甩给我,他就能保住面子。
我慢条斯理地嗑开一颗瓜子,吐出瓜子皮,才冷笑着开口:
“林月儿,你是不是忘了?和离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徐府的所有债务,承诺,皆由徐瑾帆及现任主母承担。”
“再说了,”我指了指那块功德碑,“那上面刻的是你的名字。怎么,领功劳的时候你是活菩萨,掏钱的时候你就成哑巴了?”
“当初是谁说,只有你的名字才配得上这书院的风骨?既然要风骨,那便拿你的骨头去熬油点灯,别来沾我的边!”
围观的乡亲们哄堂大笑。
“原来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这新夫人看着清高,原来是个赖皮!”
徐瑾帆最是个好面子的,哪里受得了这种羞辱?
他猛地转头,一巴掌甩在林月儿脸上。
“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
他咬牙切齿,压低声音怒吼:“你是当家主母,这钱你必须出!若是让乡亲们看扁了徐家,我休了你!”
林月儿捂着脸,眼泪夺眶而出。
被逼无奈,她只能当众摘下头上那根唯一的银簪,那还是我以前赏她的,又把徐瑾帆书房里仅剩的几方砚台,挂画全拿出来抵债,才勉强打发走了第一波人。
但这只是开始。
为了维持体面,林月儿不得不辞退了府中大半下人。
傍晚时分,徐府的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伴随着呛人的咳嗽声。
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只知吟诗作对的徐夫人,如今被迫挽起袖子,灰头土脸地亲自下厨。
我看着那狼狈的烟火气,心情大好。
“夫人,咱们回娘家吗?”丫鬟小声问。
“回什么娘家?”我指了指徐府隔壁那座刚挂上“白宅”匾额的院子,“我买了隔壁,我们就住这儿看戏。”
这场大戏才刚刚开锣,作为最大的债主和唯一的观众,我不坐在第一排,岂不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