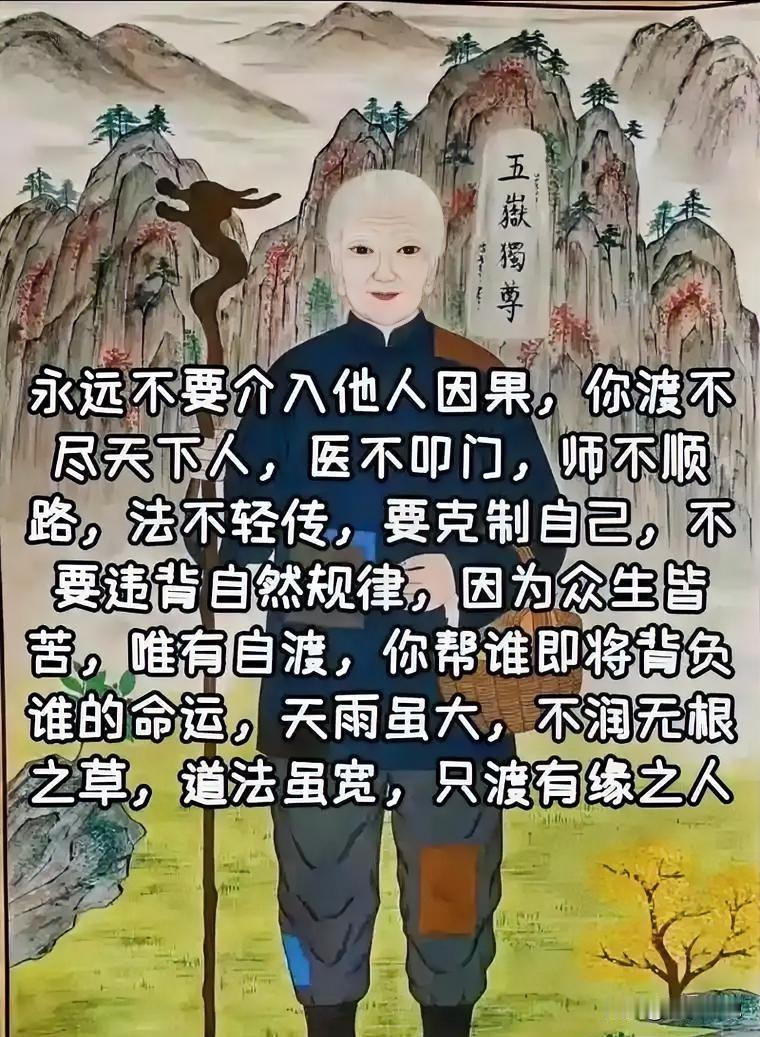父亲养了7年的藏獒,最近行为越来越古怪。
它总在半夜一动不动地蹲在父亲床边,死死盯着熟睡的父亲。
父亲欣慰地说,这是山风年纪大了,在守护他。
直到我国庆回家,亲眼目睹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山风绕着床缓缓踱步,鼻子轻耸,目光盯着父亲脖颈的位置。
它甚至无意识地咧开了嘴,露出了森白的牙齿。
我连夜联系了一位动物行为学专家。
听完我的描述和看完视频后,他的回复让我如坠冰窟。
01
“程教授,情况就是这样,您看我父亲养的这只獒犬,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将整理好的视频和文字描述通过手机发了过去,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屏幕那头是国内知名的动物行为学专家程锐,我费了好大周折才联系上他。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程教授发回了一段语音,我点开播放,他沉稳而严肃的声音在寂静的客房里响起:“周先生,你发来的影像资料我仔细看过了。”
他的语气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
“我必须告诉你一个可能不太容易接受的事实——这只名叫‘山风’的獒犬,它目前表现出的行为,并非你父亲所理解的守护,而是一种典型的‘狩猎前评估’状态。”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几乎停滞,握着手机的手心渗出冰凉的汗。
“獒犬这类原生犬种,骨子里保留着极强的等级意识和野性本能。”程教授的语音继续播放,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打在我心上。
“在它们的认知体系里,族群的领导者必须是强者,当领导者出现衰弱迹象时,某些本能就会被触发。”
我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听着他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分析。
“山风每晚在你父亲床边进行的转圈、凝视、调整角度、乃至无意识的张口动作,都是捕食者在发动攻击前评估猎物状态、计算攻击路线的典型表现。”
“它嗅到了你父亲因疾病而改变的体味,看到了他行动变得迟缓,在它深层的本能逻辑里,这位曾经的‘头领’已经不再适合领导它了。”
“我建议你立刻采取措施,将山风与你父亲进行物理隔离,并尽快为它寻找新的、合适的安置场所。”
程教授的语音结束了,房间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声。
窗外,凌晨三点的夜色浓得化不开,我知道山风刚刚完成它今晚的“巡视”,回到了院子里的窝棚。
而我父亲周怀安,今年六十五岁,正浑然不觉地在隔壁房间安睡,他还以为陪伴了他七年的山风,是他晚年最忠诚的守卫。
我必须做点什么,时间可能不多了。
02
一切的起因要追溯到七年前。
母亲因病去世后,独自住在老宅的父亲肉眼可见地消沉下去,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
那时我刚在省会城市站稳脚跟,工作忙得焦头烂额,除了每月寄钱和打电话,能做的实在有限。
看着父亲迅速灰白的两鬓和越发佝偻的背影,我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
那一年春节回家,我试探着提出:“爸,要不……养条狗吧?有个活物陪着,家里也能添点生气。”
父亲当时眼睛亮了一瞬,随即又黯淡下去:“小狗没意思,大狗我也伺候不动了。”
“那养只獒犬怎么样?”这个念头不知怎么就冒了出来,“听说它们最认主,也护主,咱们这地方偏,有它在我也放心些。”
父亲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通过朋友介绍,我们从城郊一个专门的犬舍接回了山风。
那时它已经快两岁了,是一只铁锈红与黑色相间的大型獒犬,骨架雄伟,眼神锐利。
第一次见面时,它低沉的喉音和充满戒备的姿态让我有些发怵。
但父亲却表现得出奇平静,他慢慢地蹲下身,向山风伸出手掌。
山风嗅了嗅,竟没有排斥,反而用鼻子轻轻碰了碰父亲的手心。
“就叫山风吧。”父亲脸上露出了母亲走后的第一个真切笑容,仿佛有一阵山风吹散了些许暮气。
从那以后,山风就成了父亲生活的全部重心。
他们每天一同出门散步,父亲生病时山风会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它甚至从池塘里救过邻家小孩,也吓跑过试图翻墙的宵小之徒。
父亲在电话里谈起山风,语气总是充满骄傲和依赖,他说:“有山风在,我就不孤单。”
我曾为此感到欣慰,以为找到了弥补自己缺席的方法。
直到一个月前,父亲在电话里用带着笑意的声音说:“山风最近有点怪,总爱半夜溜进我屋里,就蹲在床边看着我,可能年纪大了,更黏人了。”
我当时正被项目进度追着,随口应和了几句,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温和描述的背后,潜藏着怎样令人战栗的真相。
03
真正让我警觉起来,是这次利用年假回家给父亲过生日。
父亲看上去比视频里更清瘦了些,精神倒还不错,山风趴在他脚边,俨然一副岁月静好的画面。
但父亲私下告诉我,他的高血压和血糖问题比之前更明显了,需要持续服药控制。
我暗自留心,决定亲自看看山风半夜到底在做什么。
头一晚,我躲在客厅的阴影里,亲眼目睹了那诡异的一幕。
凌晨两点二十分左右,山风那庞大的身躯如幽灵般无声地穿过客厅,用头顶开父亲虚掩的房门。
它走到床边,以一种极其标准的姿势坐下,前肢并拢,脊背挺直,然后,它的头微微低下,那双在黑暗中幽幽发光的眼睛,就一眨不眨地、死死地盯住了床上熟睡的父亲。
那不是宠物依恋的眼神,也不是警戒护卫的眼神。
那是一种纯粹的、专注的观察,带着一种冷静的评估意味,它的视线焦点,牢牢锁定在父亲脖颈附近。
我的后背瞬间爬满冷汗。
接下来的几晚,我借助手机录像,捕捉到了更多细节。
山风会在“观察”前,绕着床缓慢走一圈,鼻子轻轻耸动,仿佛在分析空气中的气味。
它会极其细微地调整自己的坐姿和角度,直到找到一个“最佳位置”。
有一次,父亲在睡梦中无意识地咳嗽了几声,山风的肌肉瞬间绷紧,身体前倾,喉咙里发出几乎听不见的低鸣,嘴巴甚至无意识地张开了一条缝,露出了森白的犬齿。
那个瞬间,我脑海中闪过的是动物世界里,猛兽扑向猎物前的定格画面。
白天,山风却完全恢复了常态,温顺,听话,会蹭父亲的手,会摇尾巴。
这种巨大的昼夜反差,让我的不安达到了顶点。
我询问了村里几位有经验的老人,其中一位姓赵的大爷叹了口气,讲了一件往事。
他说很多年前,村里也有户人家养的大狗,在主人重病卧床后,行为变得古怪,最后竟然……他摇摇头没再说下去,只提醒我多注意。
这些碎片化的异常,最终促使我找到了程锐教授。
而他的专业判断,将我心中模糊的恐惧,勾勒成了清晰而狰狞的形状。
本能,正在压倒七年朝夕相处的情感。
04
向父亲坦白的过程,比想象中更加艰难痛苦。
当我将程教授的分析,结合自己拍摄的视频,一点点摊开在父亲面前时,他先是愣住,随即脸上血色尽褪,但很快又被强烈的抗拒和愤怒取代。
“不可能!”父亲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山风跟了我七年!它救过我!它怎么会……你想多了!你就是嫌它麻烦!”
“爸,我不是嫌它麻烦,我是担心您!”我试图抓住他的胳膊,却被他用力甩开。
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父亲痛斥我对山风的“污蔑”,指责我常年不在身边却要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
我看着父亲通红的眼眶和颤抖的手指,心如刀割,但我不能退让。
最终,我们各退半步,决定先做一个测试——当晚不让山风进入卧室。
那天夜里,山风在紧闭的房门外,发出了持续而悲戚的呜咽,用爪子轻轻挠着门板。
父亲在门内坐立不安,好几次都想冲过去开门,都被我硬生生拦下。
后半夜,呜咽声停止了。
我透过窗帘缝隙看到,山风没有再回窝棚,而是直接趴在了父亲卧室的窗台下,仰着头,静静望着那扇窗,眼神在月光下晦暗不明。
第二天,父亲的精神明显萎靡,他看着院子里安静趴着的山风,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它一定很难过,很困惑。”父亲喃喃道。
“爸,如果它真的只是困惑和难过,那为什么眼神会变成那样?”我指着窗外,“您看看它现在的样子。”
父亲望过去,沉默了。
山风似乎察觉到我们的注视,也转过头来。
那一瞬间的目光交汇,父亲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那不是他熟悉的、充满信赖与温情的目光,那目光深处,有一种让他感到陌生的、冰冷的审视。
父亲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在那目光中崩塌了。
他颓然坐倒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微微耸动。
良久,他沙哑着声音说:“联系你说的那个地方吧……找个……找个能好好待它的人家。”
我立刻开始联系程教授推荐的、一家有资质接收和驯导大型犬的机构,对方答应第二天中午派车来接。
我们谁也没有说破,但都清楚,所谓的“送走”,更像是一场不得已的、危险的隔离。
05
机构来接人的电话是上午打来的,说车辆已经出发,大约午后能到。
挂了电话,我和父亲对坐在堂屋里,相顾无言,气氛沉重得像能拧出水来。
院子里的山风似乎格外安静,它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院里巡逻或玩耍,只是趴在它最喜欢的那个角落,目光偶尔扫过屋内,大部分时间望着不知名的远方。
“我去给它准备最后一顿好的。”父亲站起身,脚步有些蹒跚地走向厨房。
他精心煮了一大块牛肉,混合着山风平时爱吃的粮,放在它专属的那个厚重食盆里。
“山风,来吃饭。”父亲的声音很轻,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
山风走过来,低头嗅了嗅食物,又抬头看了看父亲,然后才慢慢开始吃。
它吃得很慢,不像往常那样狼吞虎咽,偶尔会停下来,用头顶蹭蹭父亲垂在一旁的手。
父亲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它吃,用手一遍遍抚摸着它颈后厚实粗糙的毛发,仿佛要将这触感刻进记忆里。
“好了,吃完了,去歇着吧。”父亲拍了拍它的背。
山风听话地走回角落趴下,下巴搭在前爪上,眼睛半阖。
时间在压抑的寂静中缓慢流淌。
突然,父亲的身子晃了一下,他抬手扶住了旁边的桌子,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爸!”我急忙冲过去扶住他。
“没事……有点头晕,老毛病了……”父亲的声音虚弱,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
我知道,这是情绪剧烈波动加上原本就有的血压问题引发的短暂不适。
但就在这一刻,趴在院子角落的山风,猛地站了起来。
它的动作不复平日的慵懒,充满了警觉与力量。
它那双半阖的眼睛完全睁开,里面所有的温顺、迷茫或悲伤都在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种极其专注、近乎冷酷的锐利。
它的鼻子在空气中快速而细微地耸动,视线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了屋内倚靠着桌子、显露出明显虚弱姿态的父亲。
它开始动了。
不是冲过来,而是以一种缓慢、沉稳、充满压迫感的步伐,向着堂屋的门口走来。
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跳上。
它喉咙里不再有任何呜咽,只有一种低沉到几乎感觉不到的、持续的震动。
我脑海中轰然炸响程教授最后的警告:“……最危险的触发点,往往是主人突然显露出的极度虚弱状态,那会彻底压垮情感联结的最后防线,让捕猎本能占据绝对上风……”
“爸!别动!”我本能地将父亲护在身后,眼睛死死盯住越走越近的山风。
它停在敞开的堂屋门口,巨大的身躯几乎堵住了光。
它微微低下头,琥珀色的瞳孔在室内稍暗的光线下收缩成危险的竖线,它的目光越过我,直直刺向我身后呼吸不稳的父亲,聚焦点正是那脆弱的脖颈。
它后腿的肌肉缓缓绷紧,那是一个准备发力扑击的预备动作。
我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门外可能存在的邻居,也朝着那个正在逼近的、我曾视为家人的黑影,嘶声喊道:“快!来人啊!把山风弄走!它这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