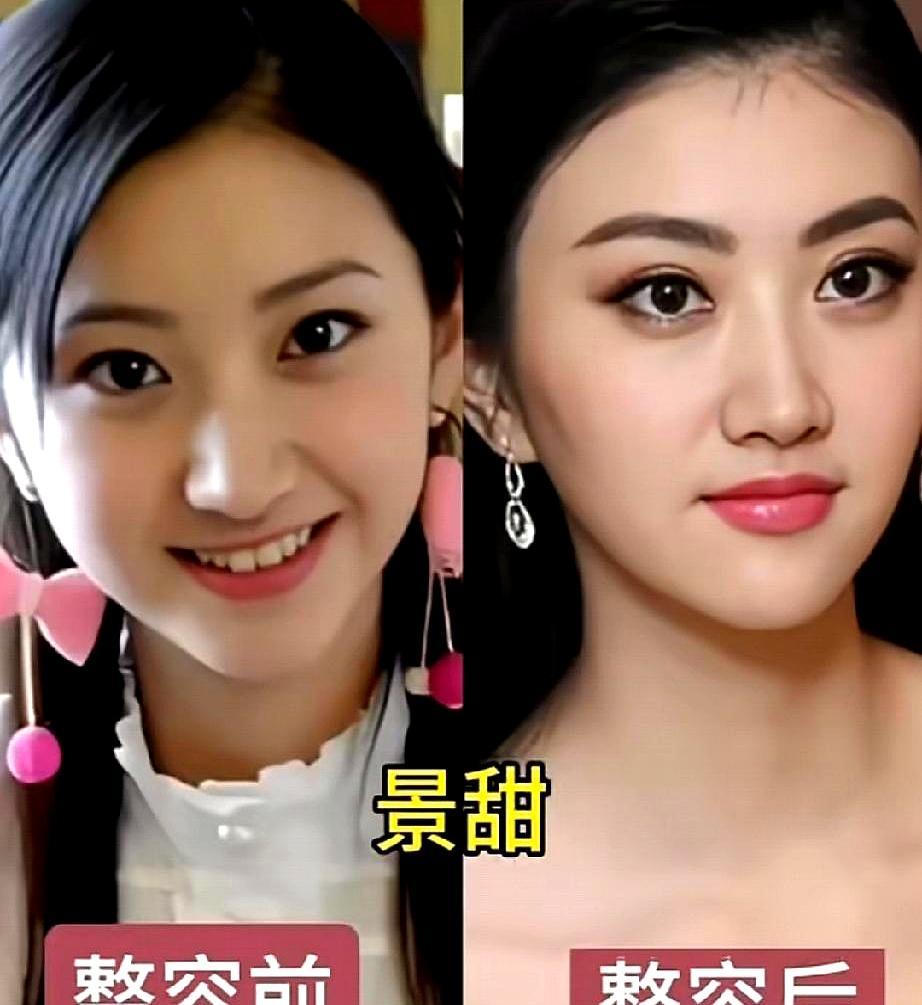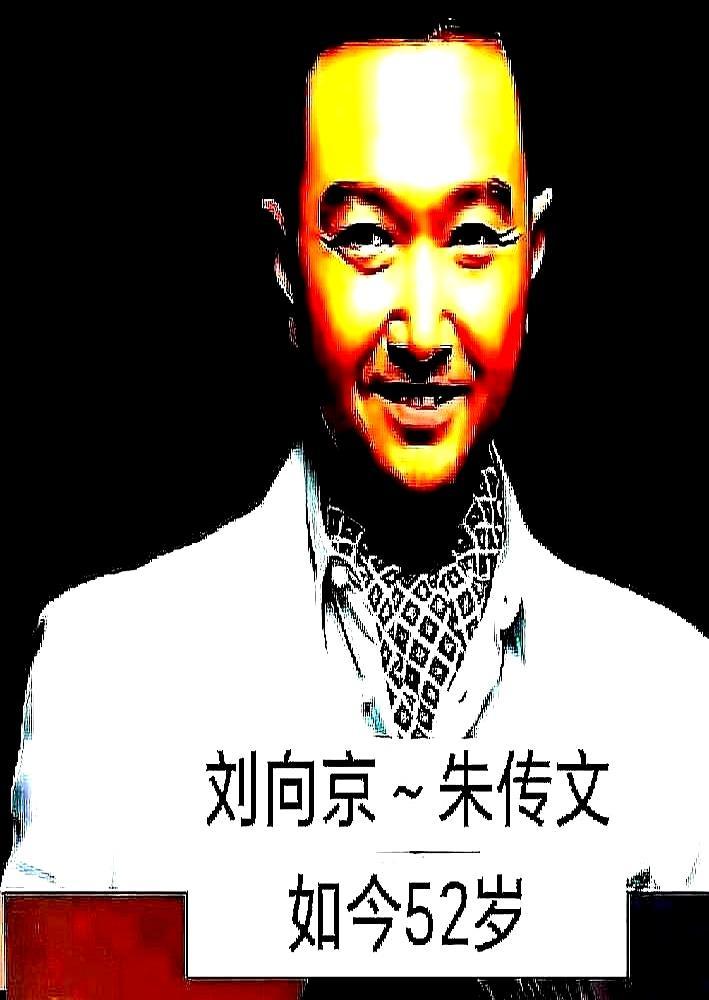这便是袁世凯的真实模样,这可不是演戏,也不是影视剧里的演员 一九一四年冬天,天坛圜丘重新铺上黄土,黄土大道一直铺到坛前。 钢甲小汽车从新华门开来,乐队在冷风里吹号。走下来的是民国大总统,不是皇帝,却要“祀天”。 按旧礼,这场面本该属于天子。 坛上这人,后来被写进课本叫作“窃国大盗”,可早些年,他只是北京科举场里那个读书读到吐血也考不上举人的落第生。 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在京城读了四年书,指望靠八股翻身。 光绪五年乡试,考场上没混出名堂,只留下“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这一联句。 他自己说,那是“一生最大的遗憾”。等到家书和奏折都汇在一起,另一面才显出来:字不算工整,条理却很清,算钱、调兵、安排亲友,都写得干净利落。 骆宝善花了多年,把能找到的信札文牍全编进三十卷、二千五百万字的《袁世凯全集》,二〇一一年夏天出版,这一摞书,多少打碎了“粗人军阀”的刻板印象。 家里人记得的,是军人派头。三女袁静雪说,父亲一身黑呢制服,站着坐着腰背都挺得笔直,平日少笑,急了嘴上就是“混蛋”,再急“混蛋加三级”。对部下说话客气,谁也不敢不听,那种客气里带着压力。有人说他往椅子上一坐,眼光一闪,像只老虎。 中南海那几年,他吃饭要奏军乐。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总管太监张谦和一听那边军乐响起,嘴就气得扁起来,认定这个大总统“比皇上还神气”。袁世凯自己倒觉得顺手,在他眼里,统兵比做文章轻松。 张之洞问他练兵诀窍,他只说一句“绝对服从命令”,一手官帽银子,一手刀子,听话的有官有钱,不听话的挨刀,用的就是这一套。 清廷把他开回彰德洹上的那三年,纸面上写的是“回籍闲居”,院子里却没消停。各省消息往这里汇,留日学生回国也喜欢绕道来拜访,屋里常常坐满人。 他按人品才干给路子、给盘缠。 许指严记笔记时感叹,那几年几乎每月都有革命党举事,“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话说得重,也说明他不肯把自己钉死在一块牌子上,更像是在清廷和新党之间来回周旋。 在官场早年,他和康有为称兄道弟,是强学会里第一个捐银的人。 甲午战败后,他心里偏向变法,对西方法制和制度了解得不比康有为少。呈给光绪帝的那篇新政万言书,从用人、理财到经济、军事、外交,都主张“彻底更张”。 风向一转,戊戌那年康梁、谭嗣同希望他出手杀荣禄,他却靠荣禄自保,这一步救了自己,也把他推到“卖友求荣”的那一头。 往上看,他离不开李鸿章、荣禄、奕劻这些权力中枢。 李鸿藻器重他,荣禄在小站弹劾案里出面保全,他非但没倒,还得了嘉奖。 庚子义和团起,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他从小站赶到济南当山东巡抚,用铁腕手段“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替清廷立下大功,政治威信就是在那里立起来的。李鸿章老幕僚张佩纶渐渐看他不顺眼,在密信里骂他是“有才的小人”。 胡思敬写《国闻备乘》,干脆说光绪末年小人求富贵的捷径有两条,一条在商部载振手里,一条在北洋袁世凯手里。 用人这件事,更能看出他的算计。 一边,他起用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这些留美幼童,又重用严修、胡景桂一类在士林里有名望的人;另一边,段芝贵这样的巡捕出身,也能被捞起来。 段芝贵抓回袁家的逃仆,被夸一句“有才”,捐了个道员,又花重金买下歌妓杨翠喜献给庆王府载振,一夜之间成了封疆大吏。 袁世凯本人,从朝鲜回来后就和李莲英一类权宦往来,即便当了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年年还得进京“走动”。 在革命党人那里,他照样用的是这一套。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在北京,都挨过他的隆重招待。孙中山来时,他把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腾出来,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 孙中山后来回忆,说袁世凯会办事,气度不小,只是惯于玩权术;刚见面时像个至诚的人,细聊几句,就感觉到话里藏着锋芒,眼光四射,让人看不透。 等到几年后看他做的事,又和当初说的对不上,只能摇头,把他叫作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 日俄战争又给清廷上了一课。 日本一八八九年就有议会,俄国战前没有,日本赢了,俄国输了,这样的对照很扎心。伊藤博文劝中国钦差,说皇帝要是肯“钦赐宪法”,照样能坐在万民头上,只是最高权力不能落在人民手里。 慈禧顺势发出预备立宪诏书,一九〇八年定下九年训政期,一九一一年改组内阁,十三个阁员里满族九个、汉族四个,样子学上了,实权却还在老地方。 辛亥以后,华中、华南、东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新军指挥做督军,和省议会一起搭省政府。 有学者认为,这多半是地方绅士借独立摆脱北京控制,好守住本地政治和经济,普通人只是看热闹。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袁世凯被捧上台,一头要送清王朝入土,一头被寄望给民国撑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