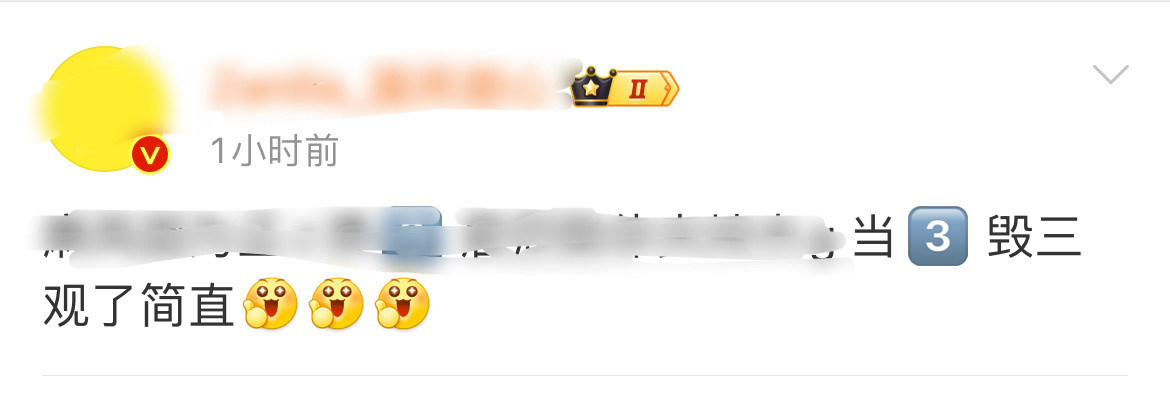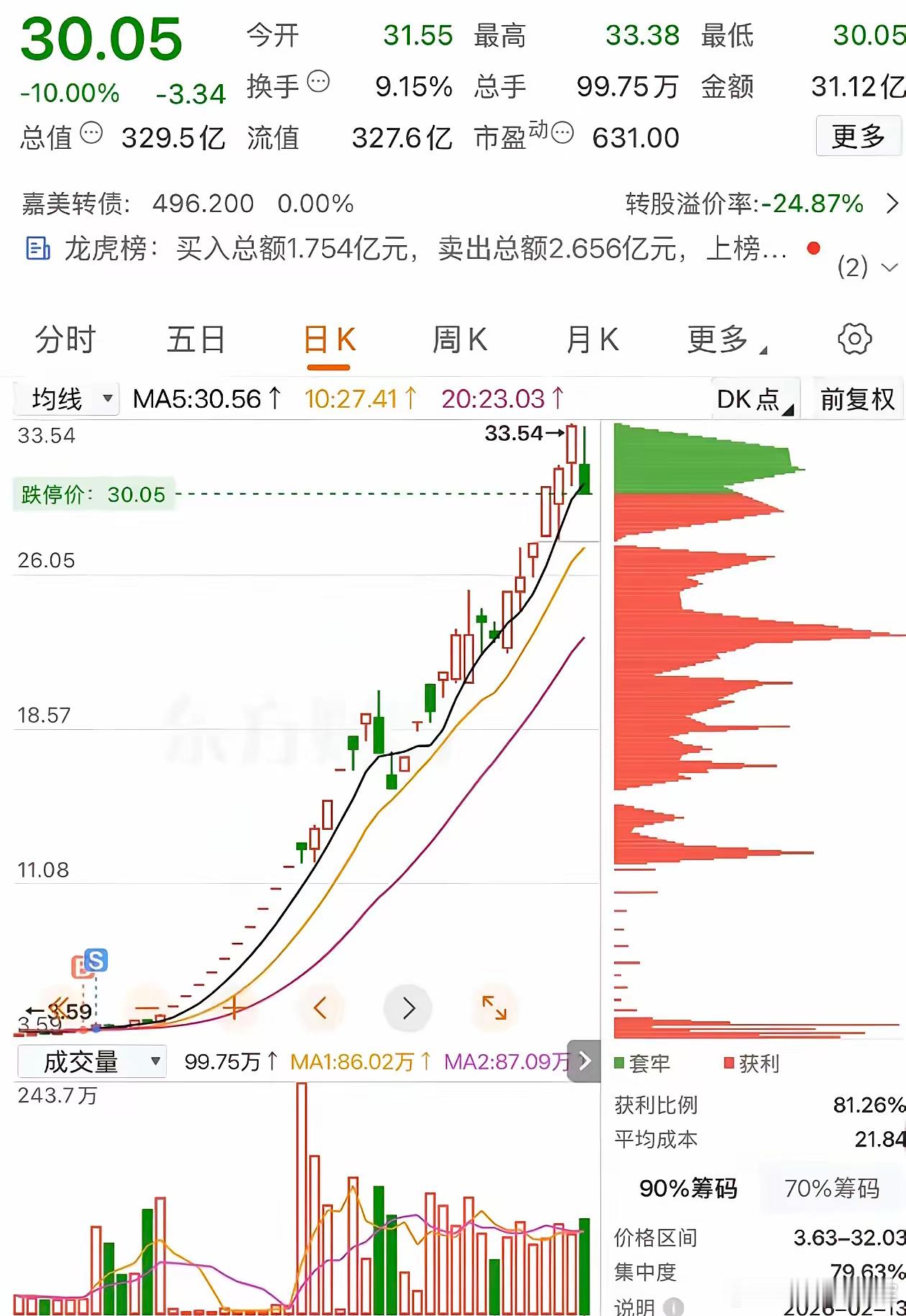沪东纱厂女工阿珍,在更衣室冰凉的水泥地上生下了孩子。没有医生,没有剪刀,她用牙齿咬断脐带,把婴儿往工服里一裹,对吓呆的工友说:“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把工牌打上,别让车间记我旷工。” 那年阿珍二十二岁,进厂四年,是细纱车间挡车工。丈夫是同一厂的机修工,两人住在厂区外的棚户里,结婚三年没敢要孩子。不是不想,是厂里有规矩:怀孕就得调离一线岗位,工资减半;生了孩子再想回来,难。 阿珍瞒了七个月。她用宽大的工装遮住肚子,把腰勒得紧紧的,每天在机器轰鸣中来回走四十里路。早班从凌晨四点开始,她三点就得起来,用冷水洗脸消肿,然后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 她算过账:少上一个班,就少两块钱。两块钱够买一斤半猪肉,够给乡下老娘寄半个月的口粮,够攒半年给家里添台收音机。她不能停。 那天是早班,机器转得像催命。阿珍正接着断头,突然觉得肚子往下坠。她扶住车架,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身边的阿英看出不对,小声问:“怎么了?” “没事,岔气了。”阿珍咬着牙把线接上,手指抖得厉害。 十分钟后,羊水破了,顺着裤腿流到地上,和地上的机油混在一起。阿珍慢慢蹲下去,用围裙挡住,对阿英说:“扶我去更衣室。” 更衣室在车间尽头,三十米的路,她走了很久。路上遇到组长,组长皱眉:“阿珍,不舒服就歇歇,别耽误生产。”阿珍点头,把嘴闭得紧紧的。 更衣室的水泥地冰凉,墙角堆着废纱头和饭盒。阿珍靠着墙坐下,脸色白得像纸。阿英想跑去叫人,被她一把拽住:“别去!叫了人,我就回不来了。” 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换班的铃声。阿珍用牙咬断脐带,用脱下的工服把皱巴巴的小东西裹起来,血糊了满手。她低头看了孩子一眼,是个女儿,闭着眼,小小的一团,居然没哭。 “帮我看着,”她把孩子递给阿英,声音虚弱却清楚,“我把工牌拿去打上。” 阿英哆嗦着接过孩子,看着她摇摇晃晃站起来,用车间洗手池的冷水把手上的血冲掉,然后从包里翻出一条干净的围裙系上,遮住洇湿的裤子。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车间主任后来从报表上看到:那天乙班出勤率百分之百,细纱千锭小时断头率低于指标,阿珍个人产量排班组第三。 很多年后,当年的阿珍成了珍婆,带着女儿回厂旧址参观。纺织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的工牌、饭票、光荣榜,女儿在玻璃柜前站了很久,指着其中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问:“妈,这个是你吗?” 照片上,一群年轻女工站在机器前,戴着白帽,穿着统一的工装,笑得一模一样。 珍婆没说话。她想起的,是水泥地上的血,是机器的轰鸣,是那个用牙齿咬断脐带的中午,以及下午接着在车间走完的那四十里路。她想起当年的工友阿英后来对她说的话:“那天我抱着孩子,手抖了半天。你倒好,跟没事人似的,接了八个钟头的线。” 珍婆笑了笑,没解释。她没法解释,在1956年的沪东纱厂,一个女工的工牌比她的身体重要,产量比疼痛重要,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她更没法解释,那天下午,当她站在机器前接着断头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刚出生的女儿,而是今天这个班如果上满,就能凑够给孩子买一辆婴儿车的钱。 那辆婴儿车,她后来真的买到了,推着女儿走过无数个清晨和黄昏。 博物馆里,女儿还在看那张照片。珍婆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走吧,都是过去的事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玻璃柜里那些沉默的旧物上。工牌上的编号还在,像是等着什么人,再打一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