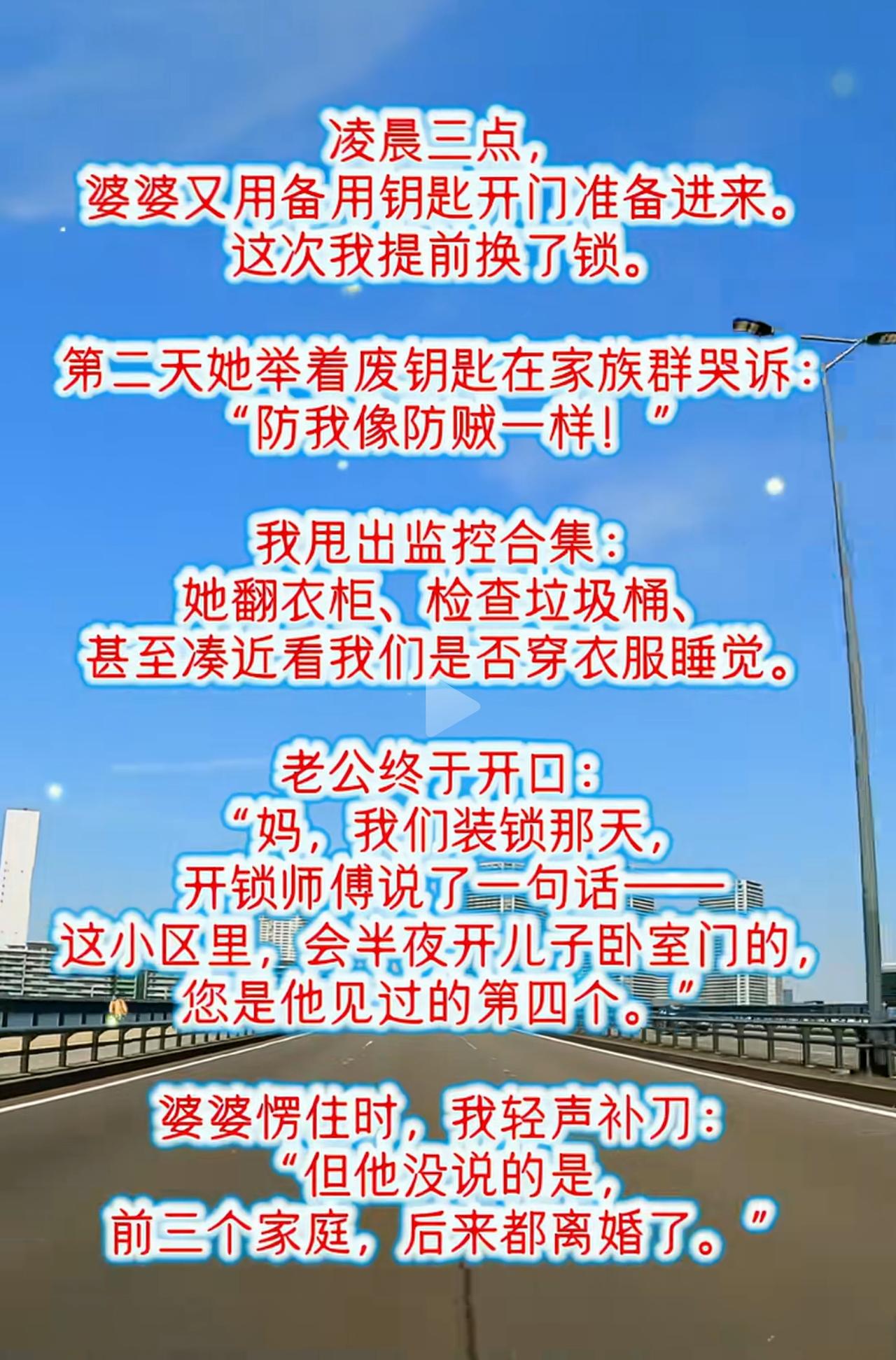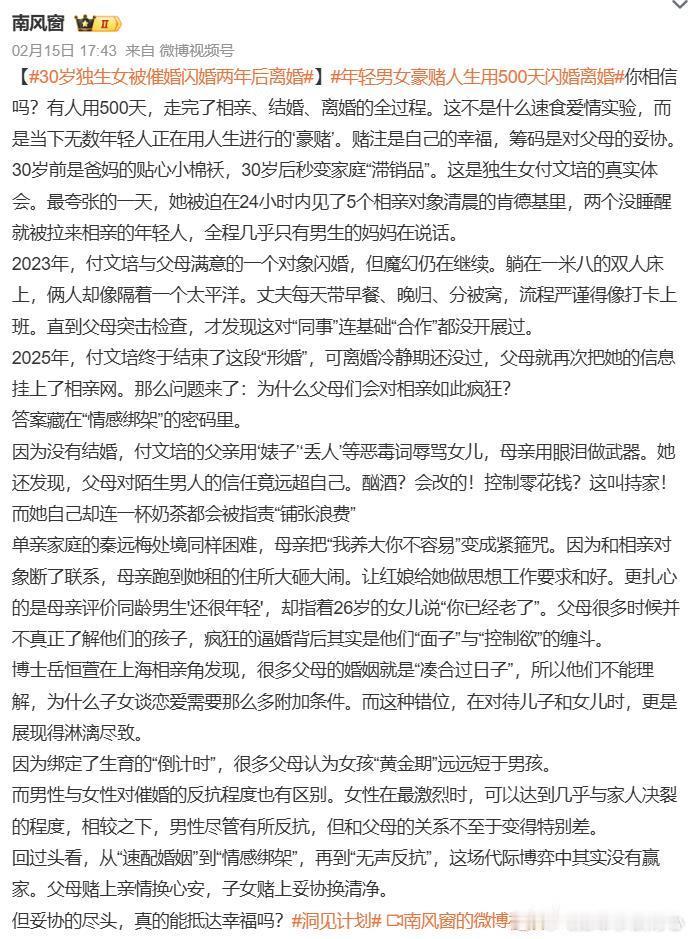新婚那晚,他泡在浴缸里喊:“小满,帮我拿条内裤。”
我手刚搭上门把,整个人僵住了。
小满不是我。
是借住我家的、他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女的。
还没等我脑子转过来,她已经推门进来了。
没敲门。
手里还捏着我昨晚亲手搓洗、晾在阳台的那条灰色平角裤。
她径直走到浴室门口,嗓门亮得像敲锣:“喂!开门!你爹给你送温暖啦!”
我没忍住,冷冰冰回了一句:“你爹坟头草都三尺高了,别乱认亲。”
她扭头冲我咧嘴一笑:“嫂子别生气啊,他就是被我们惯坏的。你可不能太宠他,惯坏了男人,以后有你哭的。”
窗外风突然灌进来,吹得我后颈发凉。
其实婚礼前一周,他们四个就来了——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全是他在老家光屁股玩到大的铁哥们儿。
我们一起布置婚房、挑喜糖、试礼服。
看我抹眼泪,他还抱着我说:“值了,这辈子就为你忙这一回。”
婚宴结束,他说要请兄弟们吃顿家常饭,感谢他们一路帮忙。
我怕他们累着,干脆让他们住家里空房间。
那天大家都喝高了,东倒西歪地躺沙发上聊童年糗事。
我给他们铺好床,叮嘱早点休息。
他在主卧洗澡时,我窝在床上翻婚礼视频——交换戒指、互换誓言、宾客鼓掌……画面暖烘烘的,像裹了一层糖霜。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天底下最幸运的女人。
正傻笑着,忽然听见他喊:“小满,帮我拿条内裤。”
我刚想起身,又停住了。
小满不是我。
是他那帮“兄弟”里唯一的女孩,也是唯一一个敢直接闯进卧室不敲门的人。
我还没回过神,她已经踩着拖鞋啪嗒啪嗒进了屋。
连象征性的叩门都没有。
指尖勾着那条我亲手洗的内裤,晃悠悠走向浴室。
她在门外喊:“喂!开门!你爹给你送弹药补给啦!”
里面传来他带笑的声音:“放洗漱台,滚蛋!”
她立刻回嘴:“你敢对你爹这态度?娶了媳妇忘了娘是吧?”
然后转头对我眨眨眼:“我就知道他洗澡肯定忘带换洗衣物。喝两口酒就忘形,我这当‘爹’的不得操点心?守在门口等着呢。”
我裹紧被子,声音有点抖:“你耳朵这么灵?隔着两堵墙都能听清他说话?”
她耸耸肩,一脸理所当然:“咱俩谁跟谁啊,他放个屁我都知道啥味儿。”
空气安静了几秒。
只有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敲在我心上。
我没再说话。
她也没走。
就那么站在浴室门口,手里还捏着那条属于我的、他的、我们的内裤。
像一个闯入者,又像这个家真正的主人。
而我,坐在床上,像个刚搬进来的租客。
窗外的风还在吹。
我闭上眼,不想看,也不想问。
有些界限,一旦模糊了,就再也划不清了。
有些位置,一旦站错了,就再也退不回来了。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没有争吵,没有爆发,甚至没有一句重话。
但我知道,从今晚开始,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至于后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也许明天醒来,一切如常。
也许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洗澡。
又或者……
我会默默把那条内裤收起来,再也不洗第二遍。
生活嘛,有时候不是靠道理撑下去的。
是靠忍,靠装糊涂,靠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直到某一天,你突然发现——
那个曾经让你觉得“世上最幸福”的夜晚,原来早就埋下了裂缝的种子。
只是当时,你太忙着感动,忘了看清人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