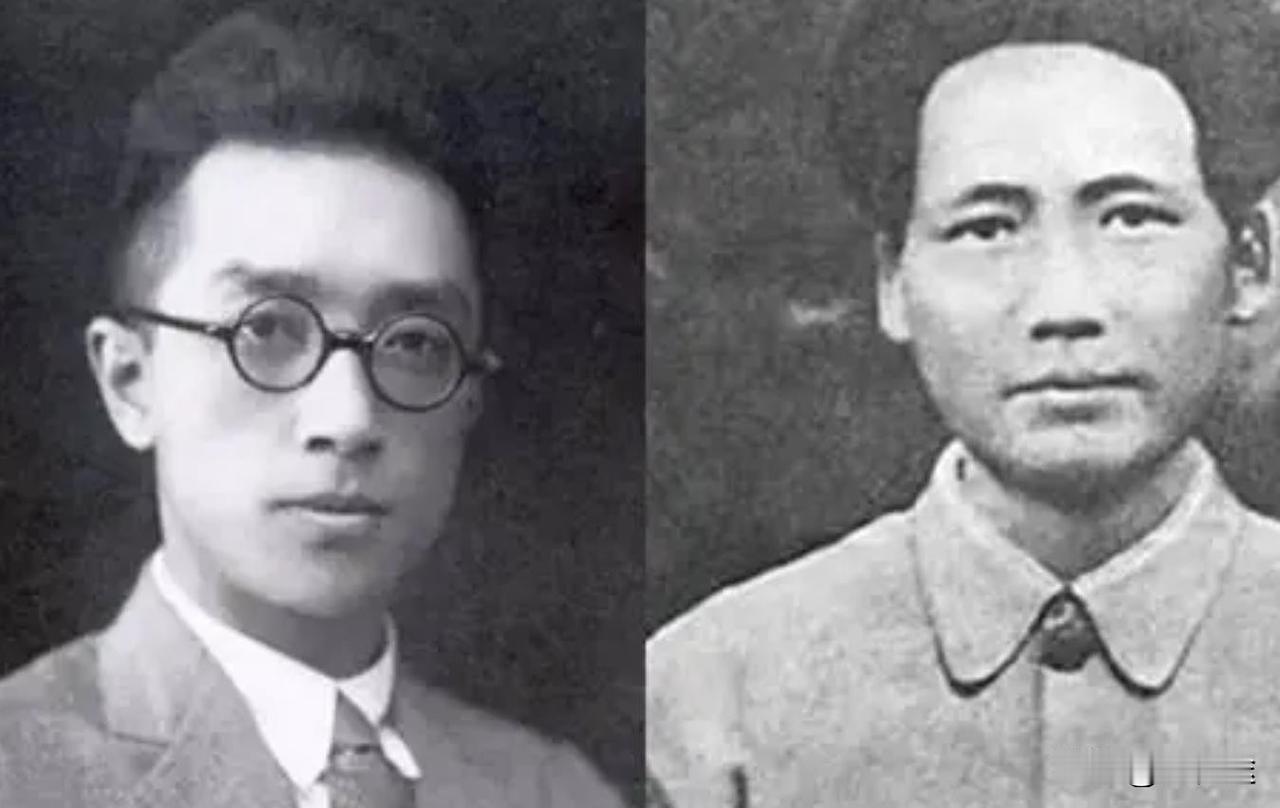1931年,淡出北洋官场、在上海爱多亚路挂牌执业的章士钊,正陷于生计窘迫的境地,这位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饱学之士,虽以律师为业,却因不愿趋炎附势而门庭清冷。 那时候上海滩的律师事务所遍地开花,街头巷尾总能看见挂着烫金牌匾的门脸,可章士钊的事务所门口总是静悄悄的。不是他没本事——当年他在北洋官场摸爬滚打二十年,起草过《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跟梁启超、杨度这些大人物都坐而论道过,连胡适都说他是“学界最有辩才的人”。可偏偏这律师行当,讲究的是“案源靠人脉,输赢看关系”,他偏不按规矩来。 有回法租界一个富商被控诈骗,托人塞给他一箱银元,求他在法庭上“睁只眼闭只眼”,他当场把银元推回去,说:“我章某人的笔,只认得法律条文,不认得钱袋子。”结果案子判下来,富商入狱,他倒落了个“不识抬举”的名声,找他打官司的人更少了。 章士钊不是不懂变通,他太清楚自己要什么。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就跟着黄兴搞革命,后来进北洋政府,本想借一官半职推行法治,可眼看着段祺瑞为了权力拉帮结派,曹锟为了选总统公然贿选,他心凉了。 1926年辞了教育总长,他说“宁肯卖文换米,也不与浊流同污”,可真到了靠本事吃饭的时候,才发现文人风骨在市井里有多“硌硬”。有次他去菜市场买豆腐,摊主认出他,好心少收两文钱,他急得直摆手:“我章某人穷归穷,不能占小便宜,你这豆腐多少钱,我照付。”摊主叹气:“您这样的好人,怎么混成这样?”他苦笑一声,没接话。 转机出现在1932年。那年杜重远在上海办《新生》周刊,因为刊发《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驻沪领事馆告了,罪名是“侮辱友邦元首”,案子闹到江苏高等法院,主审法官知道这案子敏感,谁都不敢接。杜重远急得团团转,朋友提醒他:“找章士钊试试,他敢说真话。”章士钊一开始犹豫——他知道这是块烫手山芋,日本人盯着呢,弄不好要掉脑袋。 可当他翻开卷宗,看见“言论自由”四个字被堂而皇之写在被告的罪名里,想起自己在东京留学时,亲眼见过留学生因为骂清政府被抓,忽然就红了眼。他对杜重远说:“这官司我接定了,哪怕输了,也得让他们看看,中国人还有不怕死的读书人。” 法庭上,章士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站在辩护席上,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新生》周刊的文章只是批评日本天皇的统治,并非侮辱人格。 如果说批评就是侮辱,那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得蹲监狱。”检察官打断他:“日本是我们的友邦,侮辱友邦元首就是破坏邦交!”他提高声音:“邦交靠的是平等尊重,不是卑躬屈膝。如果为了邦交就放弃法律尊严,那我们和亡国奴有什么区别?”台下坐着的旁听者,有学生、有记者,还有几个穿西装的洋人,都攥着拳头,有人偷偷抹眼泪。 这案子拖了三个月,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章士钊每天熬夜查资料,写辩护词,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手指头都被烟熏得发黄。有天深夜,他刚写完最后一页辩护词,妻子吴弱男端来一碗热粥,轻声说:“歇会儿吧,天都亮了。”他抬头看她,眼角的皱纹比十年前多了不少,心里一酸,说:“若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你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别再受我牵连。”吴弱男没说话,把粥碗往他手里塞,转身时背挺得直直的——她是著名女权运动家,当年跟章士钊一起办《民立报》,什么风浪没见过? 最后案子判下来了,杜重远被判一年零两个月,可判决书里明明白白写着“言论自由应受保护”,日本方面虽然不满,却也没法再闹。消息传开,上海的报纸都登了,有人说“章士钊是条汉子”,有人说“这下他该有案子了吧”,可实际上,来找他打官司的还是不多——那些有钱有势的主儿,还是觉得他“太轴”。不过章士钊不在乎,他说:“我当律师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给法律争口气。只要有一个人因为我的辩护得到公平,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后来有人问他,后悔过接那个案子吗?他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翻着一本线装书,说:“后悔?我章士钊这辈子做过的事,没几件是后悔的。当年在北洋官场,我后悔过;现在当律师,我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不然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