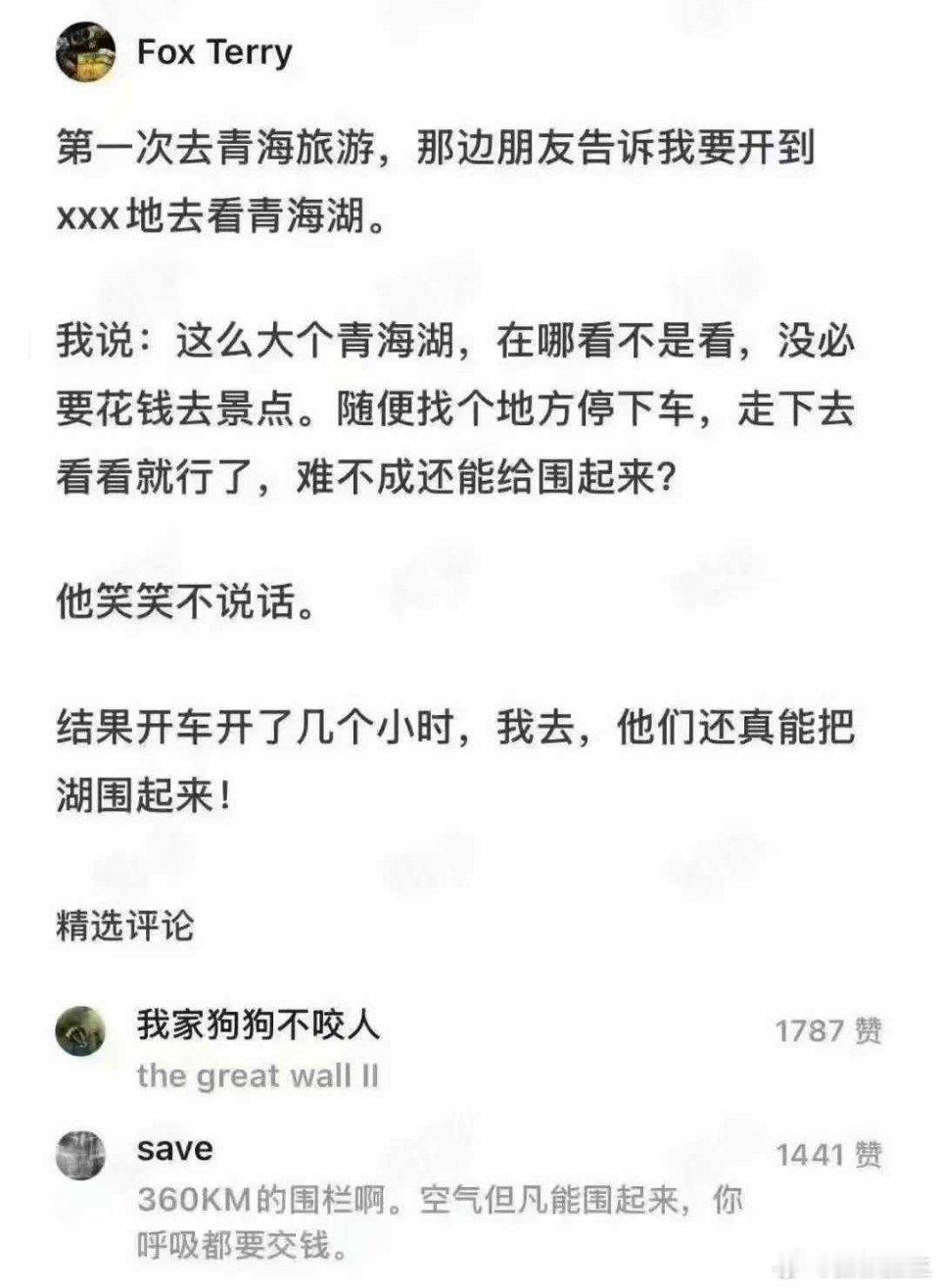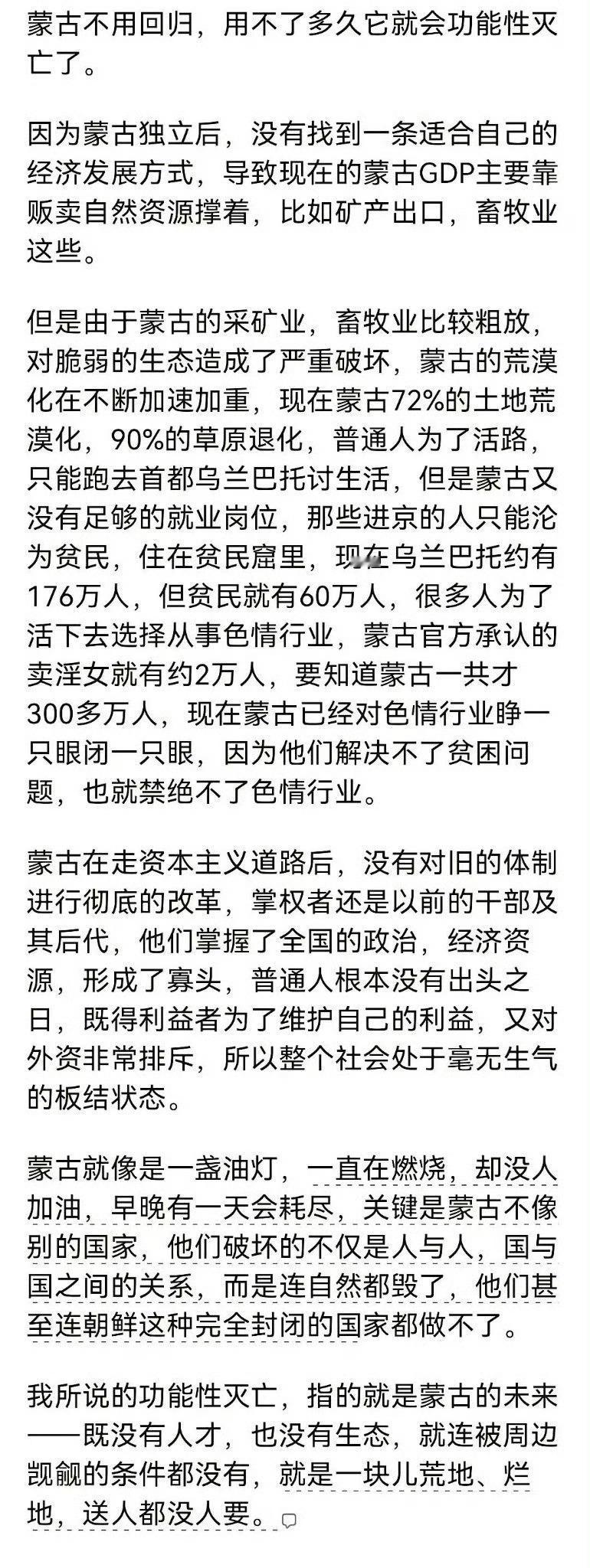牧民开始抱怨?藏羚羊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青藏公路上,浩浩荡荡的羊群,能把车队堵上几公里,司机们递烟闲聊,习以为常。但这“羊满为患”的抱怨,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奇怪?像是某种凡尔赛。因为就在不久前,这片土地上回响的,不是牧民的抱怨,是枪声。 要是现在开车走青藏公路,遇上藏羚羊堵路,可千万别急着按喇叭,司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一群群藏羚羊披着灰白相间的绒毛,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横穿公路,有的低头啃两口路边的青草,有的停下来打量过往的车辆,还有的带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幼崽,一步三回头,那小模样软乎乎的,惹得司机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现在能多到 “堵路” 的地步? 刚好最近,一部叫《生命树》的纪录片同步上映,跟着这部片子走进青海,走进可可西里,你就会找到答案,也能看到太多人与自然相依相守的动人故事。 这段时间,《生命树》是真的火了,连带青海也再次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片子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刻意的煽情,只凭着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可可西里守护者们的日常,每一个画面,都让人忍不住心头一热。 片子里,我们能看到巡护队员们的坚守。可可西里平均海拔四千六百多米,氧气还不到平原的一半,全年平均气温都在零度以下,冬天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四十多度,被称为 “人类生命的禁区”。 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巡护队员们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走进无人区巡护,一走就是几百公里。夏天,他们会不小心陷进沼泽,几个人拼尽全力挖车、推车,喘得连话都说不完整,头痛呕吐是家常便饭。 除了巡护队员,片子里还拍到了很多牧民的身影,他们如今都成了可可西里的生态管护员。 以前,牧民们放牧,偶尔会和藏羚羊产生摩擦,可现在,他们主动放下牧鞭,拿起手机,每天骑着摩托车巡护几十公里,用手机 APP 上传藏羚羊的活动轨迹,还会向路过的游客宣讲生态保护知识。 其实,藏羚羊能有今天的规模,背后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叫 “沙图什” 的奢华披肩在欧美市场走俏,一条披肩能卖到几万美元,可制作一条这样的披肩,要付出三到五只成年藏羚羊的生命。 暴利的诱惑下,无数盗猎分子涌入可可西里,枪声此起彼伏,大量的藏羚羊被猎杀,它们的尸体遍布草原,原本浩浩荡荡的羊群,数量一度锐减到不足两万只。 那时候,可可西里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藏羚羊的骸骨,牧民们听到的,不是羊叫,是刺耳的枪声,看到的,不是奔跑的羊群,是被鲜血染红的草场。 直到 1994 年,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在押解盗猎分子的途中遭到袭击,他独自与十八名盗猎分子对峙,最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救援队伍找到他时,他已经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冻成了一座冰雕,依旧保持着对峙的姿势。索南达杰的牺牲,像一盏灯,点亮了可可西里的保护之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守护者的行列。 可可西里建起专业保护站,以他名字命名的站点成了守护前沿,一批又一批巡护员扎根于此,常年驻守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带,顶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忍受缺氧、暴风雪和风沙,日夜穿梭在沟壑与草场间。 他们没有精良装备,靠着越野车和双脚,一遍遍排查盗猎隐患,收缴猎枪与陷阱,救助受伤落单的藏羚羊,用坚守把盗猎者彻底赶出了这片区域。 1997 年,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不冻泉站、索南达杰站等五个保护站相继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逐步完善,盗猎行为被严厉打击。 国家将藏羚羊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严苛法律斩断盗猎利益链,重典之下,可可西里连续二十多年再无盗猎枪声,曾经的杀戮之地彻底变回安宁净土。 青藏铁路与公路修建时,专门为藏羚羊预留专属迁徙通道,铁路架起高桥,公路留出平缓过道,不打断它们千年不变的迁徙路线。 科研人员在关键路段布设 360 度高清监控,全程记录藏羚羊迁徙、产羔的细节,用精准数据为保护工作提供支撑,让每一步守护都有迹可循。 二十多年的接力守护,让藏羚羊种群迎来爆发式恢复。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从不足两万只增长到七万多只,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总数突破三十万只,曾经濒危的物种,如今成了草原上随处可见的常客。 每年夏天,卓乃湖周边都会聚集上万只待产的母羊,新生羊羔落地不久就能跟着母亲奔跑,种群延续有了最扎实的保障。 《生命树》火了,青海火了,可我们更希望,火的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不仅仅是一片土地,更是这份守护自然、敬畏生命的初心。 这片曾经被枪声打破宁静的土地,终于找回了生命本该有的喧嚣,藏羚羊的脚步,踏响着高原的脉搏,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动人、最有力量的生命乐章。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源:西海都市报2026-02-02——《突破7万只!现实中的可可西里成了藏羚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