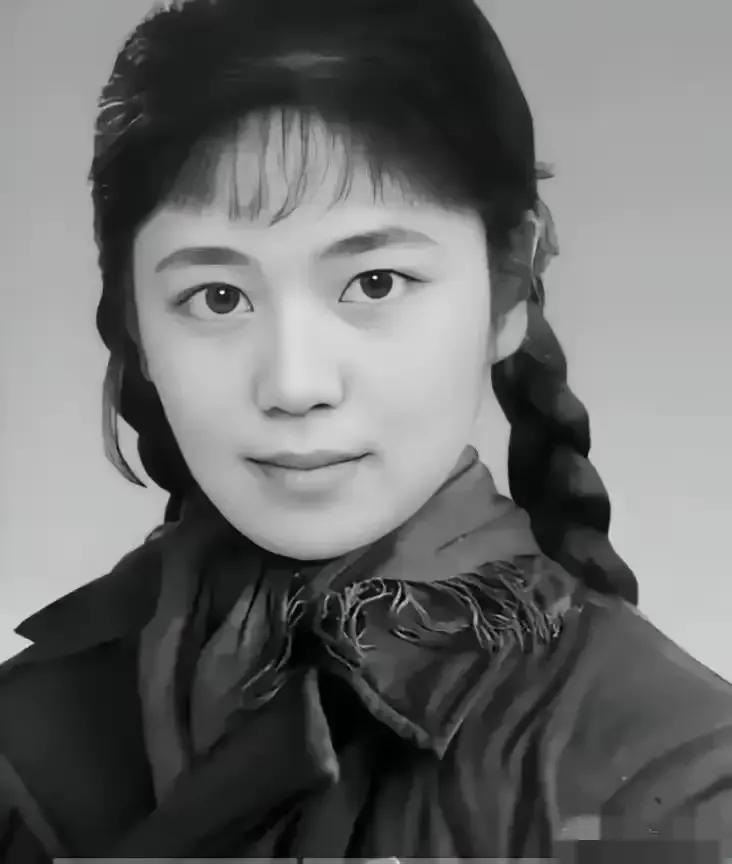火车一路向北,窗外那片待了八年的黑土地越来越模糊。于文娟攥着那张薄薄的返城证明,手心全是汗,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大块。刚才月台上那个拼命追赶的身影,这会儿怕是已经变成一个小黑点了吧。她不是狠心,是知道没结果。他是当地人,根扎在北大荒,她是必须回城的知青,两条路从一开头就没并到一块儿去。眼泪早就被风吹干了,脸上绷得发疼。 踏进家门那一刻,屋里的气氛比她想得还冷。母亲站在屋子当间,眼神在她脸上停了两秒,就移到了她脚边那个打着补丁的行李包上。“回来了?”声音平平的,听不出喜怒。弟弟缩在里屋门边,探出半个脑袋,又赶紧缩回去。于文娟“嗯”了一声,喉咙发紧,那句“妈,我回来了”堵在嗓子眼,怎么也吐不利索。 母亲接下来的话,像一盆冰水,把她从头浇到脚。“家里没你地方了。你弟弟眼看要结婚,这屋子就这么大。你爸走得早,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把你盼回来,就算对得起你了。”话里没有商量,就是通知。于文娟愣在那儿,行李从手里滑下来,“咚”地一声砸在地上。她想过回家日子会难,得重新适应,得找活路,可万万没料到,连门都进不去。那个她梦里想了无数遍的、能遮风避雨的家,连门槛都不让她迈。 街上风刮得呜呜响,她拎着行李,漫无目的地走。返城的那点喜悦,早在母亲关门的那声闷响里碎得干干净净。原来,城是回了,家却没了。街道两旁是熟悉的景象,又透着陌生的疏离。标语换了新的,路上的年轻人穿着打扮也不同了,她觉得自己像个闯错了地方的局外人,浑身都透着那股黑土地带来的“土腥气”,格格不入。 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在火车站旁的小招待所换了三晚的床位。同屋的有个姓李的大姐,也是返城知青,情况比她好点,娘家挤挤还能住,可工作没着落,天天唉声叹气。“咱们这种人,乡下待久了,回来哪哪都赶不上趟。工厂招工嫌岁数大,没技术;街道安排,尽是临时工,糊口都难。”大姐的话,句句砸在于文娟心坎上。她这才真切地感到,那列火车载她回来的,不是终点,是另一个更难的开头。 走投无路时,她想起了列车站台上那句决绝的“别再见了”。现在品出来,里头不止是给那段感情的告别,好像也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一种预告。她有点想笑,笑自己天真,还以为最大的苦是离别,没想到生活把更硬的石头堵在了她面前。 于文娟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偶然。那段特殊年月里,成千上万的青年被时代的浪潮卷向远方,又在浪潮退去时被搁浅在陌生的岸边。他们身上带着两个世界的印记:一个是想回却已疏离的故乡,一个是想忘却已刻入青春的他乡。家庭空间的逼仄、社会衔接的断层、情感世界的撕裂,这些后返城时代的“综合症”,往往比田野劳作更消磨人。政策允许你回来,却未必有能力安顿好每一个具体的人生。于文娟母亲的无奈,是那个年代许多城市家庭资源枯竭的缩影;而于文娟的飘零,则是集体叙事背后,个体必须独自吞咽的冷暖。 她最终没有去找那个奔跑的恋人。不是不想,是不能。自己的脚跟都没站稳,哪还有力气去触碰那份沉甸甸的牵挂。她在街道生产组找到了糊纸盒的临时工,在筒子楼里租了一个睡觉的角落。日子是苦水泡着的,但总得往下过。夜深人静时,她偶尔会望向北方,心里那点没熄透的火苗,微微晃一下。她知道,脚下的路,只能自己一步一步踩出来。时代的列车轰隆向前,载走了她的八年,也载走了很多东西。能抓住的,唯有当下这具还得活下去的身躯,和一颗不敢再轻易许诺、却依然得学着坚硬的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