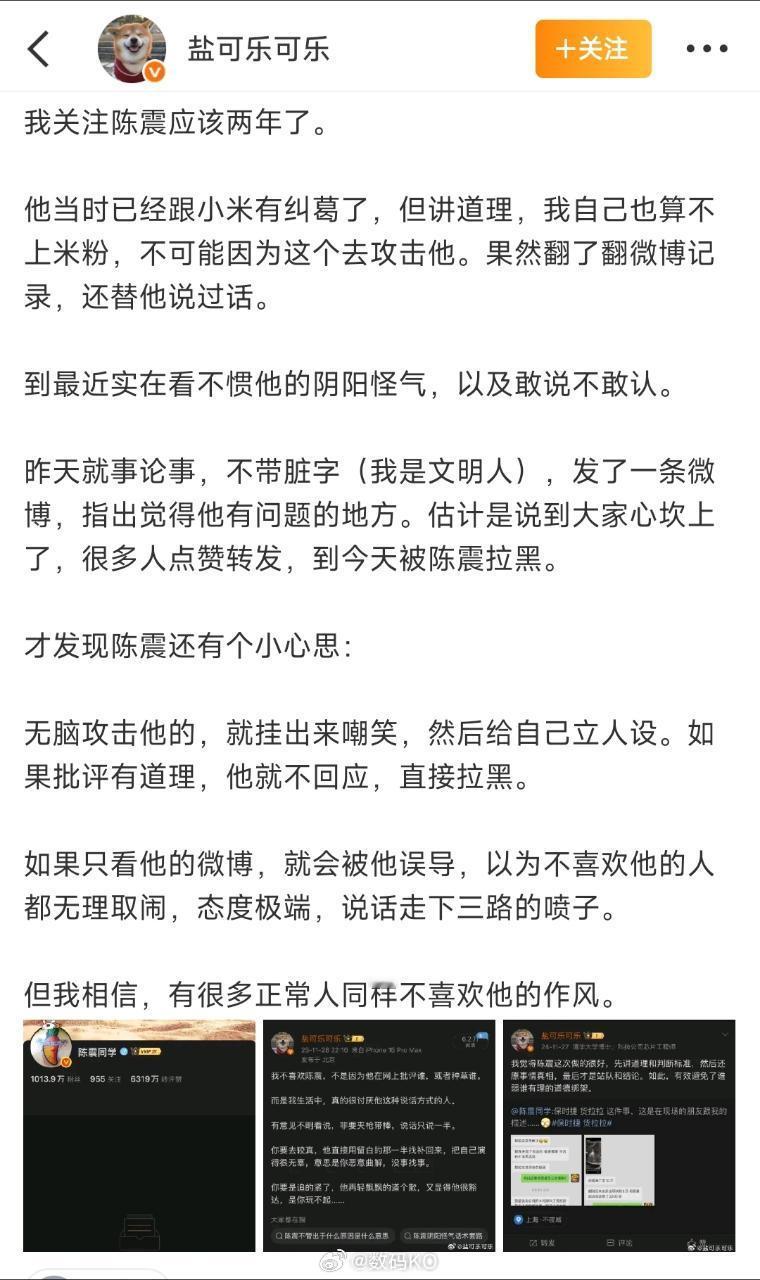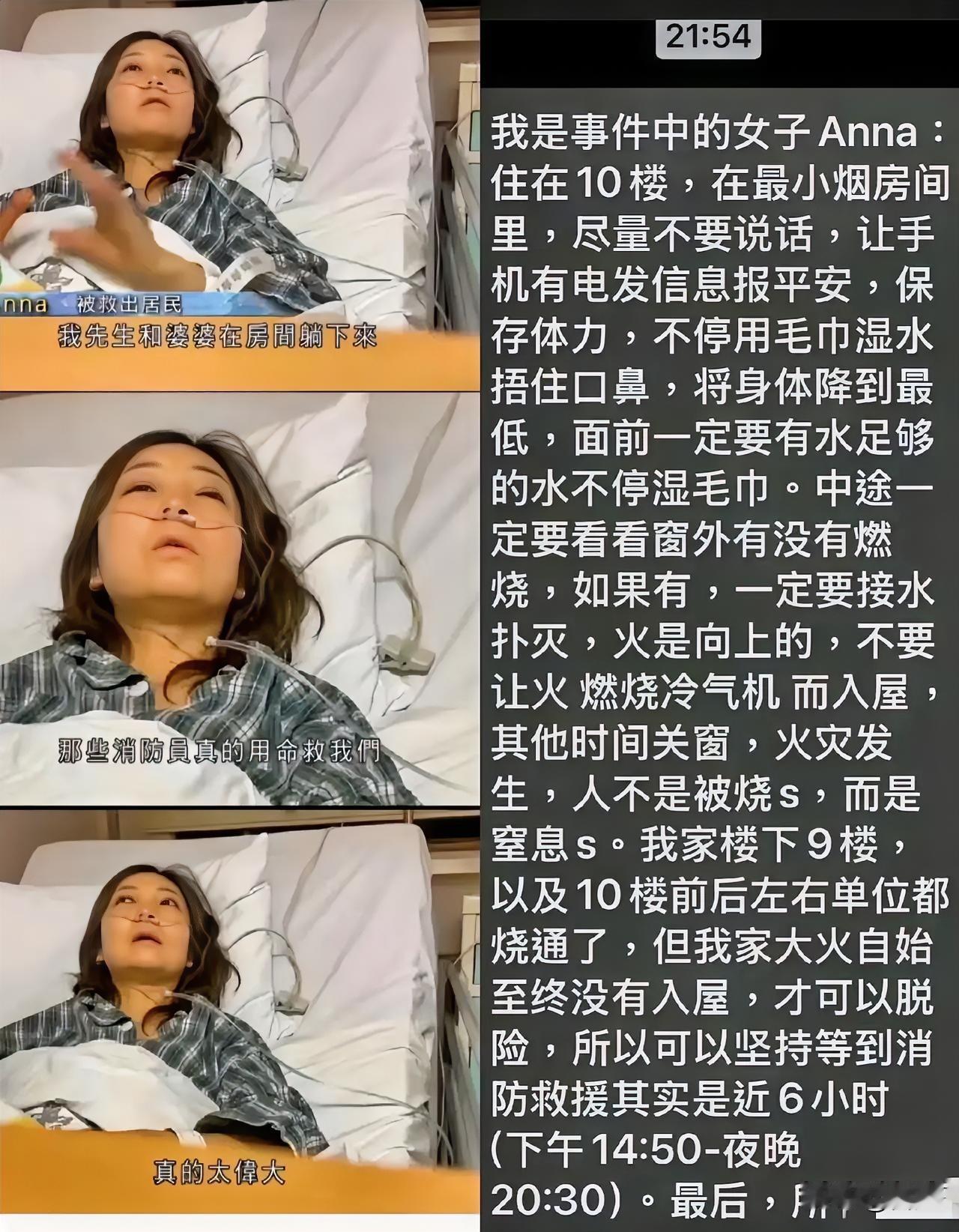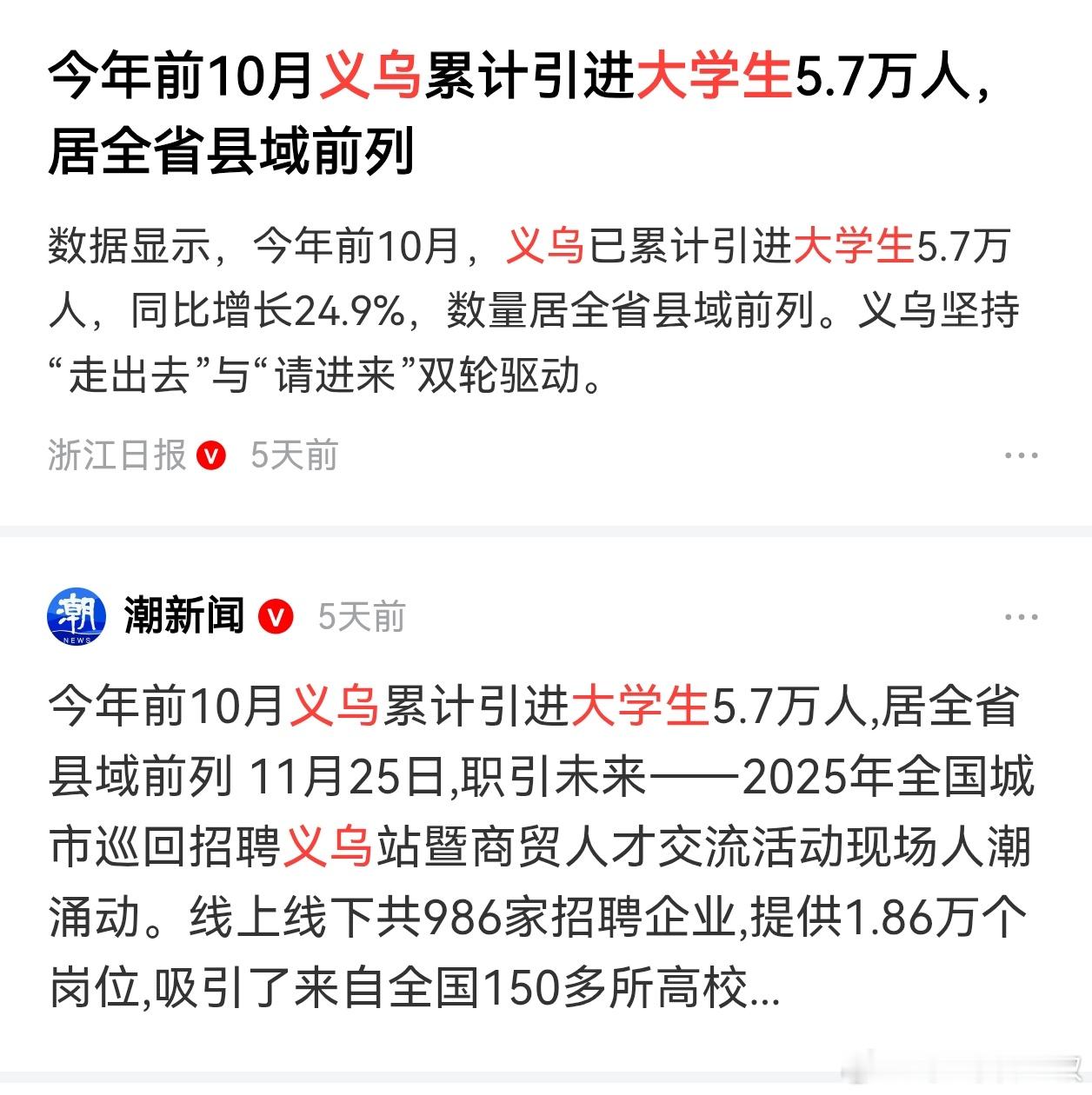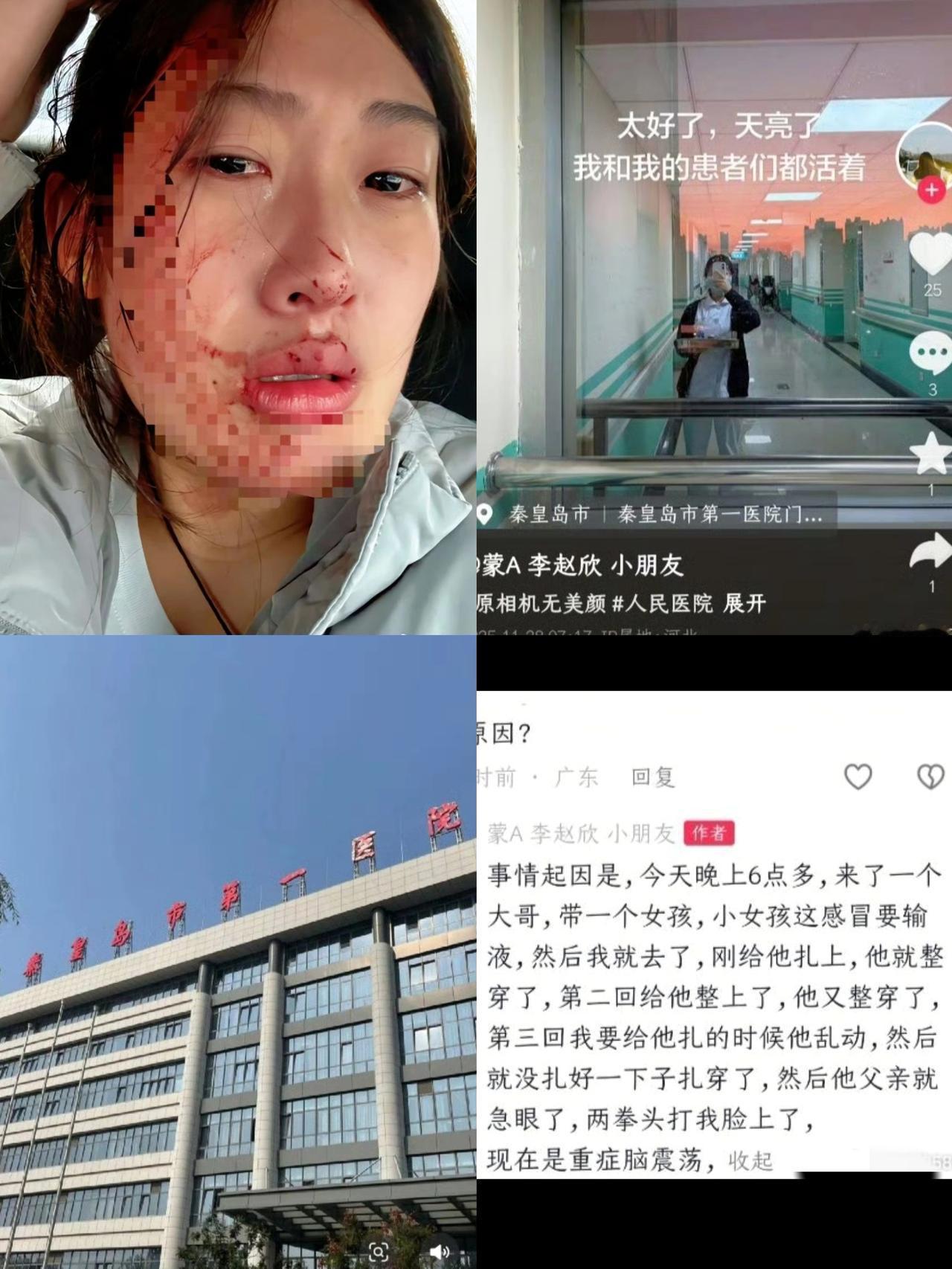女人的丈夫因为车祸去世,她拿到了 66 万赔偿款。一天,小叔子对她说:嫂子,你拿 60 万给我创业,我给你打借条。女人把钱借给了小叔子,小叔子也给她打了张借条。几天后,小叔子找借口把借条要了回去。但女人说:我们是亲戚,我信得过自己的小叔子。现在倒好,那 60 万要不回来了,小叔子连我电话都懒得接了。 丈夫走的那天,急救室的灯灭了整三年零七天。 赔偿款到账时,她把存折塞进衣柜最底层的铁盒子,上面压着丈夫生前常穿的那件灰色夹克——拉链头早磨得发亮,还沾着去年冬天的雪渍。 66万,银行短信提示音在凌晨三点跳出来时,她盯着天花板数到第一百二十八只羊,才敢确信这串数字能撑着她和刚上小学的儿子过到他成年。 小叔子来的那天是个周末,她正蹲在阳台给丈夫种的绿萝浇水。 “嫂子,”他搓着手站在门口,皮鞋尖蹭掉了一小块墙皮,“我看中个项目,稳赚,你先借我60万,我给你打借条。” 她直起身时,水壶底的水在瓷砖上洇出一小片深色,像块没擦干净的泪痕。 “都是一家人,”她听见自己说,声音比绿萝叶子还轻,“借条就不用了吧?” “那不行,”小叔子从包里掏出纸笔,钢笔尖在纸上划拉的声音很响,“亲兄弟明算账,我给你写清楚——借款60万,一年后还,利息按银行的来。” 她把存折递给他那天,阳光斜斜地照在茶几上,借条压在玻璃下面,蓝黑墨水的字迹看着挺实在。 三天后的傍晚,小叔子又来了,手里提着袋苹果,说是刚从批发市场批的。 “嫂子,借条放你那儿怕你弄丢,我拿回去锁保险柜里,反正咱们这关系,还能赖你不成?”他笑着说,伸手去拿茶几上的玻璃镇纸。 她犹豫了一下——那借条她昨天还拿出来看过,折痕处已经有点发白。 “也是,”她把镇纸挪开,“你哥不在了,咱们更得处好,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他把借条揣进裤兜时,苹果滚到地上一个,他弯腰去捡,她看见他后颈沾着片枯叶。 再联系是一个月后,儿子学费该交了,她拨通小叔子的电话。 忙音。 她以为是信号不好,走到窗边又打了一次——还是忙音。 第二天早上,她换了座机打,通了,响了七声,被挂断了。 她坐在冰冷的木椅上,看着衣柜底层那个空铁盒子,突然想起丈夫生前说过的话:“咱妈总说小伟心活,你以后跟他打交道,多留个心眼。” 当时她还笑丈夫小心眼,现在那笑声好像还在客厅里飘着,却比窗外的秋风还凉。 或许他是真的遇到难处了?她这样安慰自己,毕竟创业哪有一帆风顺的。 可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接呢?哪怕说句“嫂子再等等”,她也能宽心些。 那天她去菜市场,碰见以前的邻居张婶,张婶拉着她说:“前几天看见你小叔子开着新车呢,说是刚提的SUV,三十多万。” 她当初为什么愿意借?不只是因为他是丈夫的弟弟,更因为丈夫走后,婆婆哭着拉着她的手说:“以后小伟就是你半个儿,有难处你们互相帮衬。” 她信了这话,信那笔钱能帮小叔子立住脚,也信自己能在婆家保住最后一点体面——丈夫不在了,她不想让别人说她是个只顾自己的寡妇。 可体面这东西,有时候比纸还薄,一捅就破。 现在抽屉里只剩那张6万的存折,儿子的兴趣班停了,冬天的羽绒服还没买。 她再没去过婆家,逢年过节婆婆打来电话,她也只是嗯啊两声就挂了——有些伤口,不碰都疼。 后来有朋友问她后悔吗?她想了想说,后悔的不是借钱,是没把那句“亲兄弟明算账”当真;有些信任,得用凭证兜底,不是心热就能焐热的。 前几天整理丈夫遗物,她又翻出那件灰色夹克,拉链头还是那么亮。 她把夹克贴在脸上,闻到一股淡淡的烟草味,混着阳光晒过的味道。 要是他还在,会怎么说呢? 她不知道。 只知道那天下午,她把60万的转账记录截图,存在了手机加密相册里——不是为了讨债,是为了提醒自己,日子再难,也得活得清醒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