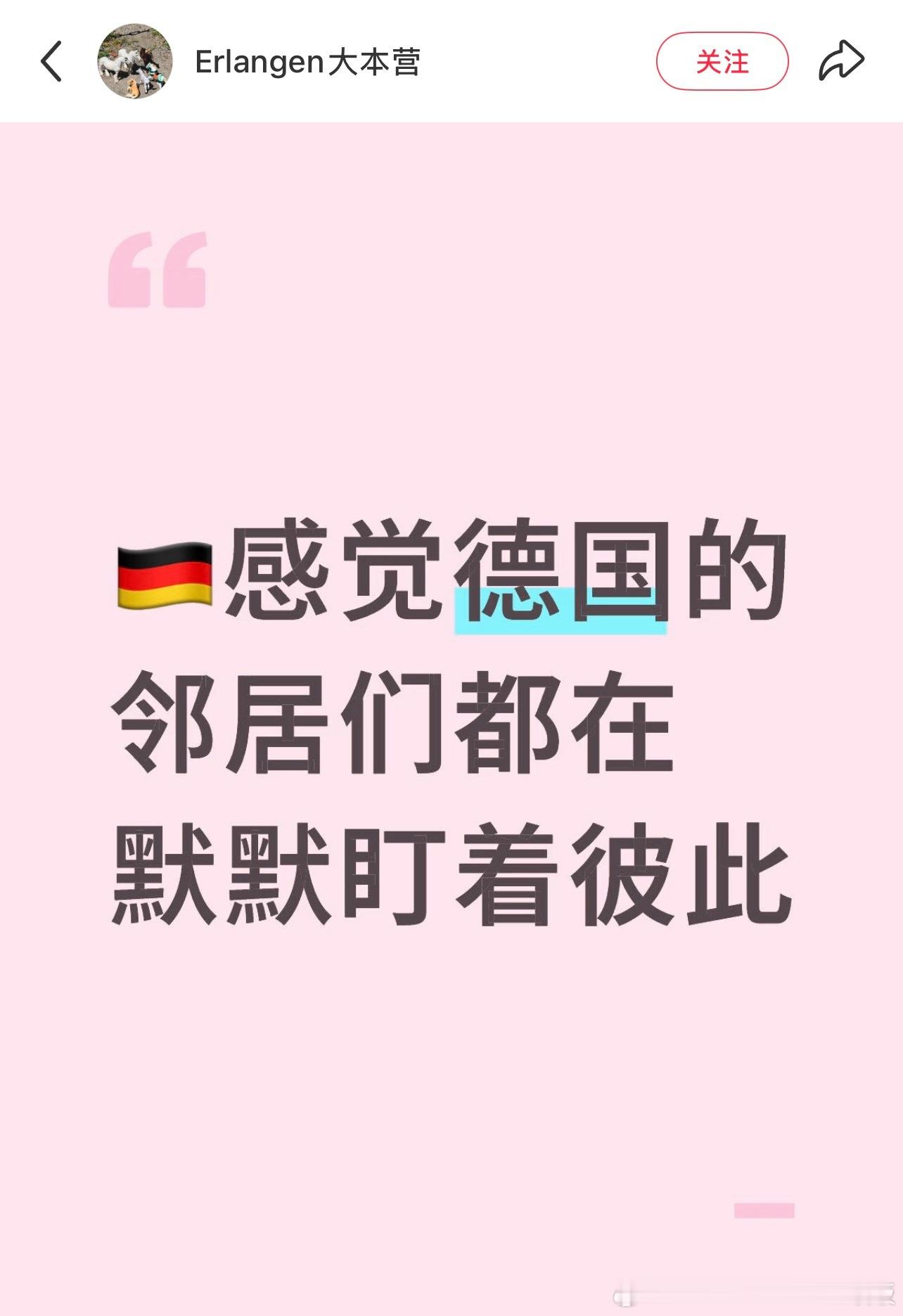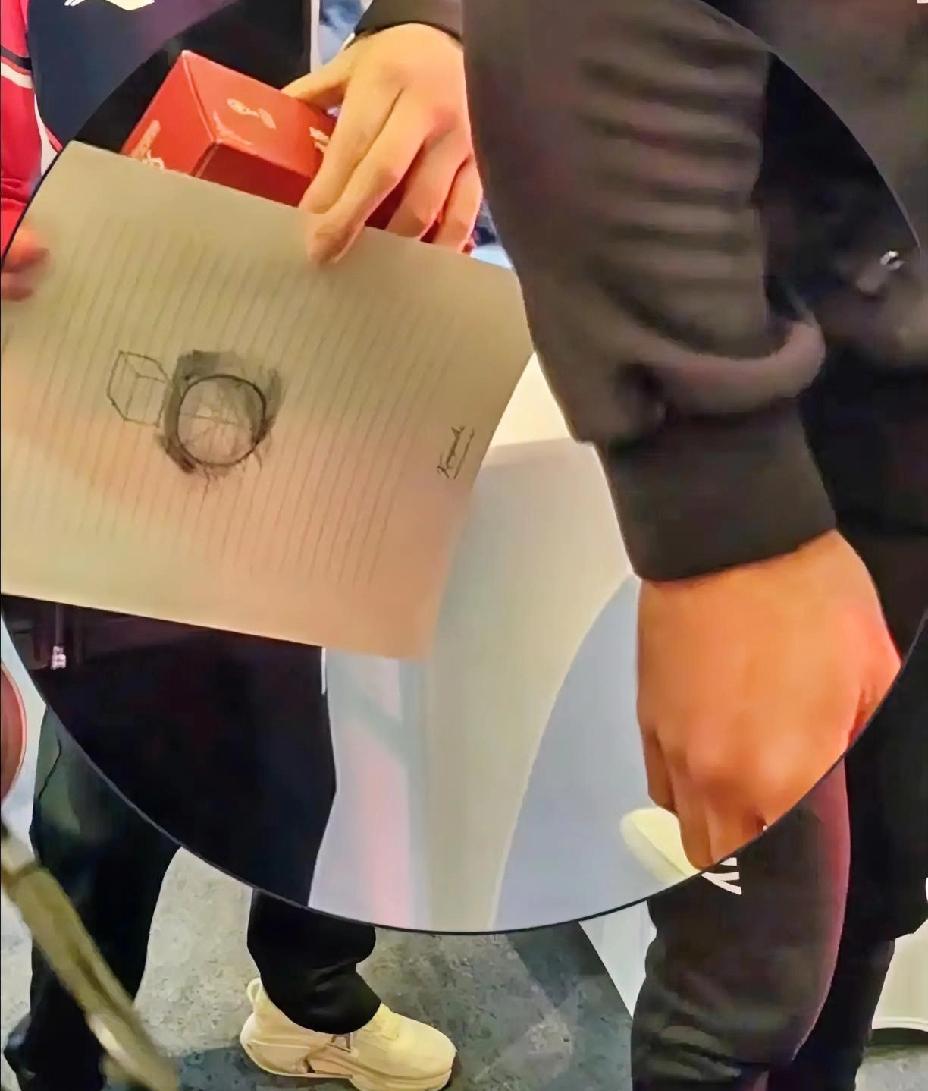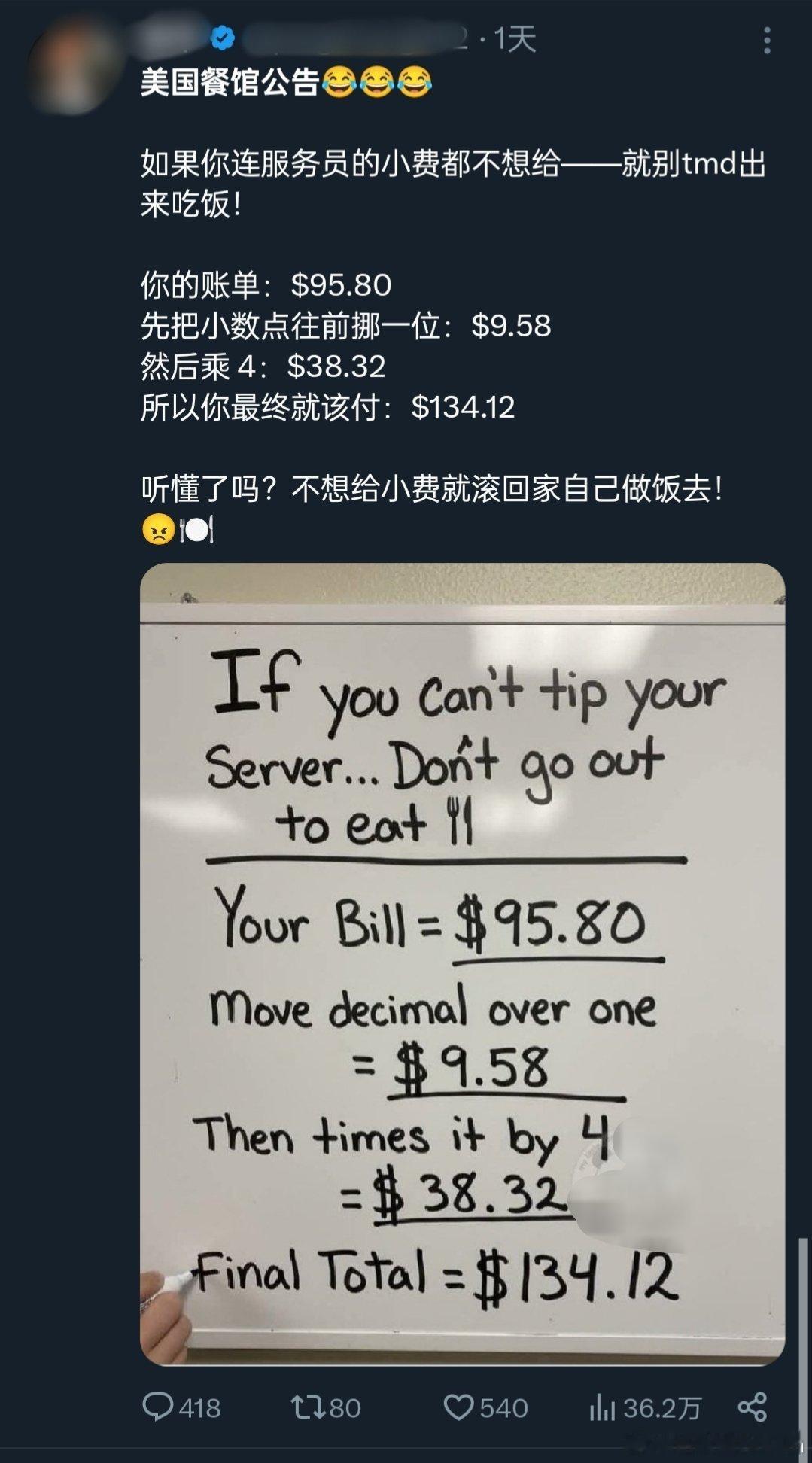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陈松年步行十多里路去为父亲扫墓。 那条土路被晨露打得湿漉漉的,踩上去软绵绵的。陈松年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裤脚沾满了泥点子。天还没完全亮,远处村子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他手里拎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三炷香、一叠黄纸,还有两个干硬的馒头。这条路他每年都要走一趟,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方向。田埂边的野草一年比一年茂盛,就像他心里的某些东西,悄无声息地疯长。 那时候的扫墓和现在不太一样。没有鲜花,没有精致的供品,连磕头都得趁着四下无人。陈松年的父亲是在特殊年代里走的,具体怎么回事,村里人都讳莫如深。他只记得父亲被带走那天,母亲死死攥着他的手,指甲掐进他肉里。后来收到通知去领遗物,只有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半包烟丝和一本缺了页的《水浒传》。坟是后来悄悄立的,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就找了个扁平的石头刻上名字。 风里带着股潮湿的泥土味,混着刚烧完的纸钱灰烬的气息。陈松年蹲在坟前,看着火苗一点点吞噬黄纸,忽然想起父亲教他认字的那个下午。也是这样的春天,柳树刚抽芽,父亲用树枝在地上写"明月松间照",说他的名字就取自这里。可后来明月被乌云遮住了,松树也被狂风摧折。这些念头像针一样扎着他,但他不敢说,只能默默烧着纸,让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都随着青烟飘散。 那年头扫墓是件冒险的事。隔壁村的老王去年清明上坟被人举报,还在公社大会上作了检讨。陈松年每次来都要绕好几里路,假装是去走亲戚。有次遇见巡逻的民兵,他赶紧躲进油菜花田里,金黄色的花瓣落了一身,心跳得像打鼓。可他还是年年都来,仿佛这条路成了他与过去唯一的连接。母亲临终前抓着他的手说:"别让你爹成了孤魂野鬼。"这句话像烙印似的刻在他心上。 纸钱快烧完了,灰烬在风里打着旋儿。陈松年从布袋里掏出那两个馒头,仔细摆在石头前。他记得父亲最爱吃刚出笼的白面馒头,总要就着大葱蘸酱。可现在连白面都是稀罕物,这两个杂粮馒头还是他省了三天的口粮。他跪下来磕了三个头,额头抵在冰凉的土地上,突然觉得鼻子发酸。抬起头时,看见远处山坳里也有几处青烟袅袅升起,原来这条路上从不孤单。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那条土路早就修成了水泥路,开车十分钟就能到。父亲的坟前立起了大理石墓碑,每年清明都摆满鲜花供品。可陈松年还是会想起一九七六年那个清晨,露水打湿的裤脚,怀里揣着的冷馒头,还有烧纸时小心翼翼环顾四周的心情。有些印记就像胎记,永远擦不掉。时代在变,路在变,但总有些东西要有人记得,要有人走十几里路去守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