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广人稀,原住民本来就不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六七十年代大批甘肃人移居新疆,有些地方整村整社几乎都是甘肃人,虽历经几代人,现在连口音都基本没怎么变。 在乌鲁木齐街头,牛肉面馆里传来熟悉的“牛大碗,辣子多放”的甘肃方言。 从1950年代徒步穿越天山的甘肃农民,到如今在写字楼里用乡音谈生意的第三代移民,300万甘肃人在新疆的土地上扎根,却固执地保留着祖辈的口音。 新疆与甘肃的缘分,始于两千年前张骞凿空的丝绸之路。 清代乾隆年间,甘肃贫民被招募至乌鲁木齐屯田。 数百户人家带着犁铧与种子,在戈壁滩上开垦出第一片绿洲。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甘肃青壮年组成“运粮队”,用骆驼驮着军粮穿越吐鲁番盆地。 许多人就此留下,成为“新疆最早的甘肃移民”。 19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迁徙迎来高潮。 甘肃河西走廊干旱肆虐,粮食亩产不足百斤,农民李老汉带着全家五口,推着独轮车踏上西行之路。 他们沿着兰新铁路线徒步七天七夜,抵达库车时,发现当地生产队已有半数同乡。 “老乡见老乡,心里不发慌”。 正是这种地缘纽带,让迁徙队伍像滚雪球般壮大。 1970年代兵团扩编,甘肃移民再次涌入。 乌鲁木齐碾子沟收容站里,上千名无身份者挤在大通铺上,等待兵团单位挑选。 青年王建军被选中去石河子农场:“到了那儿,记得写信回来。” 这一走,就是四十年。 甘肃与新疆的距离,用“咫尺天涯”形容最贴切。 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直线距离1700公里,普通火车要跑24小时,动车也需12小时。 这个距离,甘肃向东能跨越陕西、山西、河北三省,向西却只隔一座星星峡。 地理的相邻性,让迁徙变得“顺理成章”。 气候的相似性,也更降低了生存的适应难度。 甘肃的戈壁滩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同属干旱区,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昼夜温差大。 甘肃移民带的糜子种子,在新疆绿洲里长得比老家还好。 他们腌的咸菜、酿的醋,味道与河西走廊的村庄别无二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似的生存环境,让甘肃人在新疆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文化的共通性则消解了乡愁。 兰州牛肉面在乌鲁木齐开遍大街小巷,臊子面、浆水面成了社区食堂的招牌。 回族聚居区的阿訇,能用甘肃方言诵读《古兰经》。 连吵架拌嘴的用词,都带着陇东高原的粗粝与直爽。 迁徙的核心动力,始终是“生存”二字。 1950年代的甘肃移民,是为了逃离饥饿。 1970年代的兵团青年,是为了摆脱贫困。 21世纪的务工者,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这句俗语在新疆与甘肃之间,演绎出跨越半个世纪的奋斗史。 在阿克苏的棉田里,甘肃妇女张秀兰带着儿媳采摘棉花,手指翻飞间,白花花的棉絮装满编织袋。 “在老家种小麦,一亩地收800斤;在这儿种棉花,一亩能卖3000块。”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身上。 他们的父辈用独轮车推来了生存的希望,他们则用知识和技术改变了新疆的面貌。 最令人称奇的,是甘肃移民的“口音执念”。 六代人过去了,许多家庭的方言依然带着浓重的陇东腔调。 乌鲁木齐的出租车司机刘师傅,祖籍甘肃定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却坚持用甘肃话和乘客聊天。 “娃娃们在学校学普通话,回家就得说家乡话,不然忘了根咋办?” 这种坚守源于深刻的文化认同。 在昌吉的“甘肃村”,老人们定期举办“乡音茶话会”,用陇东方言讲述祖辈的迁徙故事。 在伊宁的清真寺里,阿訇用甘肃话讲解经文,年轻信徒们听得津津有味。 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们,都会用夹杂着甘肃方言的普通话背诵唐诗。 更微妙的是“文化融合”的智慧。 甘肃移民既保留了祖辈的习俗,又吸收了新疆的元素。 “入乡随俗”与“守土有责”的平衡,让他们在新疆的土地上,活成了独特的“甘肃新疆人”。 如今的甘肃移民,早已不是当年的“外来户”。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新疆2200万人口中,甘肃籍占比超过13%,成为除维吾尔族、汉族之外的第三大族群。 更深远的变化在于“文化输出”。 甘肃的牛肉面、酿皮子在新疆遍地开花,甚至反向输出到中亚国家。 甘肃的秦腔剧团在乌鲁木齐演出,场场爆满。 甘肃的非遗技艺,剪纸、泥塑,成了新疆旅游的特色纪念品。 站在乌鲁木齐的红山之巅俯瞰全城,能看到甘肃移民修建的铁路、厂房、学校,也能听到从社区大院里飘出的秦腔和花儿。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跨越半个世纪的“迁徙交响乐”。 或许,这就是甘肃人留给新疆最珍贵的礼物。 是一种在变迁中坚守、在融合中创新的文化基因,一种“走到哪里都不忘本”的民族精神! 主要信源:(中国甘肃网——总觉得看不够的新疆 北京日报客户端——白皮书: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发展均衡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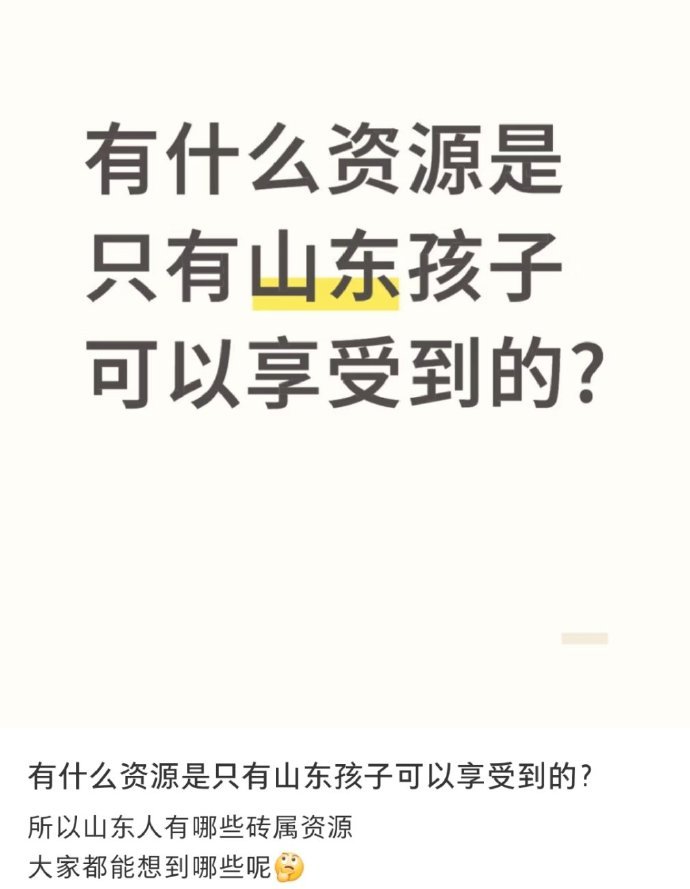





![中国最有灵魂的山,甘肃第一:[捂脸哭][捂脸哭][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631742800196482947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