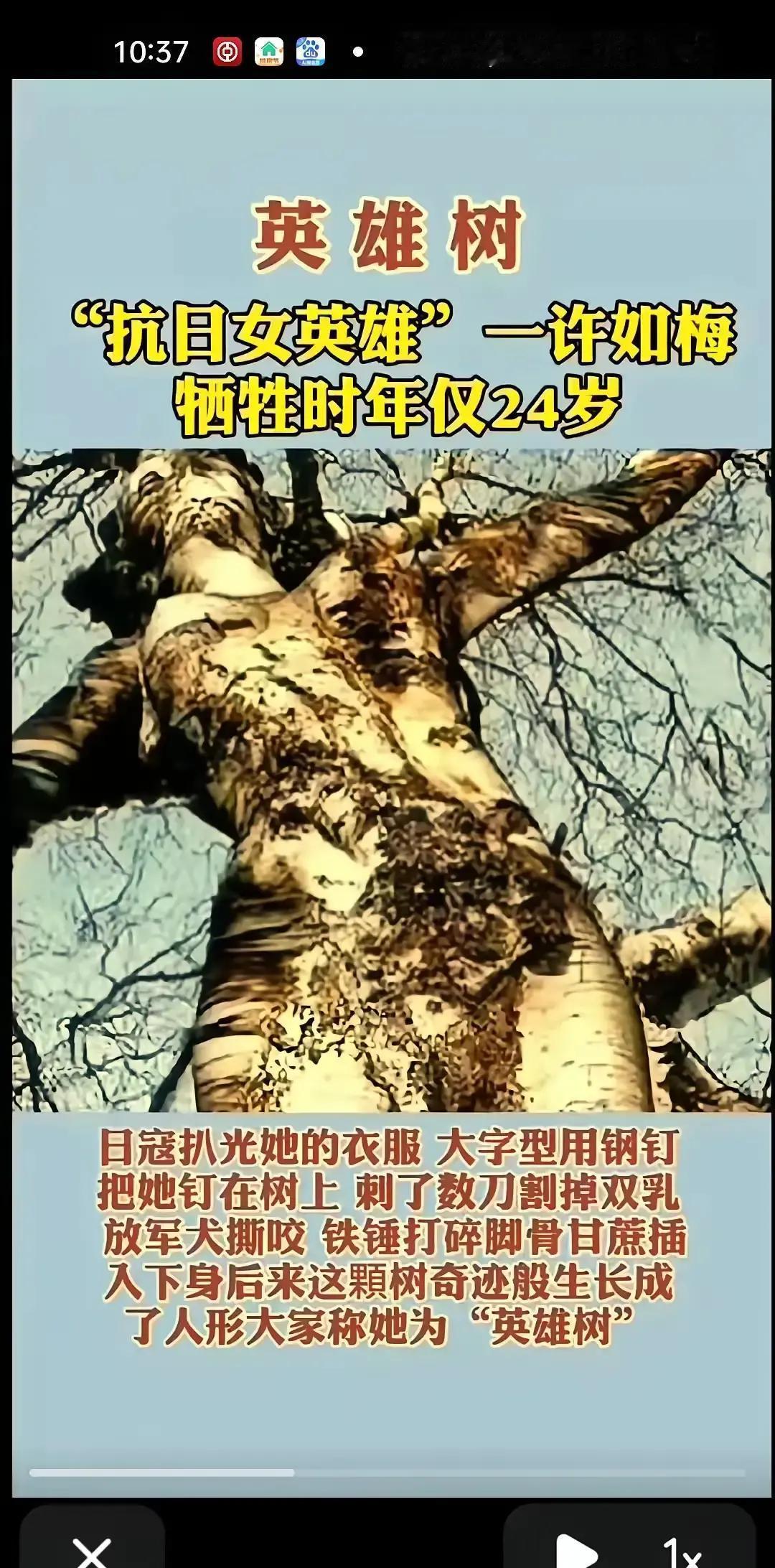你敢信吗? 70多年前,一个普通的30岁男人,被敌人塞进烧红的铁皮桶里,皮肉烫得滋滋响,烙铁还往肉里按,惨叫震得审讯室都在颤,却硬是半个字的秘密都没吐! 这个男人叫陈守义,老家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小村落,打小跟着爹娘种几亩薄田,日子清苦却踏实。22岁那年,日军闯进村子,烧了他家的茅草屋,爹为了护着粮袋被刺刀挑伤,没几天就走了,娘带着他逃荒路上染了病,也没能熬过去。孤苦伶仃的陈守义揣着爹娘留的半块粗面馍,在寒风里走了三天三夜,遇上了正在组织群众转移的游击队,看着战士们为了保护老百姓拼命的模样,他抹了把眼泪,当场就要求参军。队伍里的人见他实在,又肯吃苦,便收下了他,分配他做情报传递工作,这一做就是八年。 陈守义没读过书,认不全几个字,传递情报全靠记,哪怕是长长的联络暗号,他念个两三遍就能背得丝毫不差。每次出门送信,他都装作赶集的小贩,肩上挑着担子,里面藏着卷在油纸里的情报,裤脚绑着备用的联络信物。有回遇上敌人盘查,他心里发紧,手心攥得全是汗,却硬是笑着递上担子让敌人翻,敌人搜了半天只找到些零散的针头线脑,骂了句穷酸就放他走了,走出老远,他的后背都湿透了,却没敢回头看一眼。 30岁那年深秋,陈守义接到任务,要把一份重要情报送到邻县的游击队驻地。出发前,他特意回了趟临时住处,摸了摸枕头下娘留的银镯子,那是娘唯一的遗物,他一直带在身边,想娘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可他没想到,队伍里出了叛徒,把他的行动路线透给了敌人,他刚走到半路,就被埋伏的敌人围住了。敌人把他绑到审讯室,先是好酒好菜招待,劝他交出情报,说出队伍的藏身地,许他高官厚禄。陈守义瞥了眼桌上的酒菜,一口没动,只冷冷地瞪着敌人,骂他们是丧尽天良的刽子手。 软的不行,敌人就来硬的。先是用鞭子抽,他的衣服被抽得破烂不堪,身上全是血痕,疼得他直咧嘴,却还是梗着脖子不说话。敌人急了,就烧红了铁皮桶,几个人架着他往里面塞。滚烫的铁皮贴在皮肤上,瞬间就起了泡,滋滋的声响里混着皮肉烧焦的味道,他疼得浑身抽搐,惨叫一声接一声,震得审讯室的窗户都嗡嗡响。敌人还嫌不够,又拿来烧红的烙铁,狠狠往他胸口按,青烟冒出来的时候,陈守义疼得昏了过去,敌人用冷水把他泼醒,接着逼问,他睁开眼,嘴里全是血沫,却只挤出一句“不知道”。 就这样,敌人折磨了他三天三夜,能用的酷刑都用了,陈守义的身子早已不成样子,意识也模糊了,可关于队伍和情报的半个字,始终没从他嘴里吐出来。最后一天,敌人见实在问不出东西,就把他拖到了野外,枪响的时候,他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只银镯子,眼里望着的方向,正是游击队驻地的方向。后来,战友们找到了他的遗体,从他贴身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他用血水歪歪扭扭写的几个字:“别管我,守好老百姓”。 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火早已平息,陈守义的名字或许没能被太多人记住,可他这样的人,却撑起了那段艰难岁月里的希望。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平凡的普通人,有着牵挂的亲人,有着朴素的愿望,可当家国蒙难,他们就愿意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挡住风雨,用坚定的信念守住秘密。我们如今能安稳地过日子,能踏踏实实地工作生活,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无数个像陈守义这样的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他们的付出,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该永远被铭记。 英烈的热血滋养了这片土地,他们的信念传承在每一代人心里。不忘过去,才能珍惜当下;铭记先烈,才能砥砺前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