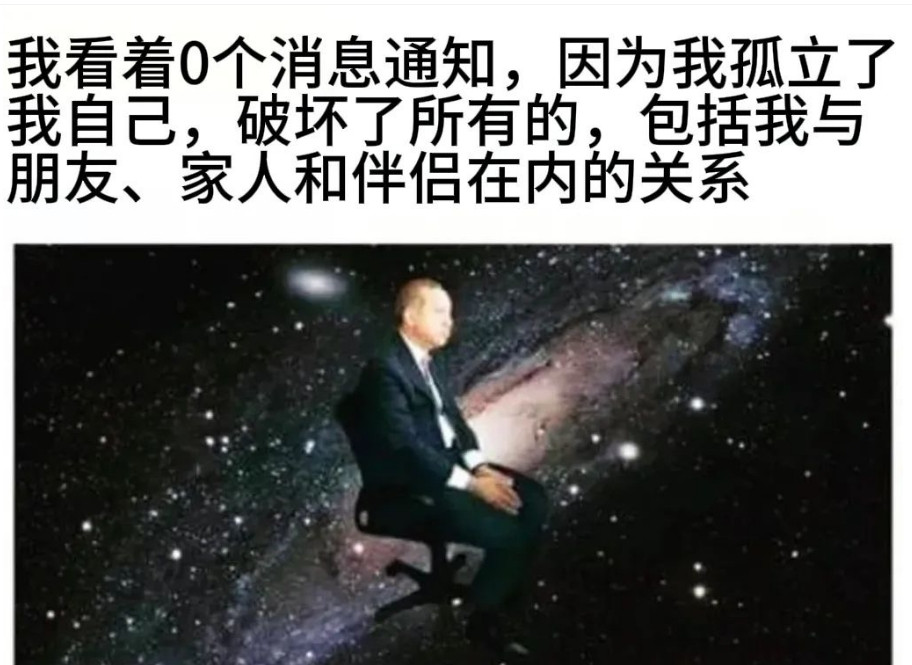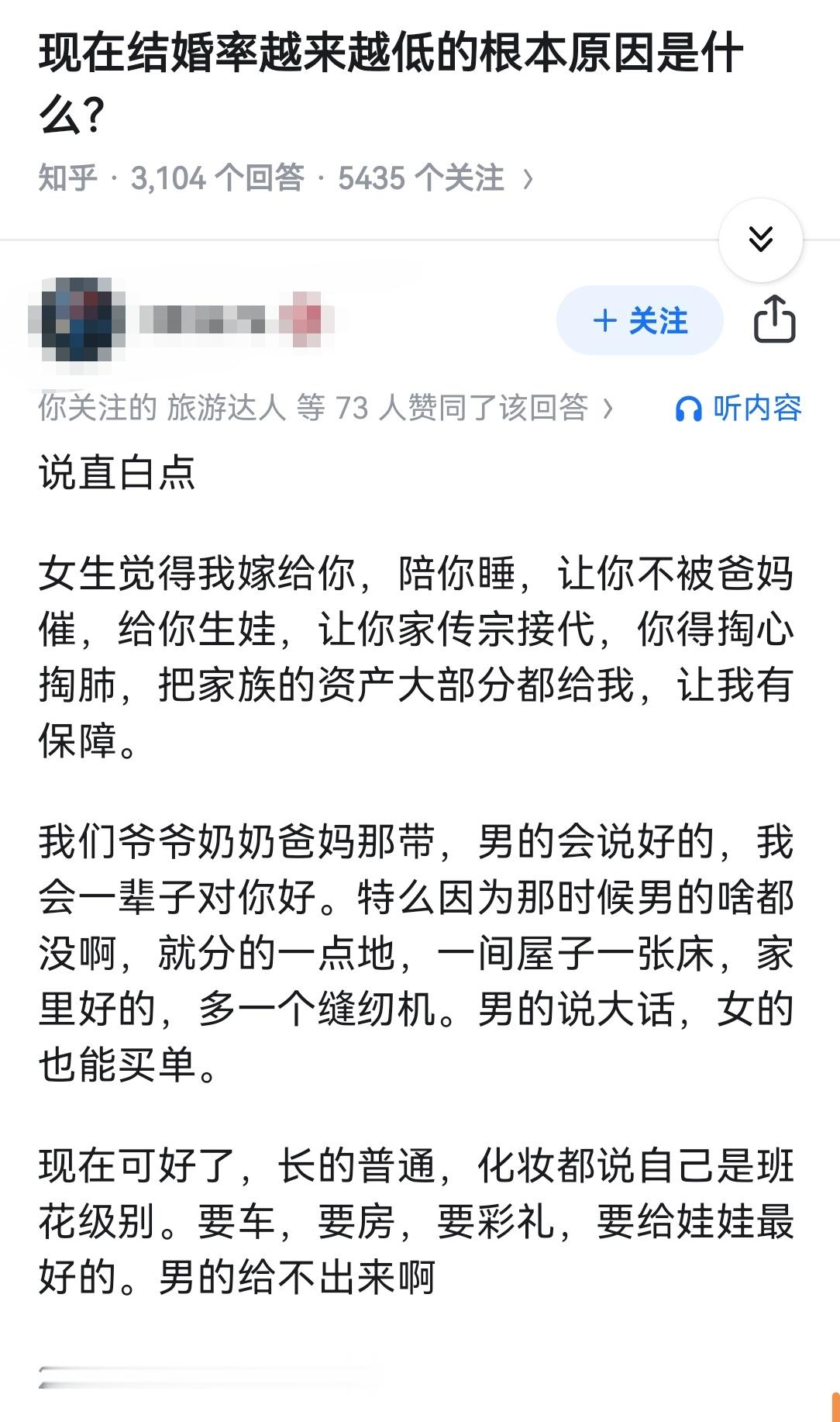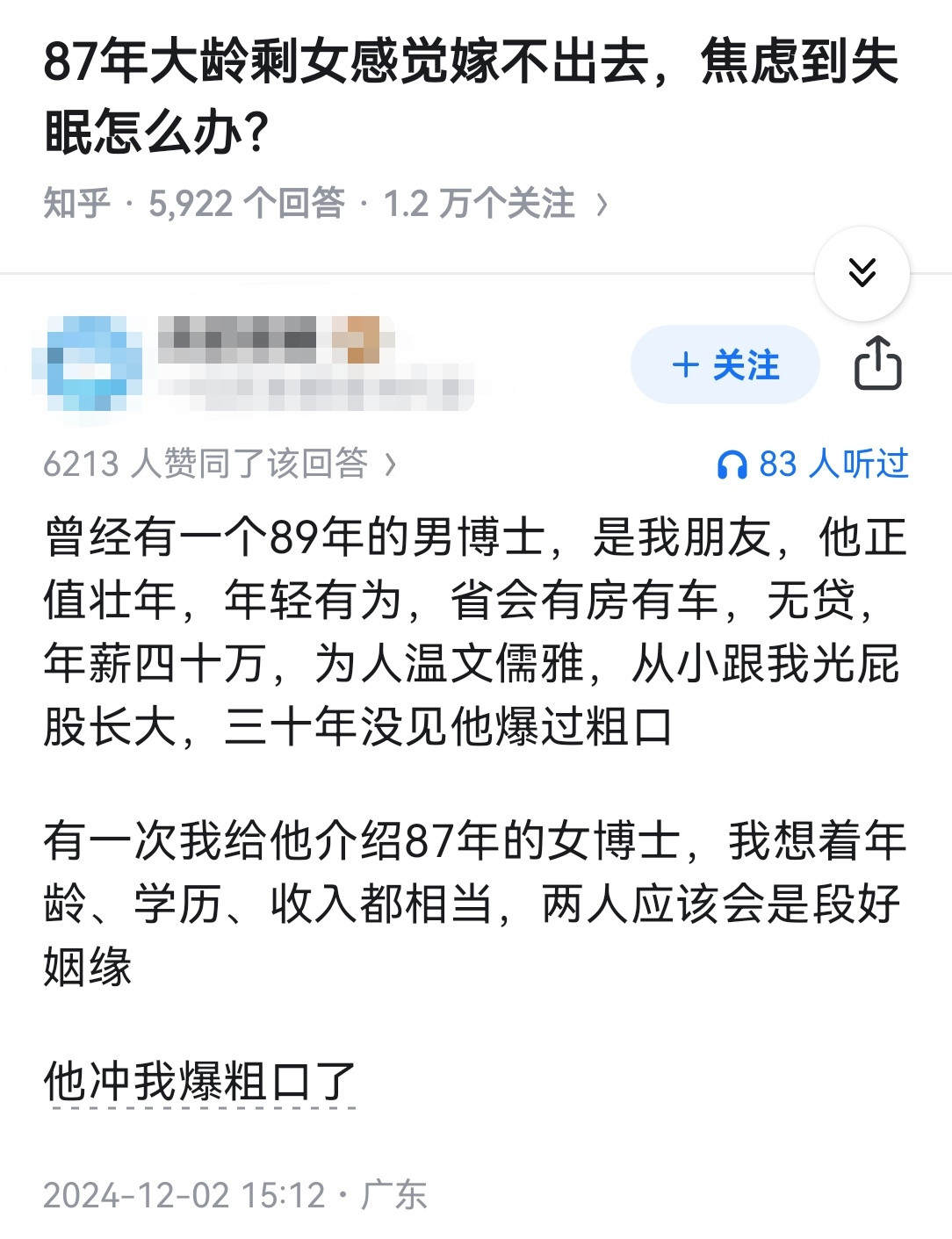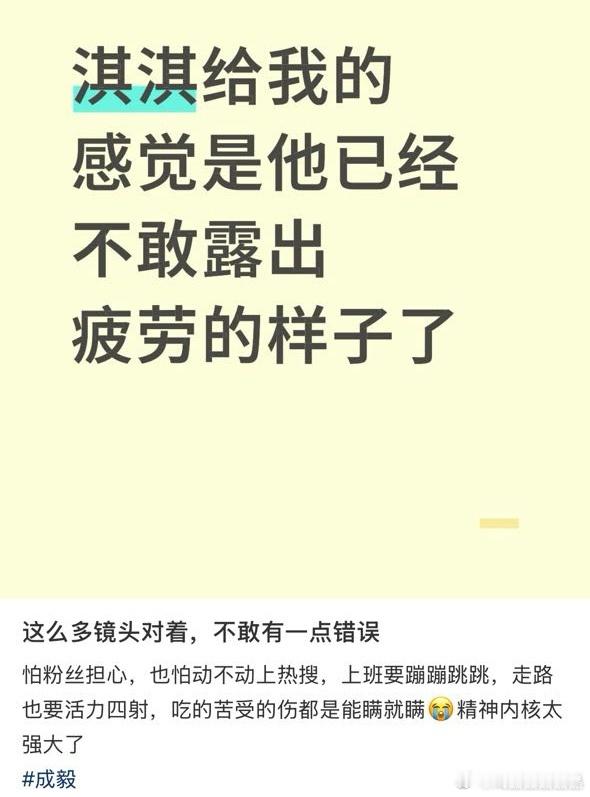我爸和我二叔关系不好,常年不说话,就连我出嫁,我爸都没有打算让二叔来,就在我出嫁的前一天,邻居给我捎信儿说二叔二婶在村口等我,我有些紧张,不知道他们叫我有什么事。 我爸和二叔的矛盾,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当年爷爷去世,留下一间老房子和几亩地,兄弟俩为了分家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我爸觉得自己是长子,理应多分一些;二叔却认为自己常年照顾爷爷,付出更多,不该少分。 明天就要出嫁了。 红漆木箱的锁扣被我摩挲得发亮,箱子里是妈连夜缝的红被褥,针脚密得能数出个数。 爸蹲在堂屋门槛上抽烟,烟灰掉在青布裤腿上,他也没拍。 “你二叔那边,不用叫了。”他突然开口,声音闷得像堵着团棉花。 我捏着箱角的手紧了紧,没应声。 邻居张婶突然掀帘进来,喘着气说:“妮儿,你二叔二婶在村口老槐树下等你呢。” 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他们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吗?还是……有别的事? 我攥着衣角往村口走,路上的石子硌得鞋底发慌。 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二叔背着手站在树底下,头发白了大半,风一吹,飘得像团乱麻。 二婶挨着他,手里攥着个蓝布包,指节都发白了。 “妮儿。”二叔先开的口,声音比平时哑。 我嗯了一声,脚指头在鞋里蜷成一团。 二婶把布包往我怀里塞:“明天你出门,我们就不去送了,你爸……怕是还在气头上。” 布包沉甸甸的,棱角硌着胳膊。 “这里面是啥?”我忍不住问。 二叔蹲下去,捡起块小石子在地上划拉:“二十多年前你爷爷走,留下间老房子几亩地,我跟你爸为这个吵翻了。” 老房子的木门槛被踩出两道浅沟,一道是爸年轻时挑水踩的,一道是二叔背着爷爷去卫生院磨的。 “你爸觉得他是老大该多分,我觉得我守着老人日子苦该多分,话赶话就动了手。”二叔的指甲掐进掌心,“后来才知道,你爸是怕我一个人还不清给你奶奶抓药的债,想多分地替我扛着,我当时光顾着委屈,没听他把话说完。” 二婶抹了把脸:“这包是你爷爷留下的老银镯,还有我们攒的五千块钱,给你当嫁妆。” 我打开布包,银镯上的花纹磨得发亮,内侧刻着个“安”字——是爷爷的名字。 眼泪啪嗒掉在银镯上,溅开一小朵水花。 “叔,婶,这钱我不能要。”我把包往回推。 二叔按住我的手,手背上全是裂口,沾着泥:“妮儿,你爸和我是亲兄弟,骨头连着筋呢。当年是我们俩糊涂,让你夹在中间难做人。” 他站起身,拍了拍我肩膀:“明天你好好出门,别惦记我们。” 我看着他们往村西头走,二叔的背比上次见驼了些,二婶扶着他,俩人的影子在地上挨得紧紧的。 回到家,我把银镯戴在手腕上。 妈进来看见,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爷当年总说,这镯子要给家里第一个出嫁的姑娘。” 爸不知啥时候站在门口,盯着我手腕上的银镯,烟锅子在门框上磕了磕,火星子溅在地上。 “明天……让你二叔二婶也来吃杯喜酒。”他说完,转身进了里屋,背影比平时直溜了些。 第二天出嫁,迎亲的车快到门口时,我看见二叔二婶站在人群后面,二叔手里攥着个红包,二婶偷偷抹眼泪。 爸走过去,往二叔手里塞了根烟,打火机“咔嗒”一响,火苗舔着烟卷,也舔暖了二十多年的冰。 现在每次回娘家,我都把银镯戴着。 有时候爸和二叔坐在院子里下棋,吵吵嚷嚷的,跟二十多年前一样,只是这次,没人再提分家的事。 亲情这东西,就像老槐树的根,看着地面上的枝桠各长各的,地底下的根须,早就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悄悄缠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