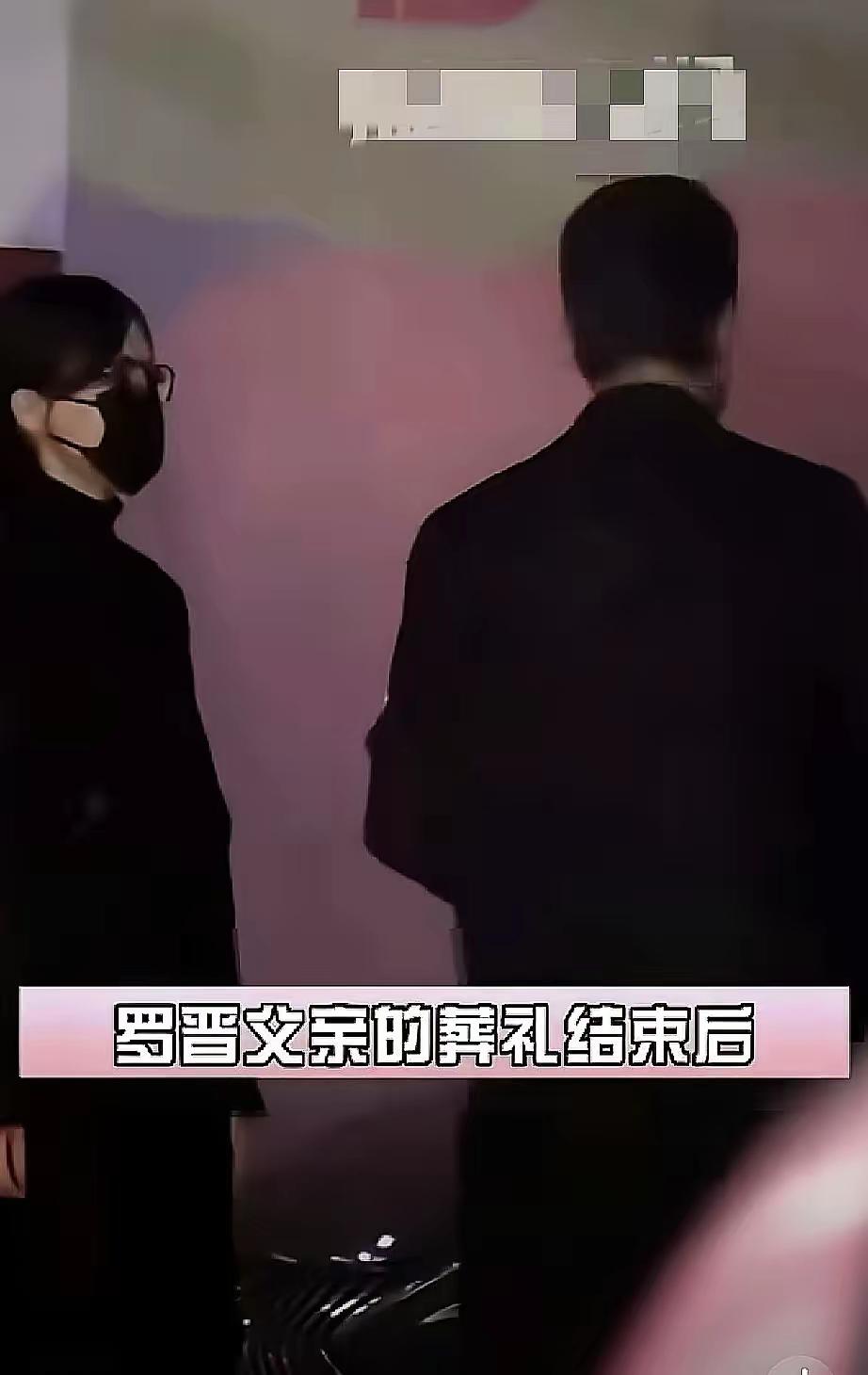演员咏梅说:“我爸爸是大学生,我妈妈是农村出来的,我妈她永远忽视我,比如说一个蛋糕,她永远会切大块的给我哥哥,我的那块就小,我爸爸就很讨厌她这一点,经常会忍不住发脾气,说两个都是咱们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厚此薄彼?因为类似这种的事,他们经常会有观念上特别强烈的冲突,但我妈妈依然我行我素,当两人之间的这种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再也没办法凑合下去了,所以很早就离婚了。” 那种被至亲之人选择性忽视的痛,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童年最柔软的地方,不致命,却时时发作。咏梅记得,她曾鼓起勇气想靠近母亲,换来的总是一句“没时间”。可转眼,母亲就能陪哥哥说笑半天。这种差别对待,让她早早学会了在角落里安静待着,仿佛自己真是这个家的“配角”。 母亲那份源于传统观念的偏执,无形中把家庭撕裂成两半。父亲看不惯,他读过书,心里装着平等与尊重,可他的愤怒改变不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离婚,成了两个世界的人最终的选择。咏梅跟着父亲生活,他成了她暗淡童年里唯一的光。父亲告诉她,人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让欲望牵着鼻子走,自尊自爱才是立身之本。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埋进她心里。 父亲虽然因为时代原因,从畜牧业大学生变成了电工,但他没有消沉,反而凭借努力成了工程师。他的精神世界是丰盈的,这种纯粹和坚持,深刻塑造了咏梅的价值观和审美。可母亲造成的创伤并未消散,那种长期被忽视的感觉,让她变得敏感、自卑,甚至影响到她成年后的重大选择——因为惧怕重复原生家庭的模式,她和丈夫栾树选择了丁克。 2013年,母亲离世。一年后,父亲也走了。双亲的相继离去,让咏梅经历了山崩地裂的痛苦。生死这道坎,逼着她去反思、去回溯。她必须直面那个曾经让她受伤的母亲,也必须重新理解父亲给予她的力量。这个过程充满挣扎,但最终,她完成了与原生家庭的和解,这是一种放下,也是对自己的救赎。 如今的咏梅,身价不菲却选择租房居住,没有儿女,生活依然过得惬意丰足。她的人生轨迹,仿佛是对过去的一种超越。童年那个分不到大块蛋糕的小女孩,最终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生命的丰盛。这种蜕变,比任何戏剧都更有力量。它告诉我们,原生家庭的伤或许深刻,但决定我们最终模样的,永远是自己选择如何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