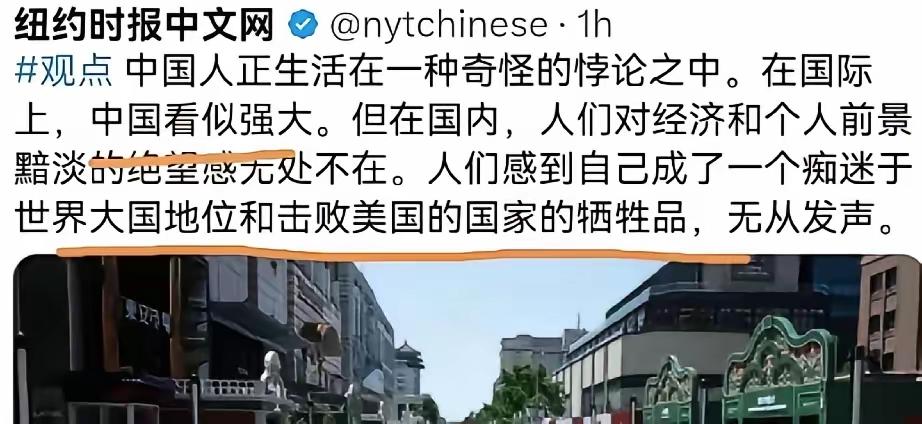纽约时报称,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悖论中,在国际上中国看似强大,但在国内,人们对经济和个人前景暗淡的绝望感无处不在,人们感到自己成了一个痴迷于世界大国地位和击败美国的国家牺牲品,无从发声。老实说,这一段话表面上看似乎还挺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完全是舆论战的拙劣手段。 在大洋彼岸的媒体笔下,当下的中国被贴上了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标签——“奇怪的悖论”。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描绘了这样一副图景: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看起来肌肉发达,但把视线转回国内,却是满地灰暗,民众仿佛成了大国博弈棋局里的“牺牲品”,在无声的绝望中挣扎。 这种把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强行对立的逻辑,乍一听似乎精准切中了某些情绪痛点,但只要我们稍微把镜头拉近,贴着中国社会的地面走一走,就会发现这所谓的“深刻洞察”,不过是又一次戴着有色眼镜的认知拼凑。 这种“外强中干”的叙事模板其实并不新鲜。 回望几十年的国际舆论场,类似的剧本换个主角演了好几轮:上世纪80年代,日本被描述成“没有灵魂的富裕机器”;90年代,东南亚的危机被归咎于“价值观缺陷”。 如今,轮到中国接棒这个“矛盾体”的角色。这种话术的核心伎俩,就像是只盯着半杯水的空当处大做文章,刻意无视那个正在不断注入活水的过程。 现实的数据流淌出来的,并不是媒体口中那股浓得化不开的绝望。麦肯锡发布的2023年中国消费者报告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78%。 这份数据对应的是受访者对未来五年个人收入增长的乐观占比,而这一比例甚至比上一年高出了 5 个百分点。 而在宏观债务焦虑的喧嚣背后,西南财经大学的调研却展示了另一条曲线——中国家庭的债务压力从2021年开始实际上处于缓解通道,负债结构正在趋于健康。 这些实打实的微观体感,显然被那个宏大的“悲情滤镜”给过滤掉了。 把视线投射到具体的个体身上,“国家强大是个人牺牲代价”这个论断更是显得苍白无力。 在山西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农产品主播王大姐把家乡的小米装进了发往迪拜的货柜,对于她来说,那条曾经只存在于新闻联播里的“一带一路”,如今变成了手机直播间里叮当作响的订单;在成都高新区,90后的创业者李哲正带着团队攻克AI医疗影像算法,他们的技术精度已经反超了欧美竞品,服务触角伸向了东南亚的多家医院。 对于这些人而言,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张,不是压在身上的大山,而是脚下的一块跳板。 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是“大国竞争的牺牲品”,相反,国家护照含金量的提升、出海路径的畅通,让每个走出去的中国人腰杆更硬,这种安全感和机遇感是无法用“牺牲”来定义的。 当然,我们也无需回避当下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压力。年轻人忙着做项目、考公、搞副业,中年人在家庭与事业的夹缝中顶住重担。 但这叫奋斗的张力,不叫绝望。真正的绝望是死水一潭,而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里到处是解决问题的尝试。 西方观察家往往看不到中国基层治理的这种韧性:在浙江,“民生议事堂”能把菜市场的租金纠纷搬到台面上,商户、管理者坐下来面对面谈妥;在深圳,数十万年轻人通过“青年安居计划”在大城市有了落脚之地;这些自下而上的创新、为了美好生活而具体的奔波,才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底色。 说到底,不管是城市里不断延伸的地铁线、医保异地报销的便利,还是新疆光伏基地给千万家庭送去的清洁电能,这些变化的受益者终究是每一个普通人。 把这种发展与民众福祉对立起来,把正常的社会压力渲染成“无处发声的窒息”,本质上是因为某些观察者依然沉浸在非黑即白的二元认知框架里出不来。 他们理解不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在保持庞大社会稳定的同时,还能进行如此深刻的自我革新。 或许真正的悖论不在中国,而在于那些制造话题的媒体本身:他们一边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实力的客观跃升,一边又顽固地试图论证这种力量缺乏根基。 在信息如此通透的今天,无视亿万中国人为了好日子热气腾腾的努力,而强行编写一套“悲惨世界”的剧本,这才是最尴尬的认知错位。 信源: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09元2025年10月20日 10:06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