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作家周扬回乡探亲,顺道去看前妻吴淑媛墓,谁料,半路突然大雨倾盆,顿感慌张,立马转身离开,不敢去坟前。 益阳板桥周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族,祖上能追到三国东吴大将周瑜。 1908年,这个家族出了位后来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旁人都喊他“二少爷”。 周扬在信义中学读书时,房东是位叫姚仁涛的私塾先生,先生有个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年纪和周扬相仿,模样长得标致。 姚先生觉得两人般配,就跟周扬的母亲提了句:“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 后来周扬邀着同学去吴公馆看亲,进门就见吴淑媛在绣花,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肩头,周扬一看就满意了,笑眯眯地回了家。 吴淑媛乳名“娇娇”,身边人都叫她“娇小姐”,她对周扬也是一见倾心,16岁那年,两人顺理成章成了亲。 刚结婚那阵,小两口好得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用一只杯子一把壶。 周扬初中毕业去长沙读高中,后来又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吴淑媛始终跟着他,里里外外打理得妥当。 周扬在上海的生活全靠吴淑媛撑着,她把外婆陪嫁的一大包金首饰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就取一件换钱。 这份信任和付出,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有回吴淑媛在周扬的西装口袋里翻到异性写的信,她没闹没问,坦然地把信还给了丈夫。 1928年,益阳有两位女共产党员为了避祸跑到上海找周扬帮忙,周扬说要和她们假扮夫妻、兄妹同住二十多天。 跟吴淑媛商量时,她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眼里全是对丈夫的支持。 变故发生在1934年深秋,那时吴淑媛已经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把她和两个孩子送回益阳待产。 往常这种时候,周扬总会等孩子生下来再回上海,可这次他没等,临走时只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信笺纸,嘱咐她“常给我写信”。 吴淑媛哪能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诀,往后两人只能靠信笺联系。 周扬回上海后像换了个人,脱下常穿的西装,换上白绸长衫,戴起白色礼帽,身边多了个复旦大学的女学生苏灵扬。 远在益阳的吴淑媛对此一无所知,1935年春天她收到周扬的信,说“暑假就回益阳”,她立马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动手给丈夫做他爱吃的甘草梅。 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又甜又脆,装在粉彩瓷坛里放在摆柜上,孩子们再馋也知道是给爹爹留的,谁都没动。 可暑假到了,周扬没回来,那坛梅子就一直放在那儿。 到了第二年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做了第二坛,周扬又来信说暑假回,结果还是落空,这年他去了延安。 即便如此,吴淑媛在1938年收到周扬寄来的《安娜·卡列尼娜》译著时,她一边读一边又做了第四坛甘草梅。 周扬的母亲看出不对劲,写信质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忘了?” 周扬回信说自己在延安肤施当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这话让吴淑媛的希望又撑了几年。 1941年6月,长子周艾若从寄宿学校回家,发现周家大屋气氛不对,乡邻和家人都在传一张桂林办的《救亡日报》。 报上周扬给郭沫若的信末尾写着“苏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这句话像炸雷一样劈在吴淑媛心上。 七年的等待,那些信笺、那些甘草梅,她苦心搭建的爱情童话,瞬间碎得彻底。 从那以后,吴淑媛就病了,先是脖子上长起一串串淋巴,很快就肿得像荔枝那么大,接着全身浮肿,躺在床上起不来。 她肚子疼得厉害也不吭声,就用被子死死摁着,最后把被子都摁破了一块。 病危时她想吃粉皮、新鲜包谷,还想吃北方的大梨,等弟弟好不容易托人买到大梨,她已经咽不下了。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那丛多年没长枝叶的牡丹突然开得茂盛,老人们都说这是异兆。 当年深秋,35岁的吴淑媛就走了,葬在周家后山,离老屋就百米远,坟头长满青草灌木,连块墓碑都没有。 1980年春天,周扬回到了益阳,先看了老屋,接着在当地人陪同下去看吴淑媛的墓。 墓地不远,走几分钟就到,已经走了一半路程,再几步就到坟前了,偏偏下起雨来。 随行人说:“下雨路滑,别去了。”周扬听了,转身就往回走。 晚年的周扬曾抱着儿子周艾若痛哭:“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可这份愧疚,终究没敢在那座无碑坟前说出口。 吴淑媛出身官宦却没半分娇气,把丈夫当成天,用嫁妆养家用,用信任包容一切。 她的七年等待,是用一坛坛甘草梅、一封封没寄出的信主动维系希望,可她把人生全部系在男人身上,一旦男人变心,她的世界就塌了。 周扬在文艺领域有自己的追求,可在感情里他太懦弱,临盆时不告而别,用谎言敷衍家人,直到老去都没勇气面对那座坟。 他的愧疚,比假深情更让人唏嘘。 【评论区聊聊】你觉得一段感情里,坚守与责任究竟该放在什么位置? (信源:周扬的晚年忏悔——人民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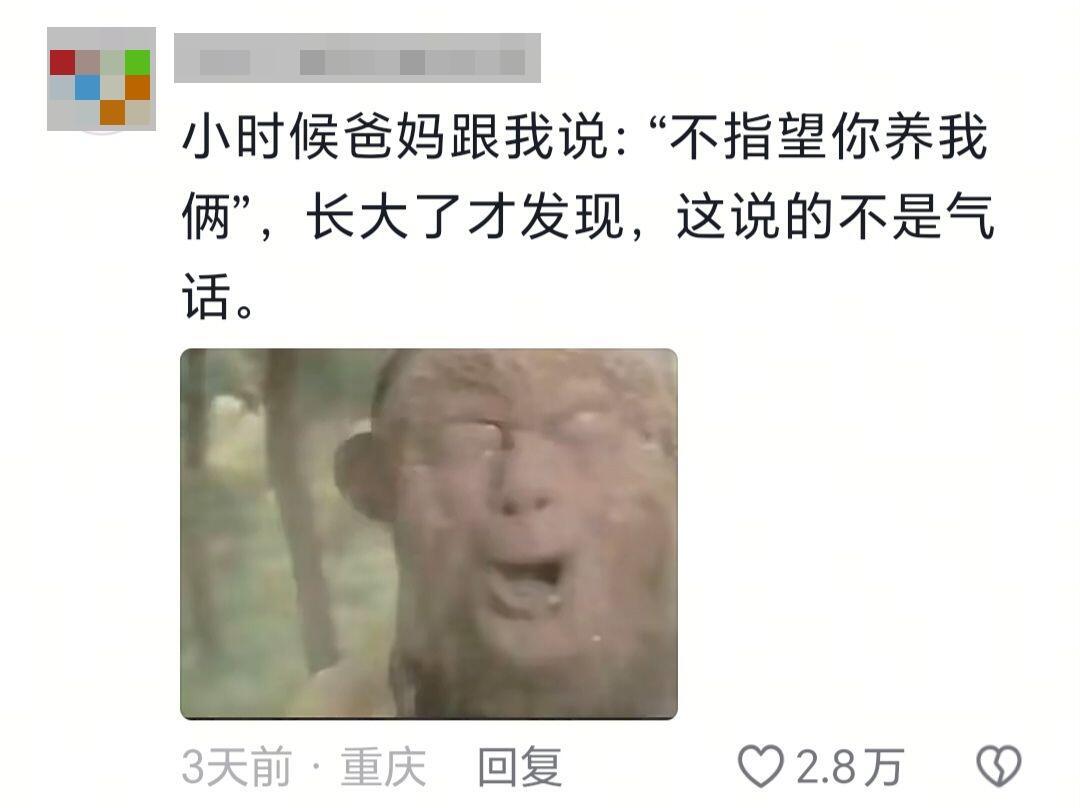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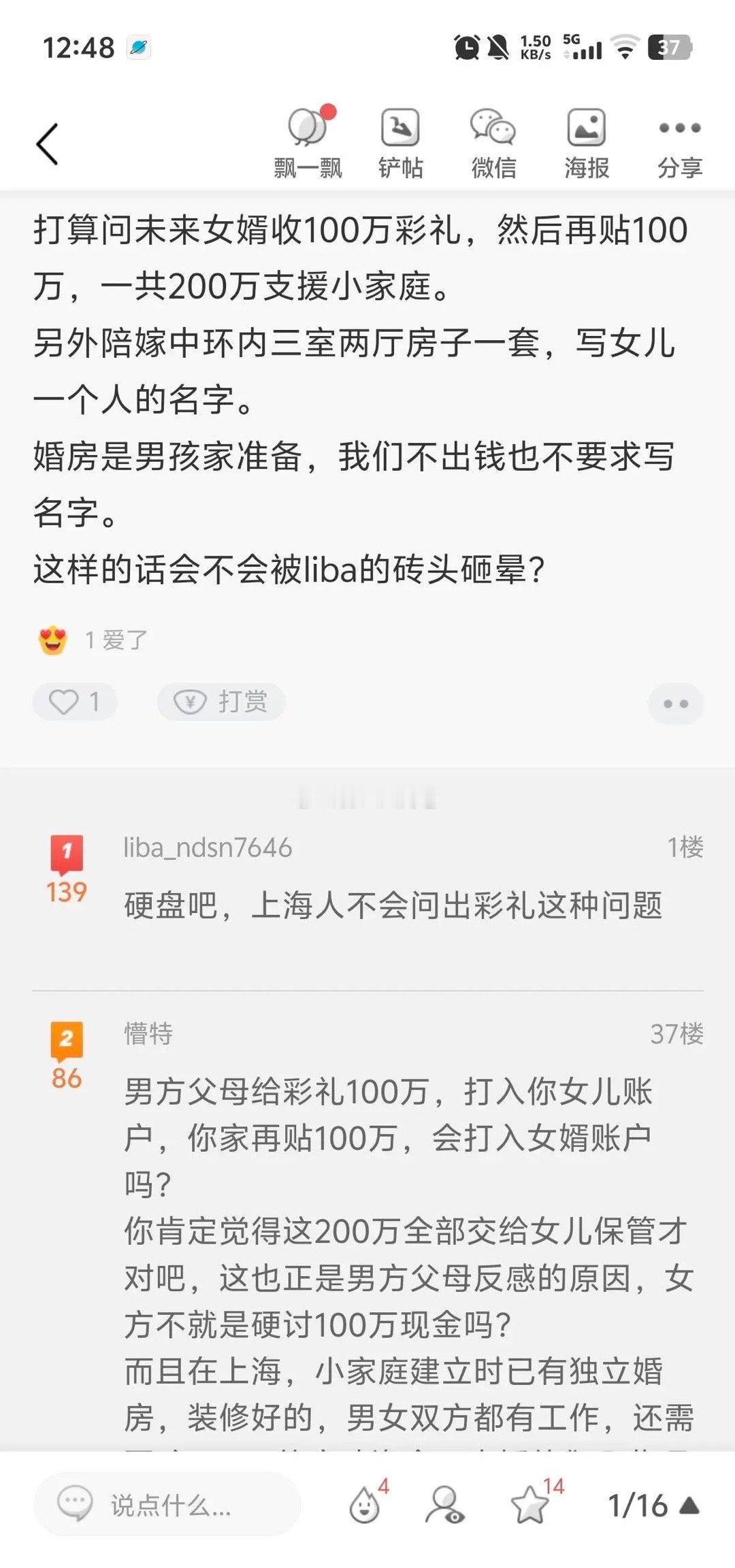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