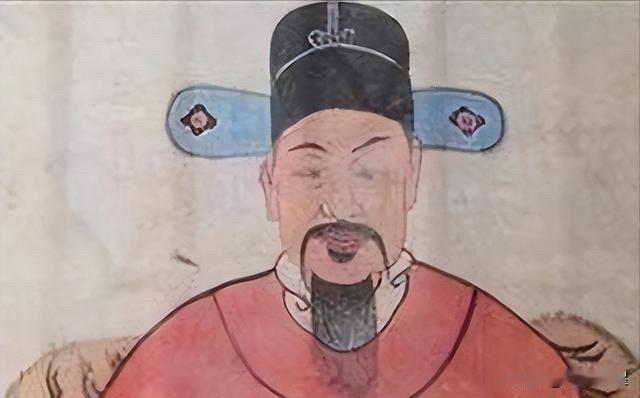毛主席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刘少奇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两句话都提到了人民。可总觉得又不太一样。 很多墙上,两句话并排挂着:左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右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看上去挺和气,细一琢磨,味道并不一样。 “全心全意”这四个字,早就写进章程里。 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要同工人、农民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并巩固广泛联系;每个党员要懂得,党的利益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 后来历次党代会又一再把这句话写进党章,这条线一直被拧得很紧。 再往前看,1939年2月,毛主席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谈到孔子的“知”和“仁勇”,指出那种不根于客观事实的理论,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所谓“仁”,只仁在统治者头上,对大众不仁;所谓“勇”,只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住封建制度,不勇于为人民服务。老的“仁勇”,就这样被换了标准。 同年,知识分子问题被单拎出来。 1939年12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知识分子应该“为工农服务”“为群众服务”,并以能否为群众服务为标准,区分不同知识分子,也作为吸收入党的条件之一。 “为人民服务”在这时起了筛子的作用。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讲话里那句“作家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把文艺也拉进这条线里;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只要加以改造、加进新内容,就可以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1943年10月写《论合作社》时,又明确提出,为群众利益着想,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1944年夏,陕北安塞县石峡峪山上,中央办公厅抽调会烧木炭的人去打窑,中央警卫团同中央社会部组成烧炭生产队。 副队长叫张思德,四川仪陇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参加过长征,多次负伤。1938年在中央军委警卫营当通讯班长,1942年11月任中央警卫团一连通讯班长,后来调到延安枣园,担任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 到石峡峪烧炭,他干活总往前冲。那年雨水多,窑顶被雨泡软。 1944年9月5日,炭窑突然塌下,他正弯腰干活,被压在里面。 战友把人挖出来时,他已经牺牲,年仅二十九岁。那张和战友一起烧炭的照片里,他站在左侧,是生前唯一留下的影像,由新华社保存。 三天后,1944年9月8日,中央警备团为他开追悼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谈生死时,他引用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 谈批评时说,因为是为人民服务,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谈队伍时要求干部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同年10月4日,在中央印刷厂礼堂,他对《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人员讲:“为人民服务,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1944年冬天,他又给党内刊物《书包简讯》题词:“书包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这里把“党”和“人民”的关系连在一起:真为党,就是为人民。 1945年,这条线继续往下走。 5月,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月,又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1953年,《为人民服务》正式成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张思德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一起留在书里。 此后历次党代会都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变了,社会结构复杂,利益关系更细,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还是那几个字。 现实生活里,不少人是通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来感受这种关系:社保、学校、医院、公共服务,人人往公共的池子里添一瓢,也从里面舀一瓢。 两句话摆在一起,各管一头。 毛主席那句,是给执政党定家法:知识分子能不能为工农服务,文艺肯不肯为劳动人民说话,干部敢不敢听批评、会不会关心战士,烈士的死算不算“重于泰山”,都要按“为人民服务”来对照。 刘少奇那句,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既帮别人,也不把自己撂在外头。 墙上的字不会说话,人得自己对号入座,每一代人都得算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