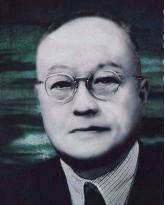1975年,蒋介石快不行了,弥留之际,嘴里轻轻喊出一个名字:“阿凤”,身边人面面相觑,谁啊?宋美龄也不懂。 1981 年美国纽约公寓,陈洁如临终前摩挲着旧合影。 照片里 15 岁的她笑靥如花,指尖突然顿住 —— 六年前那通来自台湾的电话,又在耳边响起。 窗外飘着雪,她轻声呢喃 “阿凤…… 他终究是记得的”,眼里满是释然与遗憾。 陈洁如 1905 年生于上海,父亲是绸缎商人,家境优渥。 她从小读私塾,学英文,还跟着母亲学绣花,是邻里眼中的 “大家闺秀”。 14 岁时,身边已有不少追求者,可她都没动心,觉得 “少了点什么”。 直到 1919 年遇见蒋介石,这个比她大 10 岁的军官,让她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 起初陈洁如对蒋介石保持距离,觉得他 “经历太复杂”。 可蒋介石每天雷打不动来陈家,雨天撑伞送她上学,雪天帮她暖手炉。 还会讲自己的 “抱负”,说 “想让中国好起来”,眼神格外真诚。 陈洁如渐渐被打动,觉得 “他虽然有过婚姻,却也是个有担当的人”。 1920 年结婚时,陈洁如特意绣了一对枕套,上面绣着 “永结同心”。 婚后她收起小姐脾气,学着给蒋介石做饭、缝衣服,把小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蒋介石晚归时,她总会留一盏灯,温着饭菜,从不抱怨他 “不顾家”。 那段日子,她常听蒋介石喊 “阿凤”,觉得 “这辈子就这样安稳过下去也挺好”。 1923 年随蒋介石去广州,住的房子漏雨,她自己动手补屋顶。 蒋介石没钱买新衣服,她就把自己的首饰当了,给他做新军装。 有次蒋介石生病,她衣不解带照顾了三天三夜,自己瘦了好几斤。 蒋介石醒后拉着她的手喊 “阿凤,委屈你了”,她当时觉得再苦也值。 1927 年蒋介石提出让她去美国留学,陈洁如心里满是不安。 她追问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蒋介石却避而不谈,只说 “为了我们的将来”。 出发前一晚,她抱着蒋介石哭,说 “我等你接我回来”,把绣着 “同心” 的枕套塞给他。 她没料到,这一别,“阿凤” 这个称呼,竟成了往后几十年的念想。 到美国后,看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报纸,陈洁如当场昏了过去。 醒来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看着枕套上的 “同心” 二字哭到脱水。 她想过回国质问,可又觉得 “他既然做了选择,再问也没用”。 那段时间,她夜夜梦到蒋介石喊 “阿凤”,醒来却只剩空荡荡的房间。 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她决定 “为自己活一次”,重新走进学校读书。 1930 年毕业后,陈洁如在美国找了份翻译的工作,生活渐渐稳定。 有人追求她,条件很好,也很真心,可她都拒绝了。 她说 “心里装着人,没法再接受别人”,其实是没放下那个喊她 “阿凤” 的人。 偶尔看到关于蒋介石的新闻,她会默默关掉,却又忍不住偷偷关注。 1949 年蒋介石去台湾,陈洁如在美国听到消息,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蒋介石偷偷给她送钱,她起初不肯收,觉得 “拿了钱,就成了他的附庸”。 可架不住送钱的人反复劝说,最终还是收了,却把钱存起来,没舍得花。 她想,这或许是那个喊 “阿凤” 的人,唯一能给她的补偿了。 1971 年回台湾,她特意去了当年和蒋介石住过的地方。 房子早已换了主人,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想起他喊 “阿凤” 的模样。 有人劝她 “见蒋介石一面”,她却摇头说 “见了又能怎样,徒增烦恼”。 那时她还不知道,四年后,会从电话里听到那个让她泪目的消息。 1975 年 4 月,台湾的朋友突然给陈洁如打来电话,声音很轻。 说 “蒋介石先生走了,弥留之际,一直喊着‘阿凤’……”电话那头还在说什么,陈洁如已经听不清了,手里的杯子 “哐当” 掉在地上。 她走到窗边,看着远方,突然就哭了,几十年的委屈好像都有了着落。 那天下午,她把压在箱底的旧合影拿出来,用布擦了又擦。 照片里的蒋介石笑容灿烂,好像下一秒就会喊出 “阿凤”。 有人问她 “恨不恨”,她叹口气说 “恨过,可也爱过,都过去了”。 从那天起,她心里的执念,好像终于慢慢散了。 1981 年病重时,她把旧合影和枕套放在枕边,说 “要带着这些走”。 临终前,她让朋友把自己的骨灰送回上海,“葬在父母身边”,没提蒋介石。 她的墓碑上只刻着 “陈洁如女士之墓”,简单干净,像她后来的人生。 如今,上海的陈洁如墓前偶尔会有游客驻足,听导游讲 “阿凤” 的故事。 有人为她 “抱不平”,也有人佩服她 “活得清醒”。 那张旧合影藏在博物馆里,见证着一段被权力拆散的感情。 信源:人民网《民国往事:蒋介石与陈洁如的七年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