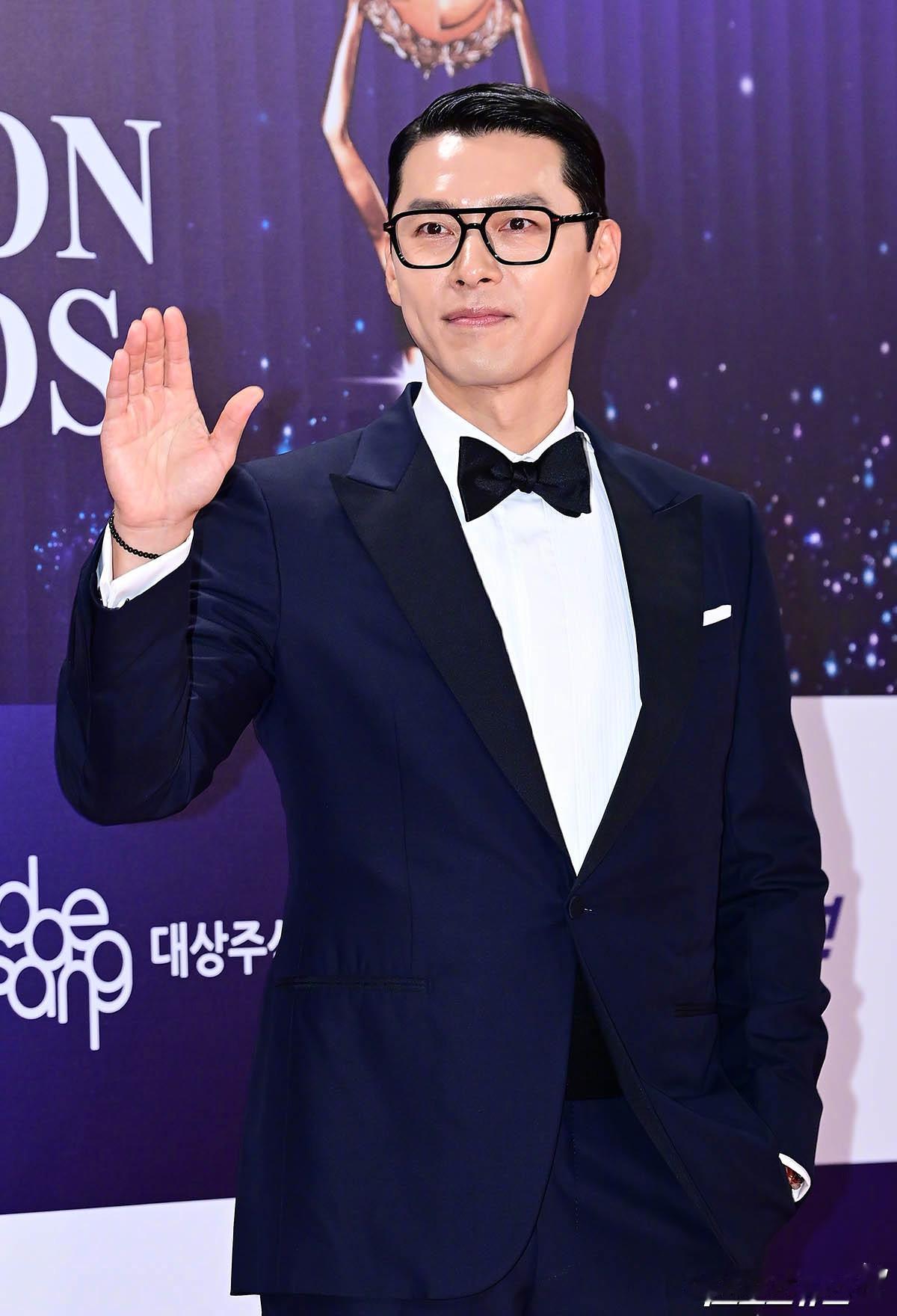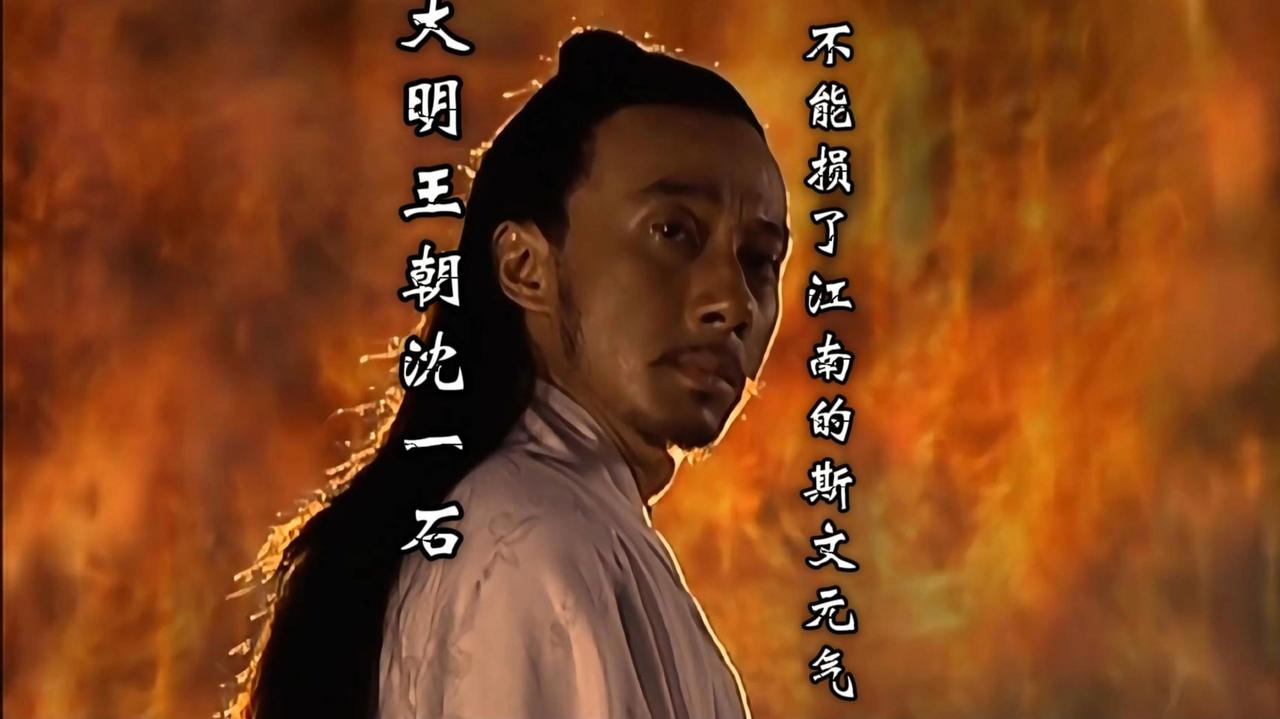大宦官鱼朝恩屡屡为难郭子仪,郭子仪总是忍让。时间一长,鱼朝恩反而不好意思了,一次宴请郭子仪,席间痛哭流涕,说再也不会与郭子仪为敌。 但朝堂的风浪从未真正平息。就在鱼朝恩心中惴惴不安的时候,边报传来急讯——吐蕃大军已越陇山,攻陷长安,代宗李豫被迫逃往陕州。此时已是公元763年岁末,郭子仪正在河中府,奉命整军防备再战。 这时的长安,几无防守之力。唐军主力尚未回防,中央百官逃散。吐蕃趁势而入,宣称“迎立代宗”,但民心依旧向着大唐。代宗在陕州仓促召见郭子仪,授以全权。郭子仪未做迟疑,只带了数名心腹随行进宫述职。他面色如常,并未因兵权交出、政敌环伺而有所抱怨。 代宗亲自出迎,将郭子仪安置于近侍厅中,又赐以金帛厚礼。郭子仪婉拒,只道:“臣老矣,愿赴河中招募义勇,不扰民资,不动国库。” 回到河中府,郭子仪昼夜兼程,走访乡绅地主,劝百姓共筑防线。他以身作则,主动削减军中开支,派兵修渠疏水、供民耕种,河中上下士气大振。消息传至陕州,代宗大喜,密令鱼朝恩遣马百匹、金器数箱送往郭府。 然而河中军情未稳,吐蕃未退。郭子仪不发一兵,反命士卒备酒犒赏乡兵,又将朝廷赠马悉数分予百姓看护,表示:“谁守一日土城,便赠一骑。” 吐蕃见唐军未出营、百姓自发守城,心生疑忌,退兵至长安郊外不敢深入。郭子仪趁夜派人暗通回纥,说:“我愿调解你我旧盟,只请勿助贼。” 几日后,吐蕃军在无果中悄然北撤,长安得以复归。代宗闻报,封郭子仪为“中书令、尚书令”,赐号“太尉上柱国”。 这一战无一刀兵,却保大唐一座帝都,鱼朝恩表面称颂,实则羞愧交加。他本欲借吐蕃入侵,借机压制郭子仪声势,未料此番郭子仪再立奇功,自己却毫无作为。有人暗中进言:“郭公威望隆盛,百姓皆称‘再造大唐’,不可不防。”鱼朝恩未置一词。 转年,北地回纥复来议盟,请唐朝派使。鱼朝恩自荐出使,言之凿凿:“此等外夷,吾一纸令书便可制之。”代宗却当着百官面点名郭子仪:“朔方旧事,非子仪不可。” 鱼朝恩未得其志,愤而离朝数日。然天子之意已明,郭子仪复领旧职,统筹回纥、吐蕃边事,兼摄西北六道兵马。 这一年间,郭子仪多次调解边事,未开边疆一战,但安定西北五州之乱、息民怨者皆赖其调处。 而鱼朝恩在朝愈发骄横,不数月便强令代宗赐紫衣于其义子鱼令徽,招致众臣非议。宰相元载见时机已到,密奏代宗:“今社稷赖郭公而存,鱼氏弄权,恐伤根本。”代宗沉思良久,只回一句:“可备事。” 大历五年三月,寒食节宫中设宴,鱼朝恩酒后回内侍省,被亲信借口“护驾不周”,缢死于庭中。太监走告百官时,仅言“鱼公偶染旧疾”,但朝堂上下皆知真相,群臣相视一笑。 而此时的郭子仪,正在汾阳老宅陪子孙习射,不闻朝政,终生未再提及鱼朝恩。 这位历经开元、天宝、至德、大历四朝的名将,至卒时,仍被诸国称为“令公”,享年八十五,葬于七里岗,门无守兵,仅一座残碑书“唐太尉郭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