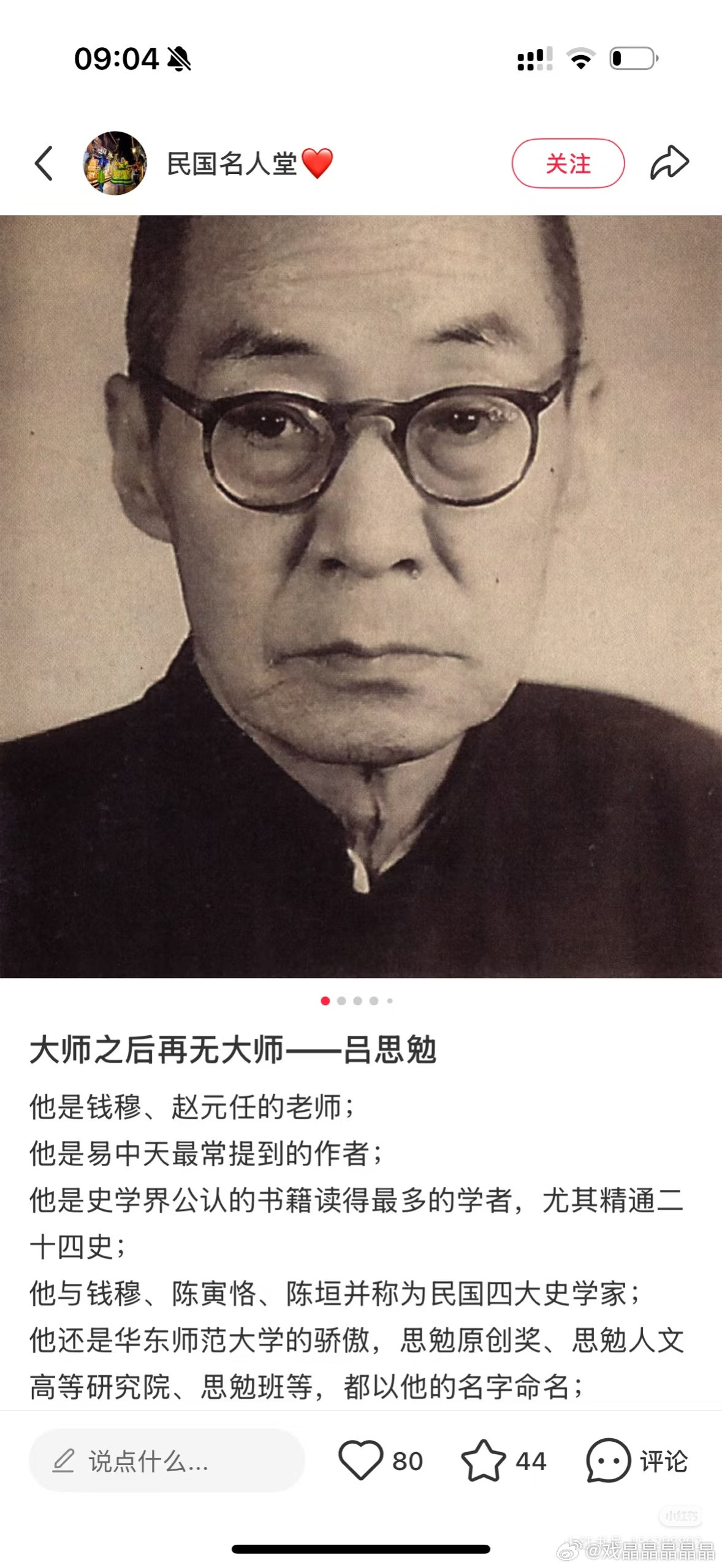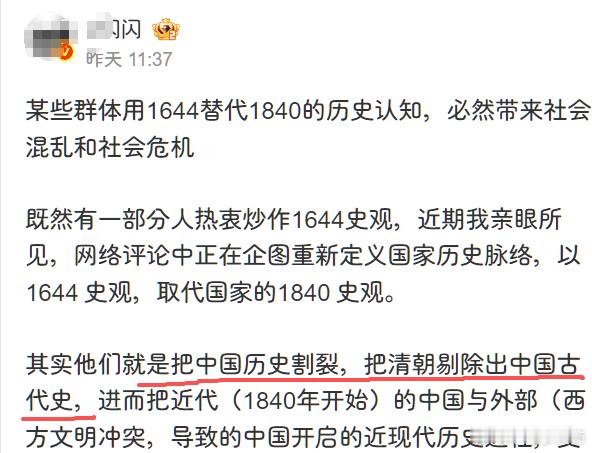1793年的一个秋日,北京紫禁城外,秋意正浓,桂香微漾。 八十三岁的乾隆帝坐在御花园的长椅上,披着缎绸金袍,神情难得露出一丝调皮。 他正端详着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金发少年——十二岁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你说,你真会讲咱们中国话?”乾隆饶有兴致地弯下腰,用汉语问。 小斯当东腼腆地点点头,鼓起勇气念出一串刚学的汉语:“陛下好,天子万岁。” 乾隆乐得大笑:“好,好,好!”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腰间解下一个锦绣荷包,递给小男孩,又抓起一颗槟榔,笑呵呵地塞进他嘴里,“赏你的。” 这一幕,旁人看着温馨,似乎预示着中英将迎来友好的开端。 可谁也没想到,这颗被乾隆塞进小男孩嘴里的槟榔,四十七年后,会在另一个地方被彻底咀嚼成战争的苦果。 那年,随英国使团一同来到中国的,还有那位焦头烂额的马戛尔尼。他不是没见过大场面,可这一次,他真慌了。 上头给的任务太离谱:求通商、要税惠、盼驻使、讨海岛——甚至要求清朝“割地”。这哪是外交?这是赤裸裸地敲门要地盘! 马戛尔尼在船上日日写日记,写着写着就叹气。 他知道中国皇帝高高在上,怎会轻易答应这些?更糟的是——他连能翻译这些“委婉要求”的合适人都找不到。 最后临时拉来一位名叫李自标的传教士,还指望一个英国小孩边学边翻当翻译……简直荒唐。 使团还没到,马戛尔尼就绞尽脑汁写了封信——又敬又显摆:国王多牛、礼物多贵、请求多合理。 结果到了清廷手里,这封信被改得面目全非:乔治三世变成了“远夷小国君主”,马戛尔尼成了“贡使”,表达亲善变成了“叩见乞恩”。 乾隆看了,自是龙颜大悦:“哈哈,又有外夷来朝贡啦,赏!” 英国人以为自己在谈贸易,中国人却以为他们来送钱认祖归宗。牛头不对马嘴,自然谈不成任何“平等”。 更荒唐的,还在后头。 英国人送来的“天体运行仪”,描述得天花乱坠,什么太阳绕地、星辰运转,清朝官员一看翻译,愣了:“这不就是个会动的‘大架子’?” 马上盖章定性:“钟表一枚。” 还有那个超大号凸透镜,英使说它能“引阳为火,焚金炼铁”,和珅见了,惊为天物。但第一反应不是震撼,而是实用主义发作: “阴天的时候,还怎么点烟?” 乾隆帝没有意识到,他用“天朝上国”的标准,打发了一个彼时正在全球扩张的帝国;而那个曾被他亲手喂槟榔的少年,数十年后站在下议院的讲台上,拍着桌子说: “我到过中国,要让他们开门,只能打!” 鸦片战争的投票以微弱优势通过,英国大炮开进了珠江,曾经被拒之门外的英使节,换了一种方式“叩见”中国。 这不仅是一场战役的序幕,也是两个帝国认知碰撞的残酷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