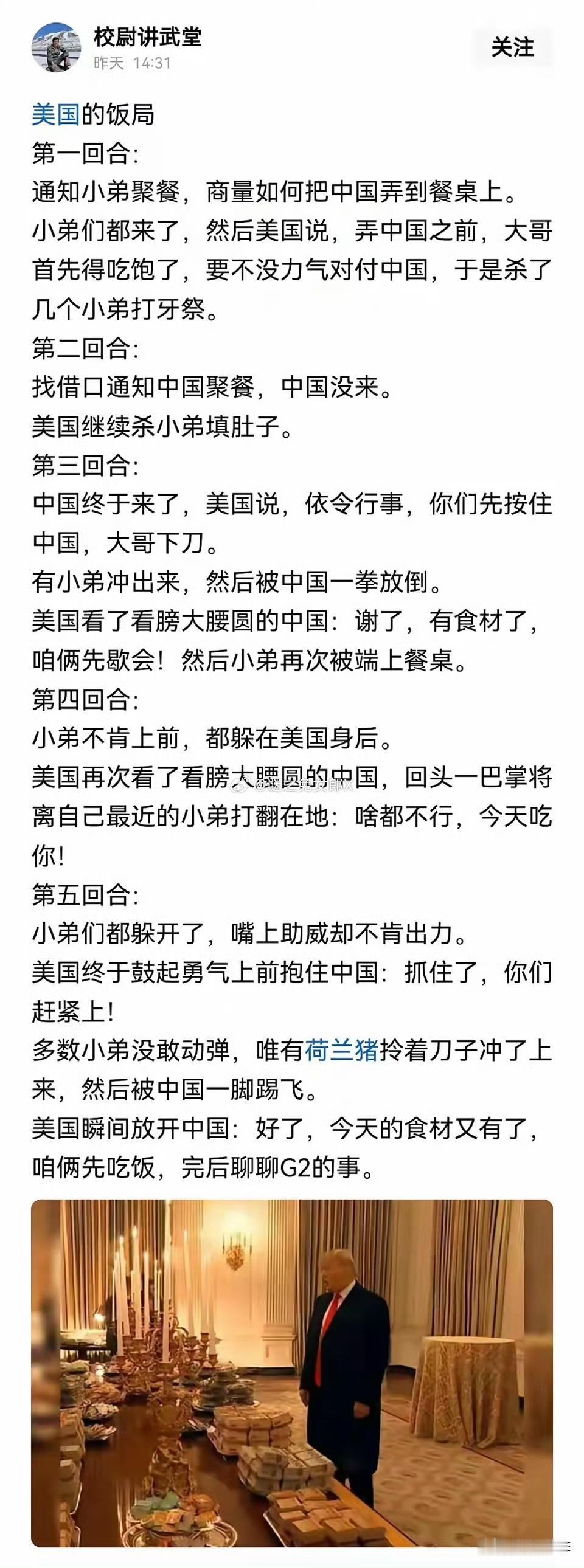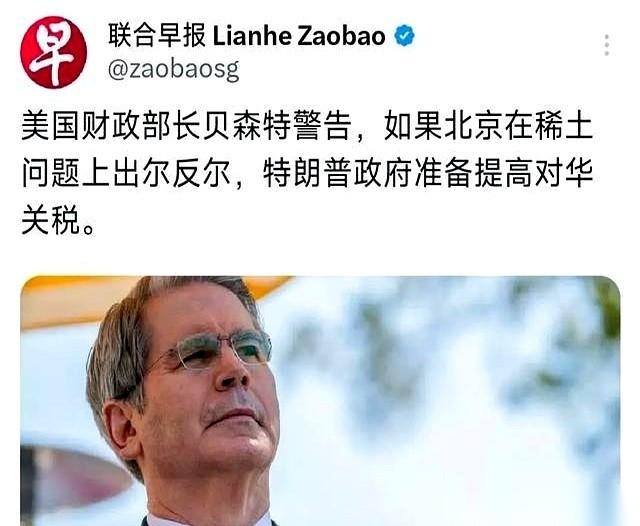吴石遇害后,侍奉他家29年的佣人阿香,凭3个选择全身而退。 这人不起声,劲压在地底下,像井边一块石,日头照着也不动,雨过一回也不动,谁要去踢它才会响一下,然后又沉下去不说话。 那阵人说没了就没了,从书房到刑场只隔一夜,灯灭了再亮,院里脚步乱,门口停一阵又走一阵,谁被叫出去谁没回来一清二楚,厨房门口站着个女人,围裙没解,水盆里的衣服漂着泡沫,名叫林阿香。 不是官,没枪,手里锅铲抹布,走廊里影子晃过她把火往小拧一点,汤在那儿咕嘟,她耳朵不抬,脚跟落稳,像早知道哪股风会直接拐进这道门。 十六岁进门,二十九年,家里起起伏伏过眼就是一阵,谁走谁留心里有杆秤,哪天窗纸薄了,哪天桌角松了,哪天心气被风吹出门槛,她不言声,只把柴塞进灶肚,水再滚一会儿。 一九四九,调令去台北,她提个小包跟在后头,台北天色不亮不暗,街口脚步紧,队伍拉长,白色恐怖三个字贴在墙上像块影子,人群里有人被叫名,有人回头有人低头,她在巷口买半斤盐,转角一辆车停着,铁门开开合合。 念书不多,眼睛在灶台边练出来的,谁在客厅停了多久,谁说话压了声,谁鞋底带了泥,一眼心里有个印,女人看这些,比翻报纸快,老屋要塌之前,先给自己留条小路,拐出去能不踩到水坑。 一九五零年二月底,书房门往外开了下,吴石叫她进去,柜门一扇一扇拉开,金条整,首饰包在绸子里,老物件擦得亮,话不多,就一句你拿够一辈子用的,她站着,手在围裙上抹了一把,眼睛扫过去,门轻轻合上。 她回一句两件旧衣够了,识字那本小册也带上,折好塞进布包,跟去街口找针线铺一样的步子,院子里的狗抬眼看她一眼又趴回去,地上影子挪了半寸。 第一件事就这么定下来,金不碰,拿了你就不是这屋里的用人了,站的位置全变,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她不求谁记住,只求脚下那条缝干净,拉绳子的手别沾泥。 第二天门口车停住,保密局的人进屋,抽屉一格一格拉,包翻开在桌上,旧衣两件,识字卡一本,角上毛边卷着,手指一摸是糙的,目光飘过去又收回来,像瞟到竹竿上那条补丁裤。 审问的屋里风从门缝里挤进来,木椅直直的,她把手摊在腿上,掌心全是茧,问话的人看着她,声线平,问题一把一把丢过来。 你家先生和谁接触清不清,她说我在灶台边,锅得看着,客人来不来,她说有人进门我就在厨房翻汤,汤别糊,传不传话,她说我就认那么几个字,识字卡是老太太教的,念得慢,不派用场。 每句话都落在锅碗瓢盆里,不躲不闪,不往外扯谁,也不拿自己当事,桌上纸笔摆着,线挂不上她的名字,捋到底就是无关两个字,像账本上随手划一道平线。 出来院里空,王碧奎在里头,孩子散在外头,屋檐下那股风把灰吹到角落里,桌上有个瓷碗扣着,翻开半碗冷稀饭,她把碗洗了,立在架子上滴水,围裙解下来叠成一块方。 第三件事走哪条路心里早有图,码头人多眼也多,渔船低低伏在水上不惹眼,夜里潮水起起伏伏,船板上有盐味,衣服上落的灰先抖干净,她缝进去的三根小金条躲在棉絮底下,针脚密密密,外面罩一层旧被套,再压几件洗到发白的衣裳,一包看着像擦桌子的布头。 检查的人踩上来,她先把东西自己倒一地,袖口一甩,衣服铺开,识字卡啪一下落在船板,她弯腰去捡,把卷起的角抹平,嘴里念两行卡上的字,手指着包角说这边旧被子,动作快,眼神不撞人,脚边的水晃一圈又平过去。 回到大陆,村口的树还是那几棵,泥路还是那条,她把名字改回原来的,遇上问的就说出去做工几年,学会几样菜,手脚利索,挑水的架子还在,肩窝的位置还是原来的位置。 没人把她和“烈士吴石”的屋里连起来,没人知道她那年看过谁的背影,听过谁的脚步,她把日子往前推,天亮做活,天黑歇,屋里拉一根麻绳,衣服洗了搭上去,风穿堂一过干了就收。 一九八三,消息进到她耳朵里,吴石被追认为烈士,子女站在墓前,纸花一排排,她就说他是好人,声音不高,像在屋里算晚饭要煮几碗米,邻里说她话少,人走后碑上刻三个字,林阿香。 回头看那三回,她都把事往小处落,手不伸,嘴不阔,脚不踩大路,留一道缝给风过去,也留给人过去,自己站住,天往哪边变她看着火候,锅里沸了就关火,起锅的时候不拖不拉。 保命能细到这步,全靠分寸,知道自己站哪块地,哪句能说哪句不说,什么该放下什么时候起身,门开着从侧边走,门关了不去碰,路一直在,脚步轻一点,印子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