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通透的话: “退休后最好的活法不是打牌,跳广场舞,串门,而是做这四件事。第一,每天下楼的理由就是买菜,倒垃圾,然后就不怎么出屋了,自己在家待着舒服,也不觉得闷。第二,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菜,平时刷刷手机,累了就躺会儿,简单自在。第三,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人打扰,也不用讨好别人,还不用被别人消耗。第四,不盲目跟风旅游,不上当受骗,还没人管着,吃好喝好休息好,心情好。” 退休第一周,儿子送给我一个智能手环,女儿给我报了老年大学书法班。我把手环收进抽屉,书法课去了一次就没再去。 从第二周起,我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方舟。 每天清晨六点,生物钟自然唤醒我。不紧不慢地煮粥,看小米在锅里翻滚出细密的泡沫。七点整下楼,不是为了晨练,是扔垃圾,顺便去菜场。 菜场的老刘认得我了。“老李,今天冬瓜好,炖排骨正合适。” 我挑了一小圈冬瓜,两根排骨,又买了半斤活虾。儿子总说网上买菜方便,但他不懂指尖触碰虾壳时那微微的弹力,不懂冬瓜霜白的茸毛在晨光里的样子。 回家八点。把菜分门别类放进冰箱,开始擦地。不是草草了事,是跪在地上,用湿抹布一寸寸擦。木地板的纹路在水痕中清晰起来,像复苏的河流。 邻居老赵在窗外喊:“老李,三缺一!” 我摆摆手:“忙着呢。”是真忙。 十点,我开始准备午饭。今天想做虾仁蒸蛋。蛋液要过滤三次,水要用温水,比例是1:1.5。上锅蒸八分钟,关火焖两分钟。掀开盖时,蛋羹平滑如镜,虾仁恰到好处地蜷成粉红的云朵。 这是我新发现的乐趣,把做饭变成实验,把家常菜做出馆子味。 午饭后,是我最享受的时光。阳台的躺椅被晒得暖烘烘的,我泡杯茶,打开手机。不刷短视频,不看新闻,专门找些冷门纪录片看。 看着看着会睡着,做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短梦。梦见自己是一片云,或者一块正在晾干的陶土。 醒来三点,喝茶,看书。看的都是以前觉得“无用”的书:《草木记》、《茶经》、《观鸟手册》。 女儿周末来看我,忧心忡忡:“爸,你天天闷在家里,不无聊吗?” 我给她看我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周二发现窗台麻雀多了三只;周三试验糖醋汁新配方成功;周四下雨,听雨打空调外机声像打击乐。 “你看,”我说,“我的世界很大。” 上个月,老同事们组织去西藏,在群里发照片,雪山壮美,湖泊澄净。他们问我怎么不去。 我回了张照片:今天做的文思豆腐羹,豆腐切得细如发丝,在清汤里悠悠散开。 “这才是我的雪山和湖泊。”我在心里说。 昨天,儿子非要带我去听养生讲座。台上专家侃侃而谈,台下老人们疯狂记笔记。中途我溜出来,在路边看两个老头下棋。 一个说:“将!” 另一个想了半天,把棋一推:“重来重来。” 他们都笑了。 我也笑了。这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生,不是被定义、被安排的老年。 今晚,我给自己烫了壶黄酒。酒温得正好,配着刚炒的花生米。窗外月光很好,落在刚擦过的地板上,碎银一般。 退休前,我以为最好的晚年是环游世界,是培养爱好,是融入集体。 现在才知道,最好的活法是安心地做回自己。像一棵老树,不再向往远方的风景,而是深深扎根于脚下的土地,在年轮里雕刻每一寸光阴。 我的方舟不大,刚好装得下我的整个世界。它不航行远方,只是静静地、稳稳地,停泊在属于我的港湾。 这就够了。 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不出门,不意味着与世界隔绝。 菜市场的寒暄、与邻居的点头之交,是一种低密度、无压力的社会连接,足以保持对社会温度的感知,却又不会消耗心神。 日常的采买,成了观察四季流转、感受市井烟火的仪式。 梭罗:“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 退休了,当外在的舞台落幕,家成了最后的,也是最真实的道场。擦拭灰尘,亦是在擦拭内心的杂念;钻研厨艺,是在用烟火气供养肉身与灵魂。 这绝非琐碎,而是一种极致的“生活禅”,在其中能收获到比在喧闹人群中更真实的存在感与成就感。 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退休后的智慧,不再是拼命做加法而是开始做减法,在“损”掉外在浮华后,抵达内心无为而治的安然。 拒绝成为“老年旅游团”、“保健品营销”的目标,不仅是智慧的体现,更是自尊的彰显。 杨绛:“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退休,正是从“期盼外界认可”的桎梏中彻底解脱的时刻。 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最大的奢华,不是诗和远方,而是内心的秩序与平静。 最好的生活,不是被安排、被看见的,而是自己亲手构建、独自享受的。 最高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的底气与从容。 这,或许就是我们用大半生的劳碌,最终为自己换来的、最体面、最智慧的奖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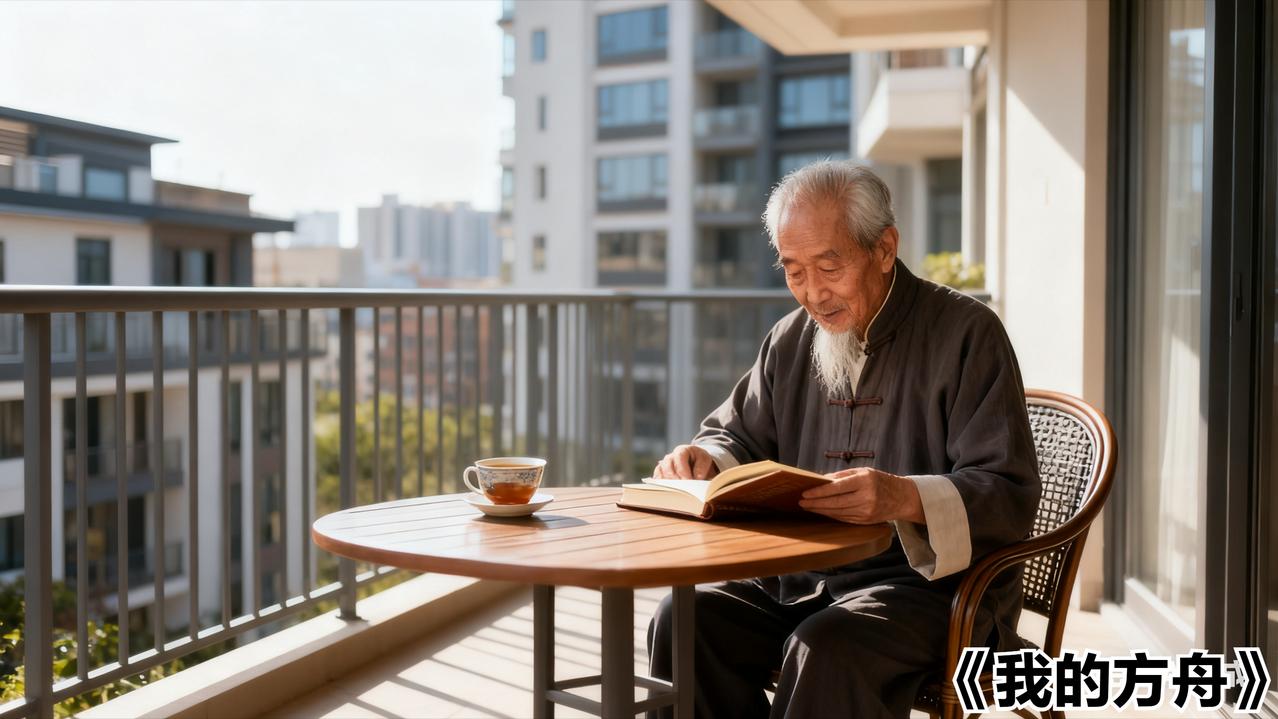
评论列表